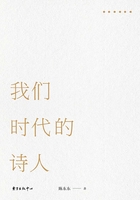除了高尔夫球和扑克牌桌旁的社交夜晚之外,在我和东姑之间的友情中,第三种消遣内容是我们对“皇者运动”(Sport of Kings)的共同兴趣——它其实应该称作“大众运动”(Sport of Everyman)。因为任何人,无论贫穷还是富有,都可以拥有赛马的一部分、享受赛马场中的乐趣。
“你的真诚的,东姑阿都·拉曼”——马来西亚第一任总理与我们的驯马师马韦(Mawi)和赛马“平加特·马斯”在一起。注意照片上东姑的亲笔签名。
东姑对马的迷恋源自孩提时期,当时他学会了骑一匹花斑小马。20世纪20年代在剑桥读书期间,他会为了参加附近的纽马基特赛马而逃课。后来,他把学习法律的失败归咎于“马太慢、女人太快”。此后他关心的是战争和政治。直到1959年,东姑在正式访问澳大利亚期间(那是个无与伦比的赛马国家),才得以继续他与赛马场之间的恋情。他参加了那年的墨尔本杯(Melbourne Cup)绝顶美妙的赛马盛事。
从澳大利亚回来,东姑心潮澎湃。“天刚一擦亮,”东姑在《观点》(Viewpoints)中写道,“我就到了马厩或者赛马场,观看赛马训练。”他要我跟他一起赌一匹名叫平加特·马斯(Pingat Mas)的赛马。他说那匹马能够赢得大赛。我回答说:“东姑,经济形势不好,我恐怕不能赌。”听到这里,他回答说:“我不管经济形势是好是坏,我已经押上了我的那份,你必须把你的那份也押上。”接着,那匹马赢了大约5场比赛。东姑从此没完没了地戏弄我:“当‘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我为你在赛马身上赚了钱。”
他为我做的并不止这些。后来,东姑的保镖没少花工夫,确保我完全了解了这一事实。
别误会,五一三屠杀开始的那天,我在新加坡,没有参加那天以及第二天晚上的备受责骂的纸牌游戏。我和我妻子急于返回吉隆坡的原因,与其说是因为我们的孩子们(他们住在我们在Jalan Damai的家里。那里受到的冲击不那么严重),倒不如说是更加担心我母亲和姐妹们,因为她们住在黑尔路,也就是现在的拉查阿卜杜拉路的家里。那里是贯穿甘榜巴鲁的主要通道,吉隆坡没有任何地方比那里更加危险。
当我给前副首相敦·伊士迈·阿都·拉曼博士(Tun Dr。Ismail Abdul Rahman)打电话时,他说只有东姑能把我们家人送到安全地带。我联系上了东姑,他批准派一辆巡逻车到黑尔路营救我的家人,同时当时的国王丁加奴苏丹派出一辆巡逻车到机场接我,并邀请我住在王宫。我知道,这个好意我是必须谢绝的。
我待的地方,就是跟我的家人一起待在家里。不过,我接受了国王送来的一支步枪和东姑给我的一把手枪——这两样武器都有许可证。
“国王和首相,”东姑的马来保镖直言不讳地对我说,“每人给了你一把枪,用来保护你和你的家人免受他们的马来同胞的伤害,这就是深厚的真挚友情。”
的确如此。可是,如果(上帝饶恕我)我不得不用上那些武器的话,我会用那些武器对付谁呢?
让小若吉舞女跳起来!
1970年6月,沙特国王费萨尔访问马来西亚。东姑作为首相的日子已经所剩无几。如前所述,那位君主请东姑当伊斯兰教会议总秘书处的第一届主任。该机构设在吉打,致力于伊斯兰教的团结。
东姑说:“我告诉陛下,我根本不是这个位置的合适人选,因为我热爱生活,我喜欢经常赛赛马、玩玩纸牌。”东姑在吉打担任那个职位几个月后给我写信,说即将启程返回马来西亚的家时说:“正像我在这些个月里让自己放弃了人生的快乐一样,我将真正享受人生的所有快乐。”我承认,当他接着在信中说出下面的话时,我深受感动:“我希望你能够陪着我,这样我们就能恢复我们中断了的日子——晚宴、扑克、赛马和高尔夫球。”
下面是记载在穆宾·谢泼德(Mubin Shepard)的《东姑的人生和时代》(Tunku:His Life and Times)中国王费萨尔对东姑的回答:“我对你非常了解。我不是要你做传教主,我只是请你帮助促进穆斯林的团结,这是你能够做出大量贡献并付诸实现的任务。”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那位沙特国王是伊斯兰教清教徒式瓦哈比教派的象征,强调可兰经戒律,竟然会邀请东姑把全世界的穆斯林都组织起来,即便我朋友因为偏离伊斯兰教教义而受到远不如他们严谨的马来穆斯林的严厉斥责。后来,东姑获得了国王费萨伊斯兰教国际贡献奖(King Faisal International Prize for Service to Islam)。
我曾经多次被问到东姑是否信教,我的回答始终不变:如果世界上还有人相信上帝的话,那么那个人就是东姑。他深信灵魂世界的存在,而我对他的这个世界羡慕不已。
“东姑,”李光耀回忆说,“经常公开谈论他的吉祥数字、吉祥颜色和吉祥梦境。对于这种另一个世界的影响作用,他的态度非常认真。”东姑的好朋友、《马来前锋报》(Utusan Melayu)第一任总编拿督阿都·阿齐兹·艾哈迈德(Abdul Aziz Ahmad)说:“他经常谈论梦的问题。他常常说:昨天晚上,我梦到了这么件事。”东姑悄悄向我透露说,有一天夜里,他的床颤抖起来,一个鬼魂出现在他的面前。他非常害怕,便开始祈祷。在那之前很久,他梦见他的父亲阿都·哈米德(Abdul Hamid)从一棵树上摔下来,而他赶忙及时接住了他。他后来解释说,那是要防止他的父亲在日本人于1941年进攻马来西亚后离开吉打。
东姑在写给我的信中,有时会怀疑是不是安拉在惩罚他。比如,他对自己离开吉达的工作而延长回国休假的时间感到内疚,因为他注意到他的几匹赛马由于他躲避责任的关系死了。“至于究竟是属于巧合,还是天意,”他在1973年10月15日写给我的一封信中说,“很难说清楚,但是这种事已经连续发生了3次。如果这意味着我必须放弃赛马的话,对我来说实在太困难,因为这是我沉醉其中的一个小小的生活乐趣,真心希望上帝能够原谅我。在吉达的时候,我会以穆斯林的方式进行悔过(献祭、扶贫),以便在上帝面前改过。”
我可以进一步证实,东姑从来没有遗漏过一次祷告,甚至是在聚会期间或日常政府管理工作过程中。他常常把一切都放在一边,以便进行他午后的祷告,也就是穆斯林日的第二次祷告,然后他再心情宁静地睡个午觉。
东姑相信,世界上伟大的宗教都是戒律的地位高于世界上最神圣的人的行为做法。他在《充满挑战的时代》(Challenging Times)中写道:“伊斯兰价值观,根据我的理解,意味着和平、仁爱、合作、诚实、准时、勤奋、荣誉……换句话说,伊斯兰价值观就是人类的美德。”有些人可能会批评他,因为他相信上帝没有怒气,会不作评判地将人们带进天国,但是,谁都不能怀疑他的仁慈慷慨之心。他认同我所信仰的基督教新教卫斯里宗的创始人卫斯里(John Wesley)的理论,即人应当:
竭尽你的所能行所有的善,
尽你所能采取所有手段行善,
尽你所能采用各种方式行善,
尽你所能在所有地方行善,
尽你所能在所有的时候行善,
尽你所能对所有人行善,
尽你所能永远行善。
谦逊的东姑知道,他距离这个理想目标还差得很远。
东姑总是指出自己的缺点,尽管其中之一并不是(他不止一次地私下向我保证)吃猪肉。他相信,关于吃猪肉的禁忌源于猪肉中危险的旋毛虫,而穆斯林宗教学者将来某一天会因为卫生条件的改善而修改这一戒律。尽管如此,他并不打算违背如此重要的一条戒律。
东姑的生活平淡无奇,但并非缺乏色彩。他被披露是20世纪50年代一个欧亚混血律师及其英国妻子离婚诉讼案中的共同被告;20世纪20年代,他作为一个年轻人在英国驾车时收到过23张交通罚单;如前所述,他玩赛马、扑克、喝烈性酒,并自称是个“花花公子”。在《回顾》(Looking Back)中,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是一种强调的口气,而不是询问:“如果你不喝酒、不抽烟、甚至不享受女性的陪伴,那么活着还有什么意义?”有一次在马来西亚国会,他要求“一次都没有在诱惑面前屈服过”的所有人站起来。当他注意到自己作为发言人还站着的时候,赶忙坐了下来,结果引起人们的轰然大笑。“我拒绝过苦行僧的日子,”他总结自己的行为时说,“因为我生来不是过那种日子的。”
东姑之所以反对清教徒,并不是他们试图让我们按照他们的方式来思考,而是试图让我们按照他们的想法来做事。他赞成给鸦片成瘾者核发许可,称卖淫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任何人,”他多次写道,“都不可能阻止它,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他相信,不断试图阻止卖淫的人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恐惧感,即在某个地方有某个人可能很快乐。他反对警察去打击(比如说)偷情(khalwat)和若吉(joget)舞女。“从人道的意义上说,真正的错误和犯罪,”他在《观点》中这么论述舞女,“是剥夺这些妇女的生计。”说到对通奸者乱石砸死,他认为:“如果在这个国家通过了这么一条法律的话,那么可能需要用来砸罪犯的石头也许不够用。”他不止一次地告诉我,有关限制就业机会和控制私人生活的企图,是在牺牲社会下层的人民,使得他们的生活比从前还要难以忍受。
但是,东姑还相信基督教所说的“祷告的力量”和穆斯林信守的伊斯兰教五大教规之一——每日5次祷告拜功(solat)。在我认识他的30年中,我在场的时候他没有错过一次祷告。认识他的时间更长的拿督阿都·阿齐兹确认从来没有见他疏忽过祷告——对于他来说,始于每天的清晨:起床、沐浴、晨礼(fajr)。
“祷告,”东姑在《星报》中写道,“令我大受裨益。年轻的时候……我对生活的严肃一面漠不关心。然后,在日本占领期间,我们面临着人生最大的挑战。结果,我开始了祷告……从那时起,我的生活发生了变化。我变得更加认真,对我们国家和人民的事情更加感兴趣,而且更注意观察。我的运气仿佛也发生了变化,而且是往好的方向转变。”
在斋戒和喝酒问题上(虽然他只是在晚上的昏礼之后才喝酒)表现出人性弱点的东姑,在祷告方面却是完美典范。“他努力了。啊,他非常努力了,”拿督阿都·阿齐兹说起东姑跟自己的人性弱点的斗争,而且他取得了成功——至少在虔诚地祷告方面。
在我们多次前往怡保赛马场的途中,东姑经常停留在路上的某个祷告场所(surau)进行午间祷告(zohor)。他完全可以很方便地在内心祷告,因为他在路上,或者因为除了亚拉以外谁都不会知道有什么区别,他也可以少祷告一次。但是,不。他总是停下来,走出他那黑色镀铬凯迪拉克-弗利特伍德的车子,然后走进屋里,跟当地人一起祷告。
有些想诋毁东姑的人会说,在社团(ummah)中间祷告是高明的政治行为。消息传了出去(比如通过本回忆录),东姑履行了一个重要的伊斯兰教义务。进一步说,那些诋毁者说的是实话。
但是,事实不仅于此:东姑不仅进行了祷告,而且他似乎很需要祷告,表明他真正相信自己是在跟上帝交流,并且很喜欢跟上帝保持一种关系。批评家们会称之为作秀。然而,我还注意到有一件事(据我所知),过去从来没有被提及,当他祷告时间很长的时候,而且常常是戴着翡翠戒指(表明他正苦恼)。他在祷告结束后一定会明显地宁静了许多,比他半个小时、甚至一个小时前走进祷告场所时更加幸福、更加坚强。
舒展的眉毛,平滑的前额,淡淡的微笑,时而由衷欢愉的神情——这些并不是一个演员的技能,而是烦恼得以解除后的幸福表现。
以我的经验,拥有宗教信仰的人有两种类型。第一种人是神秘主义者,或基要主义者。他们因为听到了上帝的呼唤,为了来世而在这个世界上牺牲甚多。第二种人是事务缠身的忙人,是东姑阿都·拉曼那样的人。他们不怎么看重诸多宗教戒条,不是因为某种具有破坏性的无神论,而是因为他们深信自己能够向上帝解释自己的罪过和弱点。对于东姑来说,祷告不仅仅是一种义务(5大教规之一),还是灵魂的食粮,用于满足他跟上帝交流的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