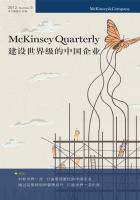镇长三刁的傻儿子结婚,在鱼镇是无人不知的大事情。所以,二月初八这天,整个鱼镇倾巢而出,都到镇上最好的酒店醉仙酒楼吃喜宴去了。在鱼镇稍微有点影响力的人都来了,唯独大蛇没有来。一个不知道内情的人问三刁:“大蛇兄弟怎么没有来呢?”三刁狡黠地笑了笑,他说:“他忙,在筹备新的房产项目。”
对于青美的家人和亲戚来说,这是一场尴尬的喜宴。在婚礼现场,黑飞的表现确实太拙劣了。甚至可以说,在这场婚礼上,黑飞不仅不是主角,他似乎算不上一个真正的人,只是夹在三刁与青美之间的一个玩物。特别是在向青美的父母敬茶时,黑飞出尽了洋相。
青美和黑飞端着茶杯,来到她的父母面前。青美说了爸爸妈妈请喝茶之后,就等着黑飞也说这句话了。可是,无论怎样黑飞就是不愿意说,青美和三刁开始循循善诱,教他如何说。不过,黑飞始终只是一个劲儿地摇头,打死就是不说那句话。最终,黑飞一口喝掉茶杯里的水掉头便走,引来人们一阵哄笑。气急败坏的三刁只得代替儿子向亲家敬茶。但是,急躁与愤懑的三刁犯了一个让人忍俊不禁的错误,他忘记了自己的身份,而是直接开口说:“爸爸妈妈请喝茶。”话音刚落,现场又是一阵哄堂大笑。
尴尬,除了黑飞以外,每一个人都觉得尴尬。青美的父母脸上原本就不多的笑容,早已枯萎了、消失了。他们呆若木鸡地坐在那里,感觉是参加一次事不关己的宴会。青美也觉得尴尬与难过,她并没有后悔嫁给这样一个男人,但是,当时内心里依然有种说不出的难受。在转身的那一刹那,她的眼泪悄悄地滑落。
这天中午的婚宴还闹了很多笑话,都是与黑飞有关的。这个傻子根本就不知道结婚是什么意思,更别说一个新郎在婚礼上的职责和义务了。黑飞就像一条被三刁和青美牵着的小狗,被迫地对一些根本就不认识的人摇头摆尾。偶尔,他也会嘿嘿地笑着说:“抽烟,喝酒。”
如果不清楚真相的人,还以为是三刁和青美结婚。这天三刁表现得格外抢眼,几乎酒楼的每一个角落都能看到他的身影,听到他的声音。其一是傻儿子结婚他真的高兴,沾沾自喜,洋洋得意;其二也是因为黑飞根本应付不了台面,只得他自己左冲右挡地圆场,尽量避免闹出什么笑话。
最终,三刁醉了,醉眼迷离的他拉住青美的手一遍又一遍地摩梭,然后他说:“孩子,三刁我保证让你这辈子过鱼镇最幸福的日子。”
“你保证有什么用?是你儿子黑飞保证。”平时与三刁要好的一个哥们眼看着他喝醉了,就上前去与他开玩笑。
“青美以后就是……就是……”过量的酒精让三刁的三寸不烂之舌结巴了,半天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来。他说,“就是我的人了。”
“兄弟,这话不要乱说,青美是黑飞的人,不是你的人。”
三刁眼睛一愣,看着眼前扶着他的哥们,半晌才发出低沉的笑声:“是黑飞的人嘛,但也是我的人啊。”
“黑飞的就是黑飞的,女人是不能共有的。”
“黑飞是我儿子,我们是一家人嘛。”三刁佯装愤怒地看着与自己开玩笑的哥们,他明白对方在调笑自己喝醉了,“兄弟,我很清醒啊,别以为我喝醉了。”
“你没醉,是我醉了。”
三刁哈哈大笑起来,尽管笑声轻飘飘的,但还是感染了众人,大家也都跟着笑了起来。
在醉仙酒楼一派喧哗与热闹时,米勒家的境况却是天壤之别。安富在派出所关押已经好多天了,至今没有一个明确的结果。福清和米勒为此焦头烂额,对于如何解救安富,母子俩也是无计可施。他们能够做的就是每天到派出所等待。每天早上一到派出所,他们就问:“案情什么时候有结果?”
“还在审理,有结果了就告诉你。”
下午离开的时候,他们又胆怯地问:“明天有结果吗?”
“那要明天才知道。”
最近几天来,几乎就是这样一成不变地度过。福清和米勒忐忑不安地带着期望而来,却又忐忑不安地带着失望而归。如何洗刷掉安富的冤屈还他一个清白,成了这个家庭唯一的目标。
二月初八这天,福清和米勒又来到了派出所。今天,安富、福清和米勒三个人的心情都格外沉重,因为青美最终嫁给了鱼镇广为人知的傻子。而且,安富走到如此境地,或多或少与米勒的婚事有关,与青美有关。如果不是青美的父母非得要米勒在鱼镇买房子才能结婚,那么,也就不会有后来安富与大蛇的争吵和打斗,在大蛇的妻子和情人相继被害之后,安富也就不会成为怀疑的对象。所以,当三个人在此时此景见面时,各自的心里都别有一番复杂的滋味。
“青美今天举行婚礼?”安富问米勒,不知道他是关心米勒呢,还是关心青美。
“在醉仙酒楼。”米勒说,“听说很热闹,好像整个鱼镇的人都去了一样。”
“镇长的儿子结婚嘛,人们当然争先恐后地去。”安富的口吻中带着非常明显的冷嘲热讽,他清楚三刁在鱼镇的影响力,就算是人们不喜欢他,也得装着喜气洋洋地道贺。他稍微停顿了一下,转而自嘲地说起来,“我没有出息,不是个好爸爸,你看黑飞那个傻子多有福气,镇长老子轻而易举地就帮他把老婆找到了。”
“这不管你的事,是我自己没有出息,连个女人都找不到。”米勒口气生硬地开解安富,他依然对青美充满了仇恨。就算是他知道自己曾经给青美带来了深深的伤害,但是,米勒也很明白她确实看上了三刁家的四套房子。他对安富说:“就算我们能够在鱼镇买一套房子,她也不会嫁给我。因为我们只有一套房子,而黑飞家则有四套。”
“青美会是这样的人吗?”安富长叹一口气。
“我觉得是。”
话题“咔嚓”一声中断了,促狭的看守所里显得极其安静,能够听见三个人慌乱的呼吸。在安富和米勒对话的过程中,福清一直神情呆滞地坐着。其实,她有些麻木了。开始的时候,她一直担心儿子的婚事,不能让米勒一辈子打光棍啊。接着,就在青美与米勒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大到伤痕无法弥合时,安富又出事了。福清又开始为老头子的事情操心,她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相濡以沫几十年的丈夫蒙受不明之冤呢?如果谋杀罪成立,那可是死罪呀。残酷的现实折腾得这个朴实的农村妇女垂头丧气、奄奄一息。
“她结婚就结吧,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福清冷不丁地说起来,让安富和米勒感到惊讶,仿佛才记起她也在现场。她说:“我看玉梅也不比青美差。”福清突然想到了玉梅,她觉得这个女孩子还是很不错。
米勒觉得母亲的话不可思议,她怎么在这个时候想起玉梅了?“她有房子,就比青美好?”他目不转睛地瞅着福清,似乎急需要她给自己一个回答。
“哪里是房子的事?”
“那是什么?”米勒突然来了兴趣,想听听福清到底如何评价玉梅,“你说说看,玉梅到底好在哪里?”
“她比青美更喜欢你啊。”福清若有所思地说,“一个喜欢你的女人,一辈子都不会给你添麻烦的。”福清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世故。其实,她之所以在这个节骨眼上夸赞玉梅,无非是想说服米勒娶玉梅为妻。福清真的担心,如果米勒不好好把握玉梅这个机会,按照目前的情况这辈子真的可能娶不到老婆了。
说完,福清一个劲儿地给安富递眼色,希望他也极力怂恿米勒不要嫌弃玉梅,与她结婚算了。安富心领神会,但却因为心情沮丧而不知该如何表达,他只得干瘪而嘶哑地说:“你妈说得对。”
米勒没有说什么,他知道父母的意思。事实上,此刻他没有心思考虑玉梅的事,他的脑子里依然浮现着青美的音容笑貌。曾经美妙的记忆,如今变成了挥之不去的阴影。到底该如何处理这段纠结的情感,对米勒来说是件痛苦不堪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