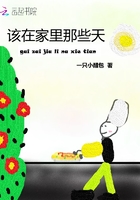红山马道间的泥泞污秽不堪,地上的血迹沿着水流一直绵延至山道口,而一队足有数千人的铁骑大队从大雨中骤然涌出,令一众城西禁军的士兵看的直瞪眼。
森寒的盔甲,面上头盔下放了面罩,腰间钢刀凌冽,战马神骏威武,这些甲士一看就不平凡。
为首一人在奔驰间高举右臂,一勒缰绳,队伍立刻缓缓停下。
那人掏出腰牌展示,问:“这里谁主事?”
“在!”为首的校尉策马前行,“卑职城西禁军校尉崔引弓。”
“我乃满红关斥候长,梁封候。”那人掀开面罩,露出一张清爽的面容,“崔校尉可是押解甄氏一族前往满红关?”
崔引弓一看那腰牌就知道来人不简单,边塞重甲铁骑,斥候分配的一般都是快马,盔甲则是鹿皮软甲。
我可梁封候领着数千身披铁甲的铁骑,却又司职斥候长一职,说明他立的军功可不止探报这么简单,这人起码是名千夫长。
“正是。”崔引弓抱拳,“队伍皆在此,都尉大人这是要带队到哪去?”
“本都尉接到驿站快报,甄氏一族已过代州地域,一路上舟车劳顿,冬季雪大,今夜又有大雨,便率本部铁骑千余,前来接应城西禁军。”梁封侯突然提高嗓音,“城西禁军的弟兄们都是好样的,这一路,辛苦了!”
“呼哈!!!”
千面森寒头盔下的咆哮声如群狼啸月,吓的一众城西禁军的士兵都面色发白。
崔引弓面色难看,这哪是来接应的,这分明是领着大军来施威。
“都尉大人这是哪里的话,都是给陛下当差的,哪来辛苦一说。”崔引弓挤着笑,“一家人,说两家话,显得多生分。”
崔引弓这番话已然将自家军队的位置放低,一众亲卫闻言都默然垂首,不敢与这支铁骑对视。
梁封侯没搭理他,顾自问:“队伍中可有甄氏一族后嗣?”
崔引弓心头一跳。
他的笑容骤然僵在面上,旋即侧头低声问:“追人的队伍回来了吗?”
亲兵面泛苦色,回答说:“大人,山道拥堵,追出去了几骑,其余的人还挤在里面呢。”
“没用的东西!”崔引弓面色阴沉,“这人要是追不回来,到了边塞,你们统统都给我去大漠杀外寇。听着没?!”
“小的这就去疏通道路!”亲兵急了眼,侧身指了几人,“都跟我来,走!”
几名亲兵连忙策马朝着山道前方奔行,这一点被梁封候看在眼里,眉头立刻微皱。
梁封侯震声问:“崔校尉,本都尉问话,你为何不答?”
崔引弓强挤微笑,说:“甄毅后嗣自然在的,我等心知甄毅虽为叛贼,但也为郑国守了那么多年边塞,自然对其后嗣礼待有加,只是队伍长,人杂。在下已派人去找了。”
崔引弓话刚说完,边塞铁骑中一骑向前逼近,问:“敢问崔校尉,在下方才听到山道内有喊杀声,这是怎么回事?”
崔引弓打马虎眼,说:“这位兄弟说笑,只是这腊月飞雪,囚犯受冷便会喊苦喊冤罢了,何来喊杀声?”
城西禁军生活在崇都,吃喝嫖赌样样精通,尤擅揣测上位者心思。士兵们听着崔引弓的话,都默默地将山道口封住,遮挡了身后满地的尸体。
尸体虽然被遮挡了,但是血迹顺着雨水冲刷而下,渐渐溢到入口处,染红了堆积的厚雪。
“崔校尉真是张口就来。”梁封候手掌按着大腿俯视,“无喊杀声,这哪来满地的血?”
崔引弓装出为难的表情,说:“都尉大人,喊杀声的确不曾有,只是方才山道有囚犯意图逃跑,弟兄们捉拿时,囚犯誓死反抗,我等便就地正法,杀了几个人以儆效尤。”
就在这时,天际的大雨中突然传出一声鹰啸,一道黑影紧跟着俯冲而下,直直落在梁封候的肩上。
轰鸣之下,雷光闪烁,借着炸起的雷光,崔引弓看的仔仔细细,那赫然是一只足有五六岁孩童大小的老鹰,一声黑白羽毛,利爪扣在铁甲上,双目炯炯有神,直勾勾地盯着他。
“哦?在崔校尉手下胆敢逃跑,真是不知死活。”梁封侯那双眼睛也像是肩上的鹰,“红山马道属边塞,城西禁军的弟兄们想来不熟路况,那本都尉便与诸位一道护送。”
他这话像是命令,语气透着不容置疑。
“这……大人,这都是卑职应该的,只是这路况不好走——”
“好走,你让人退开,我来领队。”梁封侯策马直直走到近前,两匹马高低不等,他寒声说,“另外让人把甄可笑带来,我要人。”
这是彻底说明了来意,崔引弓一阵窒息,嘴角不禁抽搐了几下。
“大人,队伍人数众多、繁杂,找人需——”
“我说了,人。”梁封侯瞪起眸子按住刀柄,“我现在就要。”
崔引弓冷汗透湿了背,结巴说:“卑职、卑职,卑职这就是去找!”
“斥候!”梁封侯收回咄咄逼人的目光,厉喝一声,“走!”
“呼哈!”
千骑雷动,铁蹄下雪水四溅,这支森寒的军队整齐向前,魄人的气势下,一众城西禁军吓地立刻主动散向道路两旁。
而就在这时,山道前方一名士兵策马疾驰而来,他一见到铁骑军队,立刻勒紧缰绳,翻身下马,跪地急声说:“报!追击的人手被囚犯杀了,大人,甄、甄可笑……”
“如何?!”崔引弓面色剧变,“快说呀!”
“跑了!”士兵嚎着哭腔,“与他同行那名少年武艺高强,杀了我们几名士兵,带着人骑马跑了!”
崔引弓攥紧拳头暴喝:“都是饭桶!连个娃娃都抓不住!”
“崔校尉。”梁封侯冰冷的声音陡然传来,“你未曾与我说,甄可笑已然逃了。”
崔引弓抬手不知是在擦汗还是擦雨水,艰难地说:“大人,我……”
梁封侯瞪了崔引弓一眼,厉声喊:“交河!”
方才说话的那名铁骑策马急奔几步,抱拳说:“在!”
“带上一队,去把崔校尉丢了的人找回来。”梁封侯沉声侧眸,“记住,不可动武,如若小姐有丝毫差池——”
交河立刻紧接着出声:“如有闪失,军法处置!”
交河带走了几名铁骑,策马飞驰而过时,撇眼看了崔引弓一眼,这道目光像是用刀刻在了崔引弓的眸子里,惊的他浑身脊背透凉,冷汗骤然冒出。
这便是大漠边塞铁骑,浑身都是杀意。
……
元吉带着甄可笑骑着马飞驰而下,一路上大雨滂沱,雪花漫天,就这样直直策马跑了足有数个时辰。
前方大路开阔,山道两头逐渐显露出幽寂的密林,地上的沙石逐渐被一层黄沙覆盖,马蹄踩的细沙飞洒,而正前方,一道巍峨雄伟的关口霍然现出。
满红关,到了。
城墙上插着火把,值守的士兵正立在墙头,听着下边的动静,高声喝问:“城下何人?”
甄可笑抬头,高声呐喊:“甄毅之女,甄可笑。”
士兵一愣,他取下火把走到城垛边,俯身向下直视,说:“走近点。”
元吉策马前行,到了城门口才停下。
昏暗的火光下,雨水滴在火把上冒着滋滋响声,士兵低头细看,心中犯起嘀咕。
他沉默须臾,说:“待我回禀尉史大人,二位稍候。”
士兵说完飞快向着城内奔走,他没见过甄可笑,但清楚天明时,梁封侯便已带队前往代州等待流放队伍,按理,甄可笑应该是跟大队一起回来才是。
可是城下的确有名少女,他必须尽快通知边塞尉史刘朔云,因为刘朔云早年曾入过王府赴宴,见过甄可笑的模样。
房内熏了香,桌前烛火摇曳,刘朔云倚着扶手撑腮读卷。
梁封侯的队伍迟迟未归,他心中不安,按照平时这时辰,他早已入榻歇息,可是迎接甄可笑入边塞一事,他已筹备了数月之久。
甄毅独女要被流放到边塞,月前他又接到圣旨,押解流放队伍的城西禁军要被编制入满红关,这一点他看的比别人清楚。
满红关已有数月无大将掌军,关内十万精锐,对于许多人来说都是一股不可忽视力量,同时也是一股令崇都上下不安的压力。
只因这支军队从郑国建都立制至今,自始至终都是甄氏一族在掌控,现在没了大将,天子又将城西禁军安排进来,想来是为将来掌军将领铺路。
那么甄可笑留在这里,对于那尚未到来的将军,永远是个隐患。
刘朔云是甄毅带出来的人,心中记着恩情,同时也察觉出太尉年迈,对军政已然不如以前那般有决定权,倒是司空与尚书台,正在逐步渗入军政一块。
也就是说边塞对于甄可笑是安全的,但也是危险的。
所以他想了个法子,就连梁封侯都未曾告知。
“报!”士兵匆忙推开门,单膝跪地,“大人,城下有人自称是甄可笑,将军的独女。”
刘朔云惊地骤然起身,急声问:“人呢?”
士兵抱拳抬头:“小人让她在城下等着。”
“封侯果然把人领回来了。”刘朔云喜色稍上,转瞬褪去,“城西禁军可曾随斥候营一道回来?”
士兵立刻回答:“不曾,斥候营也未曾回来。大人,城下只有一骑两人。”
“只有两人?”刘朔云惊疑不定,旋即一挥手,“走!”
两人出了房,沿着长廊直直来到城墙上,刘朔云俯视向下,只见大雨中的确只有一匹马,两个人。
甄可笑一眼就认出刘朔云,立刻高喊:“刘叔叔!”
刘朔云借着昏暗的火光认清了人,他颤声惊呼:“小姐!”
士兵见确认无误,立刻朝城门下喊:“快开城门!”
几名士兵闻言立刻起身去扛闩门的横木,可就在取下一根时,就听红山马道处响起了一阵呐喊。
“莫要开门!”
刘朔云探头望去,就见大雨中五名身披轻甲的士兵,骑着马奔驰而来!
轻骑士兵边跑边喊:“这二人是逃犯,莫要开门!”
城垛上,士兵看的真切,说:“大人,这不是梁都尉的斥候骑。”
“轻骑矮马,是城西禁军的人。”刘朔云看出端倪,沉声说,“快开城门,放两人进来。”
士兵闻言立刻飞奔下城门,几名士兵合力横木向下抬,而上头还有一根横木。这些横木重达百斤,需要数名士兵合力才能抱起。
就在他们忙活着开门时,那几名轻骑已然飞快逼近,旋即团团围住元吉与甄可笑,一人厉声说:“叛贼逃匿,终是插翅难飞,你二人立刻束手就擒!”
第三根横木被抱起,城门缓缓打开,刘朔云与数名士兵伫立在门前便停了步,因为现在他很是为难。
流放私逃,按律法当斩。所以他与梁封侯商量提前去代州接人,以保护甄可笑安全为由,接管队伍。
这样就能避开城西禁军,实施他的计划。
可如今城西禁军已经追到门前,他顿感无力,只觉得千算万算,不如天公不作美。
元吉抽出路上夺来的钢刀,说:“小姐,站我身后。”
“元吉。”甄可笑面有忧色,她躲在元吉身后轻声说,“要小心。”
元吉猛然拔出钢刀,雨珠落在锋锐的刀锋上,脆声如铮铮琴音。
他面色森然,刀锋遥指五人,说。
“谁敢阻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