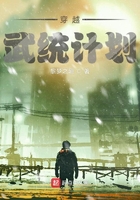有人说,结婚冲喜能治好妈妈的病。甄一圣不怎么信。
甄妈说,如果能看到女儿穿婚纱,将死而无憾了!
“怎么又来学校了?不知打电话?”我划了一下甄一圣的高鼻子。
“还怕啥?”甄一圣撅起了嘴。“是不是不想见我了?”
“咱们的事已被传成了奇葩!”我说,“怕那许多注视的人,认为我们又变回去了!”
虽然我之前无数遍想过这事,但此时一听,还是怔了一下!
“别急!我去给甄妈说,再等等,至少等到高考后。”我说。
“我已给妈妈这样说了。
医生说,妈妈…可能…可能……撑不到高考了……”。她眼泪掉下来。
“其实我心里一百个不同意,你知道吗?”我说。
“我知道!”她指了指胸口。
我心里堵得慌,我想一定要去见她妈妈。
我拉住一圣的手:“走,回你家。”
“甄妈,这个时候,我本意不想影响您的心情!”我说,“但是我不说,怕来不及了!”
甄老师瘦削的面颊努力挤出几分笑容:“孩子,说吧!”
“为什么要拆散我们?”
“那是为了你好,孩子!”她的身躯在椅子上颤抖了几下,“一圣不配你,她只能做个普通人,你们不是同路人!”
“我就是个普通人,甄妈!”
“你能放下理想,和她结婚过平凡的日子吗?”
“我能!”
“你敢说一辈子不后悔吗?”甄老师眼里噙泪,“在你成为我的学生时,我就看出你不是个普通的小孩。假以时日,必成大气!我不能让一圣拖累你啊!”
“甄妈,您高估我了。理想和爱情可以同步啊!”
“可是,这现实……,一圣等不到你理想实现的那天了。我不想在死后,她还孤苦无亲人……”她泣不成声。
“孩子,你生来就应该是做大事的人!不要被儿女情长左右了脚步。男子汉何患无妻,后来,你会找到助你腾飞的女人的!”
甄一圣的婚事很快在一个周未举行了。
小区里铺天盖地的喜字闪烁着喜庆的红,像初升的阳光涂播在人民脸上、心里。
甄妈妈打心眼里高兴!
她被病魔折磨得太过骨感的身体,穿着那件她喜爱的红色丝麻上衣,精修过的齐耳短发,招回了往日的干练。
我想,冲喜一说也可能有道理:她看上去多精神啊!
我忙着接待客人,满头是汗。
“儿,歇会吧。”甄妈妈怕我累着。
“不累,妈。”我说,“刚才,大总让我去催新娘化妆。我过去看看。”
“好,乖儿!”她抹了抹眼角。
甄一圣一人在里屋,仍旧一身素妆。给她化妆的人被撵到了门外。
“你看你,饭不吃,头发不坐,衣服不换,妆不化…婚车在外面急等着,你到底要干什么?真不像话!”我有些生气!
“这婚,我不想结了!”她赌气转过脸去。
“怎么了?”
“怎么了?!你还不知道吗?”
“小孩子过家家吗?”我怒叱,“你敢到外面说吗?你敢对你妈说吗?”
“你那么想我结婚?你心里难道没有一点留恋吗?”她哽咽……
“实话告诉你,我就是想你抓紧结婚,好了结这段孽缘!好回学校。你想想,自从我们认识,出了多少事?产生了多少悲伤?影响了我多少学习?我已经受够了!是的,没有一丝留恋……”我冷冷地说。
“你说慌,坏……”她站起来说。
“没办法,我的坏是天生的……”
“难道一直是我在自作多情吗?”
她嘴哆嗦着,眼光犀利,在寻找答案。
我把头转向一边,避开那目光,点头说:“是!”。
“好个—是!”她弯下腰,捂着胸口。
我们陷入了沉默……
她直起腰后,脸上恢复了往日的笑容。
“好,你喜欢的话,我就打扮给你看!不过有个条件……”
“什么?”
“在化妆前,我要再给你留个记号!”她左右晃动着,媚眼朦胧地向我走来。
“妈呀,你这是要让我毁容啊!”我忙捂住嘴,连连后退。
她笑了:“逗你玩的!”
“记住:以后,这种玩笑不能再开了!”我严肃地说。
“抓紧吧,大家都等着你的惊艳亮相呢!”
她走出屋,美着实惊艳了众人,说“惊为天人”,一点也不为过。可能是女人在做新娘的时候,是一生中最美的。真神奇,那种特有的美只有在婚礼当天绽放!
甄一圣这天笑容很美,虽然不是源自内心的。她像个悲伤的演员戴着笑的面具表演着喜剧。大家都沾了喜气,沉浸在幸福快乐之中。而只有她和我在内心狠狠地咀嚼着忧伤……
她和妈妈告别,泪在笑容下面狂泻如瀑。
那泪是感恩的泪,感恩妈妈生育之恩;那泪是离别的泪,即将告别魂牵梦绕的家,去往一个陌生的地方;那泪是深爱妈妈的泪……
天下有哪个女孩出嫁,离家时,不是哭得撕心裂肺呢?!多年贮存的泪从心海决堤……那画面,不忍直视,使旁观者揪心!
她脑子里,想着妈妈的好、含辛茹苦的付出……
想着女儿强大了要报妈恩,但是至今未做到;
一直认为以后尽孝有的是时间,然而,机会却转瞬即逝;
想着自己曾任性犯错,不知多少次伤了妈妈的心……
过去的时光,没有向妈妈
说一句:我爱您!
说一句:您辛苦了!
说一句:对不起!
甚至没有陪妈妈好好
谈一次心,
吃一顿饭,
散一次步,
看一场电影,
唱一首歌……
妈妈美丽的黑发全染上了霜,脸像干瘪的老树皮布满了皱纹,暴瘦的身躯像轻飘飘的影子……
从此以后,再也不能长久陪伴在妈妈身边了……
我费了好大劲,才将她和妈妈分开。
她歇斯底里地喊着“妈妈……”
“多美的新娘啊!别哭了,把脸弄花了,可就成了八怪了!”我说。
“慢些走,我想多呆一会。”
“那好,不准哭!”
“我不哭,你也不准哭!”她用手小心地擦着我的泪。
“其实,我…我心里不想走…不想离开…不想离开你…”
“我知道…”
“……”
在我把她的手放到艾乾手里的那一刻,她忽然转过头,痛苦地说:“光火,我…,真的走了…”
“啪啪啪啪……噢噢噢噢……”鞭炮声、欢呼声响起来,我们已听不清楚……
那晚,我发现了被搁置多年的一坛白酒。
它寂寞地立于墙角,覆满了尘……
无人嗅它的香;
无人尝它的甜;
无人品它的苦;
无人嚼它的狂;
无人想它的痴;
无人在意它的非凡……
我举起它,
像膜拜圣物,
豪饮,
我咀嚼着离别,
舔噬着回忆……
那个黄昏飘雨的窗外;
那个贫瘠的黄土地;
被犁耙拉弯了的父亲的瘠梁;
母亲渴望的双眼……
酒精
在我破碎的心上,
在我寸断的肝肠上,
狂舞……
我醉了,
醉成了那坛沉寂多年的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