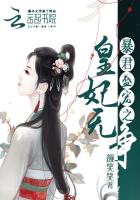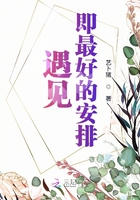大仲马不是说过“莎士比亚是上帝之后创造得最多的一个人”吗?把这句话转赠给巴尔扎克更为恰当;一个人的头脑能创造出这样多活生生的人物,的确从来还没有过。
从那个时期起,巴尔扎克拟定了“人间喜剧”的计划,他对自己的天才也有了充分的认识。他巧妙地把他已经出版的作品和他的中心思想联系起来,并把它们安插在根据哲理划分出来的类别中。虽然某些纯粹空想的中篇小说加上了挂钩仍没有联系得很好,但这不过是一些细节,在无限辽阔的整体中是看不见它们的痕迹的,有如一些风格迥异的装饰失落在一座宏伟的建筑中一样。
我们说过,巴尔扎克辛勤地劳动着,他像是顽强的铸铁匠,把不合规格的产品十次、十二次重新投入炉中;他也许像倍尔那·巴里西那样把木器、地板甚至椽子都烧掉,为了让窑里的火不致熄灭,试验不致中断;即使在极困苦的日子里,他也决不草率从事,随便把作品拿出来;这种虚心对待文学的态度留下了不少值得赞美的榜样。他一次又一次修改,改得几乎等于同一主题的另一本书,而改排的费用书店老板却记在巴尔扎克的账上,从版税里扣除;他那与作品的价值和劳动的艰苦比起来已经是微乎其微的酬劳,也就因此更加减少。他所预期的款项常常不够偿还宿债,为了要应付他笑着说的这些“流水账”,他便发挥惊人的才思紧张地工作着,这种工作也许要占据一个普通人的全部时间。但是当他穿着教士所穿的袍子坐在案头的时候,正是夜阑人静,配着绿色罩子的七支蜡烛组成的灯照在洁白的纸张上,他忘记了一切拿起笔来,于是一个比雅各和天使的斗争还要可怕的斗争开始了,我说的是形式与内容的斗争。
他每晚作战,到了早上总是精疲力竭,但他胜利了;夜里炉火熄灭以后,房间里很冷,他脸上冒着热气,身体上冒着肉眼可以看见的轻雾,像从冬天的马身上散发出来的一样。有时仅只一个句子就花去整夜的时间;他写了又改,剪裁、琢磨、推敲和增删,把这个句子写成上百种样式。奇怪的是:那需求的完善的形式,总是在列举种种似是而非的形式之后才会发现。不错,熔铁往往一下子迸射出来反倒较为细密匀称,但是在巴尔扎克的作品中却很少有几页和初稿相同。
他绞尽脑汁,认真写作,由于他超人的意志,加上勇士的气魄和教士一般深居简出的生活,因而他著作等身。每当他从事一部重要的著作,一天24小时内他要工作16到18小时,接连两三个月不停;他只匀出6小时的时间来满足动物本能的睡眠要求,倒下就睡,却又心惊肉跳,这是由于吃得匆忙,消化不良的缘故。在这些日子里,他不露一面,就是知己朋友也不知道他的去向;但是不久他从地下钻了出来,高高地举起一本杰作,笑声洪亮,十分天真地为自己喝彩;他并不要人家赞美,不过人家的赞美他也接受。没有一个作家像他那样,丝毫不关心别人如何评论和推荐他的作品。他要自自然然地扬名于世,不用一点手段,也从来不拉拢新闻记者——何况这种举动还得糟蹋他的时间。他交付稿件,拿了稿费飞也似的跑去还给债主,这些债主往往就在报馆院子里等候着,譬如,举个例子吧,替他在若尔第乡盖房子的泥水匠就是这样。
有时候,他一清早便来找我们,上气不接下气,被新鲜空气弄得有些眩晕,十分疲乏,就像从冶铁场里跑出来的铁匠之神乌尔根,一进来就跌坐在沙发上;他因为工作了整整一个长夜,肚子饿了;他把沙丁鱼捣碎后和黄油搅在一起调制成酱,抹在面包上,这种酱使他回忆起都尔城的特产:肉羔。他最爱吃这个东西;吃完就睡,叫我们一小时后唤醒他。我们没有听他的吩咐,反而尊重他的如此难得的酣睡,所以不让屋子里有一些声响。巴尔扎克一觉醒来,只见天色已暗,将近黄昏,他连忙跳起来,破口大骂,骂我们混蛋、小偷、凶手;我们害他损失了一万法郎,因为要是他早些醒来,他会想好一部新小说的内容,这部小说就能替他带来上述这个数字(再版税还不计算在内)。我们闯了大祸,造成了不可想象的紊乱。我们害他耽误了他和银行家、书店老板、公爵夫人的约会;害他不能如期还清债务;这一次要命的睡眠害他遭受到上百万法郎的损失。但是巴尔扎克这种像输了钱加倍下赌注似的夸大的计算法,从绝小的数目开始,漫无边际地增加到成为最庞大的款项,那是我们司空见惯的,所以,当我们看见都尔城的人红润的颜色又出现在睡足以后的他的面颊上,我们心里也就很容易地得到了安慰。
科莱特(1873~1945)法国作家。其代表作有《西多》、《姬姬》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