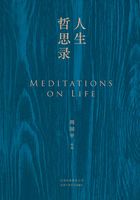(节译Cleveland Moffett所作《今世女界第一人物》,原文见美国《莫克鲁尔月报》一九一七年二月号)
今世最有名望之妇女为谁?其能以心的力量,与精神的感化力,及其事业之成功,使其自身为世界中一最有趣味之妇女者为谁?质言之,今世女界中堪称第一人物者为谁?吾苟持此问题,集全世界人而为一总投票,结果殆必马丹撒喇倍儿那(Madame Sarah Bemhardt)当选无疑。
马丹之名,举世无不知者,即远至亚洲非洲,亦称道弗衰。亦或简称其字曰撒拉,则犹拿破仑亚历山大辈之只须称以族姓,不必更举其字也。
马丹在本国时,以嚣俄(Victor Hugo)之怀才自负,目无余人,而一见所演《吕勃拉》(Ruy Bias),是剧即嚣俄所编,言西班牙皇宫中,有一仆役与皇后相爱,惧皇帝问罪,杀之,又自杀以全皇后之名誉。竟不惜屈膝其前,榄[揽]其手而亲之以吻。
其至外国京城时,魔力之大,直如上国君主下临属国。帝王也,而屈尊兀坐于包厢之中,为之鼓掌;皇后也,而手执玫瑰之花球,对舞台而遥掷;钻石之宝星,则一赠再赠;皇室之车马汽船,则有专差承候,供其随时乘用。
在伦敦时,首相格兰斯敦(Gladstone)曾躬诣其宅,与论《菲特儿》(Pbèdre)Racine所作。一剧之情节。威尔斯亲王及王妃,且自远道归来,一亲颜色。
在纽约时,大发明家爱迪生(Edison)谢客久矣,闻其至,则色然喜曰:“此拿破仑以后一人也,吾不可以不见。”乃为开一夜会,且大演电术以示敬意。以下四节半,详述马丹在美国各处演剧时大受欢迎状况,并详记所得金钱之数,均琐屑不必译。惟记其在纽约演《茶花女》一剧,第三幕毕,叫幕十七次;全剧告终,叫幕二十九次;出剧场时,迟于门外,欲与握手者,多至五万人。又总计在美国演剧,凡一百五十六次,得资五十三万三千五百二十金,平均每次三千余金,在世界演剧史中,均为从古未有之成绩云。
马丹老矣,而精神犹健,似决不愿以衰老二字,自杀其成功之志望,尝谓“已得胜利,乃过去之事实,不足道。吾惟努力前进,期时时有一新胜利见于吾前,吾意乃慰。”故通常女伶,一至暮年,即销声匿迹,不复与世人相见,日惟衣宽大之衣,倦坐安乐椅中,手抚椅柄,对炉中熊熊活火作微笑,似谓此中有无限佳趣。马丹则视暮年与妙龄无殊,当一九〇九年,渠风尘仆仆,往还欧美二洲之间,得资可数百万法郎,时年已六十有四矣,然犹是英气扑人眉宇,一火花四射之明星也。
去年马丹至美,某报派一少年记者往见之,出一亲笔署名册向乞真迹留作纪念,讫,问曰:“马丹对于此次大战,作何观念?”马丹微笑曰:“先生以为余当作何观念?”曰:“吾不知。”马丹曰:“吾亦不自知。”少停,记者又问曰:“马丹预料大战何时可了?”马丹亦曰:“先生预料大战何时可了?”记者曰:“吾不知。”马丹曰:“吾亦不知。”于是二人默然相对。记者自知无可再问,即起立告辞曰:“马丹再会。”马丹笑送之门,曰:“先生再会。”记者出,弹指自叩其脑曰:“好奇怪。”马丹则回问其书记曰:“他说些什么!”
去冬十月,马丹离美之前,演一新编之战剧,以为临别纪念;余幸亦列座。此剧情节,乃一法国少年掌旗军官亲语马丹,而马丹据实制为剧本者。余见舞台之上,残阳衰草之中,此七十一岁之老女杰,自饰少年军官,当其弹丸贯胸,血流遍体,犹手抱三色国旗而疾走,至力竭仆地,乃发其最后之呼声曰:“英吉利万岁!法兰西万岁!”而手中尚紧抱国旗勿舍。嗟乎!此景此情,吾知五十年后,凡曾于是日到院观剧之人,犹必洒其老泪,呼子若孙而语之曰:“吾于某年某月某日之夕,目睹此垂死之少年军官也。”
全剧科白,以演绎“耶稣在喀尔伐里(Calvary)之祈祷”喀尔伐里乃耶路撒冷附近之一小山,即耶稣受刑处。一节为最佳;其于“渠等明知而故犯,望勿赦其罪”(Neles pardonnezpas:IIs savent ce quils font)一语,凡三易其辞,今直录之,愿读者瞑目一想:
“渠等背弃誓言,欲以人血染历史,毁我寺院,戮我子弟,乱我妇女。天主!渠等明知而故犯,望勿赦其罪。”
“渠等违背条约,阻止人道之进行。如有小弱之国,宁死勿辱,出全力以自卫者,渠等亦弥增其暴力以摧灭之,即尽歼其人民,亦所勿顾。天主!渠等明知而故犯,望勿赦其罪。”
“天主!长夜将过,愿汝于天明之后,勿更以爱惠加诸渠等,而令其永受苦恼,倍于吾等所受;愿汝以不疲不息之手痛扑之;愿汝以永流不息,永拭不干之眼泪渥其身。天主!渠等明知而故犯,望勿赦其罪。”(原文每节之下,均有评语,今删去。)
马丹在美时,余候至四日之久,始能见于旅馆中,谈话可一小时。然余甚以为幸,因求见马丹者,日必数百人,马丹按次延见,往往有候至十数日,而谈话不过数分钟者。此下删去原文十四行,均言其延见宾客忙碌之状。既相见,余即问曰:“马丹,吾知人生所能供给之物,凡荣誉愉快爱情三者,殆已为马丹一人享尽。今马丹于艺术界与女界之中,均为不世出之怪杰,见人所不能见,为人所不能为,享人所不能享,直欲使世上一切大人先生,相率罗拜于马丹足下,而……”言未已,马丹即笑问曰:“君言信耶?”余曰:“如何勿信?此非鄙见独然,知马丹者均作是言也。然以所罗门之尊荣富贵,犹言‘世事空虚,人生如幻。生乎斯世,无非劳苦其灵魂,览一失望之终局。’不知马丹亦有此观念否?”马丹曰:“此言吾决不能信,吾知人生为一真实之事,且为一值得经过之事。吾年虽老,犹日日竭吾智力,于此真实不虚之生命中,自求其日新月异之趣味。因吾知吾人只有一个生命,有此现成之生命而放弃之,而欲于意想中另求一不可必得之生命者,妄也。”余闻言大奇,以马丹为旧教信徒,此种思想,实与教义大背。因问曰:“如马丹言,彼宗教家谓吾人于现有之肉体生命外,将来更有一灵魂生命,其言不足信矣。”曰:“然,吾不信此说。”曰:“吾人尽此肉体生命之力量,果能满足吾辈之欲望,而使其全无缺陷否,此亦一问题也。”马丹曰:“欲解决此问题,不必问人,但须问己。吾以为吾人意志中之大隐力,实神怪不可思议,倘能运用之,发达之,则吾辈体中,人人各有其梦想所不及之能力在。吾人事业之成功与否,与夫心之所羡,身之所乐之果能如愿与否,胥可与此种能力决之。”此下删去原文二十余行,乃无关紧要之谈话。
余又问:“马丹对于‘死的问题’有何见解?”马丹曰:“余认定‘人生’为‘乐趣’之代名词,故乐趣消失之日,即为身死之日。去年二月,余右足发一巨疽,以行动不能自由为苦。谋诸医生,医生曰:‘用手术去此足,代以木足,则术恙,否则疽即愈,此足终不能复动。’余即促其施术,时余子在侧,涕泣言:‘母年高,不能当此。施术不慎,是以性命为儿戏。不施术,即痪,亦何害。’余曰:‘施术不慎固死,痪亦何异于死;同一死也,而施术可以未必死,何阻为?’今吾右足已易木足,行动无殊于往时。吾于致谢医者之神术而外,更当自谢其见识与决心。否则今日之日,吾已为一淹滞病榻之陈死人,朝朝暮暮,惟有哭出许多眼泪,向废足挥洒而已。”
马丹于来美之前数月,曾至法国战壕中演剧六次,余叩以当时情况何若,答言:“此为吾毕生最悲惨之经历,亦为吾毕生最愉快之事业。吾在巴黎及各大都市演剧,虽承观者不弃,奖誉有加,要其爱我之诚,终莫此辈可怜之前敌兵士若。吾于是发生一种观念,以为我之技术,用于它处仅为普通之感化与慰藉,用于战壕之中,乃始有接触人类灵魂之意味。”
余问:“马丹年事日增,何以精力不损?”马丹笑曰:“吾亦不自知其所以然。即与吾相习之医者,亦言‘他人终有衰老之日,独此媪弗尔。察其体质,初无过人处,此诚咄咄怪事。’然吾仔细思索,知吾今日之不老,实种根于九岁时。尔时吾为小学生,一日,与一表弟同作跳沟之戏,失慎落沟中,伤臂流血,父兄辈咸戒余后此不可复跳。余曰:‘否,无论如何,余必跳。’后校中比赛运动,余以优胜,应得奖品,先生问余何欲,余曰:‘余不喜实物之奖品,但愿先生书无论如何四[字]予之可矣。’先生不解,告以故,则喜曰:‘此子可教,’遂取素笺,书‘无论如何尔终胜’数字,以作奖品。自是以后,吾数十年来刻刻不忘者,即此数字。故年达七十,犹日必骑马行数里,或击网球一二小时。至去年断足以后,始改习较柔软之室内运动,然仍按日练习,无论如何不肯中辍。吾老而不衰,其理或在斯乎。”夫以一七十一岁之老嬷,年齿与吾辈之祖母若曾祖母等,又折其一足,而犹能秉承“无论如何”之教训,实行其身体锻炼,试问此等人当今有几。
马丹一生行事,无时不有“无论如何”之观念。某年,渠在法兰西戏院演剧,余适与同寓。时天气温和,常人咸衣单薄之衣,而马丹犹御皮服,似其寒疾已深,然仍每夕登台,未尝因病辍演。又有一次,时在马丹中年,渠患肺病,尚于每夕演剧之外,精修雕刻之术。有问其何必自苦至此者,马丹曰:“吾身上有病,心中无病,病其奈我何?吾晨以八时起,骑马至郊外吸清气,自十时始,即独居一堂,治雕刻术;有时脑昏欲晕,弗顾也。”又有一次,乃马丹受伦敦某剧院之聘,准备登台之第一夕;妆已上矣,忽病发,晕扑于后台化妆室者凡三次,而绣幕既启,马丹依旧登场,观者均大满意而去。凡此所述,马丹自谓得力于“无论如何”四字,余则因以制成一定理曰:“人心万能。”此节原文共四节二十九行,兹仅节译大意。
去冬马丹至美,甫离“西班牙”号船,纽约各日报各杂志记者,已群集旅馆中候之。尔时天甫破晓,马丹睡眠未足,又已在大西洋狂风巨浪中颠簸多日,其劳瘁可不待言。乃一入旅馆厅事,见记者辈方骈坐以待,即整顿精神,与谈此次航海西来情事,清言娓娓,历数小时不倦,惟命侍者取鲜葡萄少许及牛乳一杯,以润枯吻。记者辈乃欢喜出望外,各出铅笔小册,乘其啖葡萄饮牛乳时疾书之。马丹所言,以十月八日事为最有趣。渠谓“是日为星期,船主于晨间接得一无线警电,言‘昨晚已有商轮六艘,为德国潜艇轰却,君船当严为戒备。’于是船上执事者大忙,尽出救生之物分发乘众,且放下救生艇,俾一有警耗,即可登艇。而搭客之纷扰,尤不可名状。余思戒备固当,纷扰胡为者,即商诸船主,假会食处演剧娱客;所得剧资,概由船主代收,捐充红十字会经费。搭客闻此消息,无不转惊为喜,纷纷纳资购票。余乃在此死神临顶之关头,仍抱吾‘无论如何’之素志,尽出吾技以娱嘉宾。而德国潜艇竟幸而未至,彼无数搭客之无限恐慌,亦竟为吾之‘无论如何’轻轻抹过。”
余问:“马丹嗓音清越,历久不坏,亦有保护之法否?”马丹曰:“嗓音好坏,本属天然。然保护不力,天分虽佳,中年以后无不倒嗓者。余护嗓之法,首在不束胸以害肺,次则保持呼吸之平均,使肺中恒有充分之清鲜空气。至于饮食,余恒主宁少勿多,肉类尤非所嗜,然此与全体卫生有关,不仅肺喉二部也。”
马丹演剧,得资极多,然性好挥霍,金钱到手辄尽。余因问其对于财产之观念。渠谓:“金钱与财产,实不能成为问题,吾苟需钱,但须演剧数月,即可得五六十万法郎。倘斤斤于居积,费却许多精神,转使可以化作适合人生之乐趣之金钱,居于绝对无用之地,自己凭空添出无限不适人生之烦恼,宁非大愚。”余曰:“马丹以须钱之故,乃肯认真演剧;倘不必作事,而每年能有数百万法郎之入款,马丹将安坐而食耶?抑仍认真演剧耶?”曰:“吾人作事,倘必有金钱驱策于其后,则其人必为一不知人生真趣之蠢物。然使果如君言,吾虽仍以劳动为乐,却只愿以一小部分之精力从事演剧,而以一大部分从事于雕刻与绘画,因雕刻绘画,事业较演剧略高,而成绩之流传于世间者,其时间也较为久远。故就实际言,吾以演剧为业,非出于中心之抉择,实为生活所驱策也。”余曰:“愿马丹恕我此问:马丹于雕刻绘画二事,亦如演剧之性质相近否?”曰:“比演剧尤近。”乃历举其成绩,谓一八七七年,制一图曰“阵雨之后”,经法国巴黎沙龙给予优等奖;后二年,又以云马石刻此图,形较小,鬻于伦敦,得价二千金;又有油画一幅,绘一妙龄女郎,手持棕榈数枝,独立作微笑状,英国莱顿勋士(Sir Frederick Leighton)盛称之,后为比国李奥朴特亲王(Prince Leopold)购去。以上三节,原文共一百五十余行,兹仅译其大意。
普法战争之后,各处盛传马丹拒绝德皇事,谓“德皇欲延马丹至柏林演剧,马丹谢曰:‘德皇,吾仇也,吾奈何以吾技娱吾仇?渠能举阿尔萨斯归吾法兰西者,仇立释;仇释,吾明日至柏林矣。’使者往还数次,马丹坚执其言,终不成议。”余问此说完全可信否,马丹曰:“此中尚有传闻失实处。初,吾欲至阿尔萨斯演剧,德人以邀吾先至柏林演剧为交换条件,商量至数年之久,余终不许。后余以甚念阿尔萨斯州人,必欲一至其地,即自甘退让,先至柏林。在柏林开演数日之后,忽德皇使人来言,欲亲至院中观剧,余以坚决之辞谢使者曰:‘为我代白凯撒,渠倘能以阿尔萨斯一州为吾演剧之代价,则如命。否则渠自前门入院,吾即自后门而逃,幸毋责我以大杀风景也。’德皇知余终不可强,果未至。又有一次,时在普法战争十年之后,余在哥本哈给(Copenhagen)演剧,一风度翩翩之德国大使,每日遣人以鲜花赠余,余一一却之。至演剧完毕之日,渠又开一极盛之夜宴会,为吾饯行。余觉情不可却,应约往,则在坐陪席者,均一时巨官贵妇。宴将毕,此不知趣之大使,举杯起立,高声言曰:‘吾为此多才多艺之法国大女伶祝福,兼祝产此美人之法兰西!’余以其语意轻薄,立即报以冷语曰:‘愿君为吾法兰西全体祝福,普鲁士大使先生!’于是宾主不欢而散。次晨五时许,余尚未起,忽为喧扰声惊醒,披衣出视,乃有德官一人,自称毕士麦之代表,声热汹汹,欲强余至大使馆谢罪。余冷笑曰:‘速去,毋扰吾睡!有话可叫毕士麦或凯撒自己来说,谁与汝喋喋者!’德官无奈我何,竟沮丧去。”余笑曰:“如马丹言,马丹殆善闹脾气者。”马丹曰:“然。余生平不肯让人,遇不如意事,每易发怒。昔小仲马作《lEtrangere》一剧,备吾演唱,既成,忽以剧名失之过激,有更改意。余闻而大怒,造其室,痛骂之,谓‘汝敢易去一字母者,吾必与汝决斗!汝既摇笔为文,尚欲忘却本心,为敷衍他人地耶?’时仲马亦不肯退让,二人挥拳抵几,呶呶然出恶言互詈;争执达半日,各至力竭气喘,不能更发一言而罢。而剧名卒未改。此下删去原文一百三十余行,所记均起居琐事。”
马丹恒自称为小儿。数年前,十月二十三日,为其六十七岁寿辰,渠谓贺者曰:“诸公可取果饵来,且可亲我之吻。我已往所过六十年,今已不算,只从一岁重新算起。诸公对此七岁之老小儿,理当啖以果饵而亲其吻也。”贺者见其风趣如此,果如所言。
马丹之哲学思想,谓“无论何时何世,人类决不能各得其真正之适宜,因世间奇才异能之士,往往处于为人所用之低地位,而无丝毫之权力;其有权力以用之者,卒为全无才能之蠢物。是才能与权力,永远不能相遇,即永远不能得其适宜。质言之,凡有奇才异能者,都出其才能以为他人之奴隶,而换得区区一饱之代价。此种现象,无论政体社会有何变更,非至世界消灭之日不止。”
余问马丹对于战争之意见,其答语曰:“战争为吾毕生最恨之名词,是为邪慝与耻辱与惨痛之混合物。凡一切盗窍与罪恶,一入战争时代,即可一概赦免,不复认为恶事,又从而提倡之,力行之,使为人类无上之光荣焉!”
余问对人之道如何,马丹曰:“人生苦短,即臻上寿,亦决不能与全世界之人类一一接触。故吾辈对人当分二种,其能与吾辈接触之一小部分,即与吾辈生直接之爱恶关系者,吾辈可自审其爱恶之合于正义与否,而以相当之道待之。易言之,吾辈之生命,大半当消长于此等人之中也。其与吾辈不相接触之一大部分,无论善恶苦乐,均是路人,对待之法,只须牢记‘恕而不忘’一语,多爱少恨而已。”
马丹曰:“余生平有一不肯抛弃希望不肯失却胆量之信念,无论何等难事,余必与对面为敌;无论何等重任,余必竭力担承之。”
余有一友,尝问马丹“人生最重要者是何事物?”其答语为“是工作与爱。能爱人,能爱生命,能爱工作,则君可永远不老。吾爱人,吾乃为人所爱。吾工作无已时,故吾年七十有一而犹为少年。”
六月三日,江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