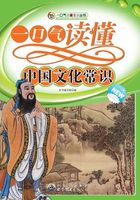整个傍晚就这样度过去,黑夜来临了。那个医师去睡觉了。姑姑们躺下安歇了。涅赫柳多夫知道马特廖娜·帕夫洛夫娜目前在姑姑们的卧室里,只有卡秋莎一个人待在女仆房间里。他就又走出去,在门廊上站住。门外漆黑,潮湿,温暖。整个空中弥漫着白茫茫的大雾,在春天,这样的雾消融着残雪,或者正是因为残雪在融化,才升起了这样的雾。正房前边,百步开外,在陡坡底下有一条河,传来一种奇怪的响声:那是冰层在碎裂。
涅赫柳多夫从门廊上走下去,踩着结了冰的雪走过泥塘,来到女仆房间的窗子跟前。他的心在胸膛里跳得那么响,他自己都听见了。他时而屏住呼吸,时而费力地深深吐一口气。女仆房间里点着一盏小灯。卡秋莎独自坐在桌旁,正在沉思,眼睛呆望着前面。涅赫柳多夫一动不动地瞧了她很久,想看一下她自以为没有人瞧着她的时候会做些什么。有两分钟光景,她坐在那儿不动,然后抬起眼睛来,微微一笑,仿佛责备自己似的摇一摇头,然后变换一个姿势,把两条胳膊猛地往桌上一放,呆呆地望着前面。
他站在那儿瞧着她,不由自主地听着他自己的心跳声和从河上传来的古怪的响声。那边,在河上,在雾里,正在进行一种不停的、缓慢的工作,不知是一个什么东西时而呼哧呼哧地喘气,时而咔嚓一声裂开,时而哗啦一声倒下来,时而薄冰像玻璃似的碰得玎玲玎玲地响。
他站在那儿,瞧着卡秋莎的心事重重的、由于内心斗争而苦恼的脸。他不由得怜惜她,然而,说来奇怪,这种怜惜反而加强了他对她的欲念。
这种欲念已经完全控制住他。
他敲敲窗子。她仿佛触了电似的,全身一震,脸上露出害怕的神情。然后她跳起来,走到窗前,把她的脸凑近窗玻璃。甚至在她伸出两个手掌,像护眼罩似的放在她的眼睛两旁,然后认出他的时候,那害怕的神情也仍旧没有离开她的脸。她的脸色异常严肃,他以前从没见过她的脸像这个样子。直到他微微一笑,她也才微微一笑,而且仿佛只是为了迎合他才微笑的,她心里并没有笑意,而只有恐惧。他对她招手示意,要她到院子里来找他。可是她摇头,意思是说不,她不出去。她仍旧站在窗子那儿不动。他再一次把他的脸凑近窗玻璃,想对她喊一声,叫她出来,可是这时候她回过头去看房门口,分明有人在叫她。涅赫柳多夫就从窗子跟前走开了。雾那么浓,离开房子只有五步远就看不见窗子,只有黑糊糊的一大堆东西,从中照出一片似乎很大的红色灯光。河上仍旧发出奇怪的喘气声、窸窣声、爆裂声、冰块相碰的玎玲声。院子里,不远的地方,在迷雾中,有一只公鸡啼起来,附近就有别的公鸡接应,随后远处村子里传来互相打岔而又合成一片的鸡鸣声。四下里,除了那条河以外,十分肃静。这时候已经是第二遍鸡叫了。
涅赫柳多夫在房子的墙角那儿来回走了两趟,有好几次把脚踩进泥塘里去,后来又走到女仆房间的窗子跟前。灯仍旧点着,卡秋莎又独自一个人靠着桌子坐定,好像心里七上八下拿不定主意似的。他刚刚走到窗子跟前,她就瞧他一眼。他敲了敲窗子。她也没细看是谁在敲窗子,就立刻从女仆房间里跑出去。他听见门扣咔地一响,然后外边的房门吱吱扭扭地开了。这时候他已经在门道的旁边等她,一句话也没说,立刻伸出胳膊去搂住她。她偎紧他,扬起她的头,用她的嘴唇去迎接他的吻。他们站在门道的一个墙角后边,那儿的雪已经化掉,土地是干的。他周身充满一种煎熬着他的、没有得到满足的欲望。忽然,外边的房门又咔地一响,又吱吱扭扭地开了,传来马特廖娜·帕夫洛夫娜生气的声音:
“卡秋莎!”
她抽身离开他,回到女仆房间里去。他听见门扣一声响,扣上了。这以后一切都归于沉寂,窗子里的红光不见了,只剩下大雾和河上的闹声。
涅赫柳多夫往窗子跟前走过去,然而什么人也没看见。他敲窗子,也没有人应声。涅赫柳多夫绕到前门的门廊上,走回正房里去,可是睡不着觉。他就脱掉靴子,光着脚,顺着过道往她的房门口走过去,她的房间同马特廖娜·帕夫洛夫娜的房间紧挨着。起初他听见马特廖娜·帕夫洛夫娜发出平稳的鼾声。他正想往前走,忽然马特廖娜·帕夫洛夫娜咳嗽起来,翻了个身,她的床吱吱嘎嘎地响。他的心停住跳动,他呆站了大约五分钟。等到一切又沉寂下来,平稳的鼾声又响起来,他就极力把他的脚踩在不嘎吱嘎吱响的地板上,往前走去,来到她的房门口。任什么声音也听不见。她分明没有睡着,因为她的呼吸声听不到。他刚刚压低喉咙叫一声“卡秋莎”,她就跳下床,走到房门口来,劝他走掉,她的声调依他听来仿佛在生气似的。
“这像什么话?哎,怎么可以这样?您的姑姑会听见的,”她嘴上这样说着,而她的全身却在说:“我整个都是属于你的。”
只有这句话涅赫柳多夫才听明白了。
“得了,你开一忽儿门吧。我求求你,”他说着这些毫无意义的话。
她不出声,然后他听见一只手摸索着找门扣的声音。门扣咔地一响,他就顺着推开的门缝溜进去。
这时候她穿着又粗又硬的布内衣,裸露着胳膊;他抓住她,抱起她来,把她带走。
“哎呀!您这是干什么呀?”她小声说。
可是他不理睬她的话,把她抱到他自己的房间里去。
“哎,别这样,放开我吧,”她说,可是她的身子更偎紧他了。
等到她周身发抖,一声不响,也不答理他说的话,从他那儿走掉了,他就走出去,来到门廊上,站住不动,极力思索刚才发生的这件事的意义。
外边亮得多了。下边,河面上,冰块的崩裂声、磕碰声、喘息声越发响起来,而且在原有的各种响声之外,还添上了流水的潺潺声。大雾开始往下降,下弦月从雾幕后面升起来,朦胧地照着一个乌黑而可怕的什么东西。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所遇到的究竟是很大的幸福呢,还是很大的不幸?”他问自己。“这种事是素来就有的,大家都是这样做的,”他对自己说,然后就回去睡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