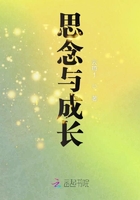钟叔和钟婶儿愣在那里不知道如何是好,他俩冷的直打哆嗦,迫切地需要回去取取暖,或者喝点热水暖暖肚子。他俩很清楚,这个时候去问薛老喜是没有用的,他会用生硬的口气说这是康队长叫他们这样做的,或者说那些地方就是公家的,谁想建什么就建什么。
去问康大功,他俩的心里都有点害怕,这种害怕是从斗地主那时候产生的,几十年来,他们都不敢多给康大功说话,更不用说去求他办事了。
先前村里有人告诉钟叔和钟婶儿,意思是说让她去求求康大功批一个宅基地,盖不动房子就搭个草棚子,那样也会亮敞许多,总比在那潮湿的坑儿里要强。
钟叔和钟婶儿只是听听,他们很有自己的主意,从来没有过要去求康大功的想法,她知道去了的结果是什么。
“他爹,你看·····”,钟婶儿对钟叔说,她的语气和表情里是满满的歉意,似乎要向钟叔表明,这一切都是因为自己造成的。
钟叔好长时间没有吱声,他在农村都是被人为认为是那种不好事的人,好人,没有本事的人,他的性格里大部分都是逆来顺受的成分。
“你去功家见见功吧,咱这车子都进不了家了”,钟叔说。
钟婶儿沉默了一下,说:“也中,咱先回家喝汤,然后再去”,钟婶儿知道钟叔是怕他那辆架子车被人偷跑了,那个年代,闺女寻婆子家,家里有没有架子车,便是衡量婆子家富裕不富裕的一个因素。
钟叔把架子车的拉带拴在离家门最近的那颗杨树上,两个人便回了家。
喝汤的时候,两个人都不说一句话,好像都在有意延长喝汤的时间。
放下碗,钟叔对钟婶儿说:“他娘,不去吧,就是去了今儿黑了车子也拉不到家,我就睡在那车子上,等天明了再说”。
钟婶儿默认了钟叔的办法,拿了一个口袋片和一条被子,在那架子车上铺好,她知道那架子车上睡着可冷,但她又知道,如果那架子车丢了,他会心疼死的。
······
第二天天还不亮,苏家屯村子里便回荡着雪玉梅凄惨的哭声,当人们循声来到这里的时候,看见雪玉梅扑在那辆架子车上痛哭
苏小钟不知道什么时候都死在车子上了,不知道是冻死的还是饿死的,不知道是气死的还是害怕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