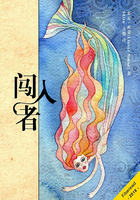“这首歌……这个旋律……我们是不是在哪儿听过?”一直沉默的沙耶加突然打断了骆川。
她这么一说,倒是提醒了我,M在迷失之海里那个神秘的祭坛上,唱的似乎也是这首歌!虽然M没有用霍皮语,但旋律和意思都是一样的。当时救人要紧,我并没有仔细思考这首歌,现在想起来,迷失之海和骆川所说的这片遗迹果然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同样的石头,一样的歌谣,不同寻常的暴雨……
“尼莫是印第安土著,M也有印第安血统,这该不是巧合吧?”迪克提出另一点相似。
“堪萨斯州和亚利桑那州都是在中部,彼此之间相隔并不遥远,M和尼莫会不会祖上都是一个族的?”
“可是M打小就和她妈妈离开了阿什利镇啊……”
“你别忘了,她跟霍克斯生活过一段时间,也许是她爷爷教她唱的呢?”
“还有,M的大脑本身就跟我们不同,她的记忆系统比普通人更复杂,或者这首歌也是她那些看不见的‘朋友’告诉她的,就像它们带领她进入迷失之海的祭坛一样。”
“可修建这些庞大遗迹的目的是什么呢?这些石头又有什么作用?”
“它们是‘入口’的标识。”骆川幽幽地说。
骆川一行人又朝里走了半小时,阳光已经彻底被遮挡住了,周围开始变得阴冷。没人知道遗迹还有多深,三只手电筒在石壁之间乱晃着,所到之处只能看见扬起的灰尘。
“唔——”舒月发出了一声痛苦的呻吟。
“你怎么了?”
“我头好疼……”她使劲按着突突跳的太阳穴,明显体力不支,“我听到什么声音,在我脑子里……好像是动物的叫声,还有一些奇怪的语言……”
这土妞怕是有密闭空间恐惧症,有的人在幽暗的空间里待久了就会产生某种幻觉。骆川想着,瞅了一眼走在前面的埃伦,这家伙完全不在意他俩的生死,更别说会在意舒月难不难受了。按这样发展,即使后面他们遇到什么危险,埃伦见死不救也是极有可能的。
往里面走和回到山谷都他妈是死路一条,骆川第八百次在心里懊恼着,被土著拿弓箭射死和在遗迹里当炮灰,没有哪个比另一个更好些。
“这里没有声音。”骆川搀扶着舒月安慰道。
“别唱了,”埃伦不耐烦地用枪托朝尼莫的后脑打了一下,“一定是因为你该死的歌声。唱什么唱,嫌死得不够快吗?”
“呵。”尼莫非但没怕,还发出一声轻蔑的笑声。
“看来你非要挨个枪子才会消停,红皮猪。”埃伦说完就朝尼莫的脚边开了一枪,顿时尘土飞扬,刺耳的枪声差点没震破骆川的耳膜。
“银项链”倏地趴在地上,一边跪拜一边念念有词。
“你想干什么?给我起来!”
埃伦一脚踹在“银项链”宽厚的背上,可他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继续跪在地上。
“让他给我起来!继续走!”埃伦向尼莫挥动着手里的枪,叫得歇斯底里,温文儒雅的教授形象早已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癫狂的探险家。
“你触犯了他的信仰。”尼莫歪着嘴,他的手被捆着。可骆川觉得他自始至终就没害怕过挨子弹,他对埃伦没有一丝一毫忌惮,反而像是一个故意惹恼大人的小滑头,露出奸计得逞的微笑。
这很危险。骆川咽了咽口水,却一时想不出里面的门道。
“即便只是身单力薄的血肉之躯,在这个地方,我们也会得到万物之灵的庇佑。这里没有恐惧,只有古老的神祇、原始的力量,伴随着我对你们永生永世的诅咒,愿蛇神像拧断鸟儿脖子一样拧断你的……”
“给我住口!你这个蛮化未开的红皮猪!”
“是的,无论再融合多少年,社区比邻,接受同样的学校教育,你们伪善的笑容下面,仍然把我们当成茹毛饮血、偏居蛮荒之地的野人。你们不相信我们的信仰,不相信郊狼和鹰堆起山脊创造了世界,不相信大神米查波孕育了人类,不相信滥杀生灵就不会再得到守护神鹿的帮助,也不相信把羽毛织成的网子挂在床头就能过滤噩梦。你们只相信电视和网络上的养生广告,靠着一堆金属器械能治疗疾病,每天一个生鸡蛋治疗阳痿;相信电视上口若悬河的政治候选人,购买名牌让生活变得优质,绿色的废纸和存折里的数字支配着你们的快乐和痛苦——我为你们感到悲哀,你们失去神的同时也失去了他的眷顾,你们早成了没有灵魂的躯壳,最后只能在泥土里腐朽……”
“乒!”
埃伦一枪打在“银项链”的腿上,对方晃了一下,仍然跪在地上,一动不动。
“你给我起来!”埃伦辱骂着,又朝他的手臂上开了一枪。
“够了!”骆川颤抖着挡在“银项链”的面前,“再打下去他就死了!”
“你他妈的给我滚开!”埃伦把枪顶在骆川的脑门上,“滚开!”
“你到底要干什么?”舒月双手握着手里的枪转向埃伦吼道,“你在杀人!”
“这些红皮猪,杀了我们的人,还带着我们在这里绕圈子!”
“骆川是我们的一员,是你的学生啊!”
三个人,就这样僵持着。
“冷静点,埃伦,放下枪好吗?”过了一会儿,舒月努力使自己的声音平缓下来。
骆川脑门上的枪口终于移开。埃伦就像一下子苍老了十岁,他靠着墙叹了一口气。
“他们在作弄我们,这里根本没有什么入口。”
“你错了,我们早就到祭坛的‘入口’了。”尼莫干笑了两声,指着不远处一块黑暗的地方。
骆川拿手电筒照过去,那是一面墙,却和其他墙面的材质不一样。它由一些奇怪的石头垒成,每块石头上都刻着若隐若现的文字。
“你想诓我们?这儿明明没有入口,连路都没有!”埃伦骂道。
“你为什么不凑近看看呢?”尼莫边说边朝前走去。
“我就是在那面墙上,看到它们的。”骆川看着餐桌上的石头,若有所思。
我们几个这才从骆川离奇的经历中回过神来。
骆川所去的遗迹和迷失之海并不相似,可两个地方都出现过这种奇怪的石头。这其中有什么联系呢?
“达尔文说,印第安人是没有文字的。”我沉吟道,“你确定这些石头上刻着的是文字吗?”
“我不但确定,而且我几乎立刻认出那些文字是甲骨文,汉字最早期的形式,在商朝以前就存在了。”
“甲骨文?”我不可思议地看着这些石头。
“是的,甲骨文,因为这是一种象形文字,单个辨认很容易把它当成普通的图案。可我在那个遗迹里看到的是一面墙,当它们有序地排列在一起的时候就很好辨认了。”
“所以你的意思是,在商周之前,中华大地就有人把那些甲骨文带到了美洲?”
骆川点点头。
“可是,这不科学啊,几千年前的人根本没办法横渡太平洋,他们产生文明的时间即使比历史记载得更早,也不可能有如此发达的航海技术……”
“当时我跟你们想得一样,我还和舒月做出了各种猜想,包括巨大的风浪把南粤沿海一带的渔船刮到了太平洋群岛,又在夏季因西北风被刮到美洲大陆……可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些假设都是错的。”
“那他们从哪儿来?”
“从地底来。”
埃伦已经走到石墙边了,他的步履有些蹒跚,拿着枪的手早已垂下来,就像完全忘记了后面还有两个印第安俘虏,另一只手则把帽子缓缓地摘了下来,露出一头半秃的银发,就像某种庄重的仪式。
骆川从来没在埃伦教授脸上见过这种表情,这让他想起了去年在拉斯维加斯的赌桌上,那个借了巨额高利贷孤注一掷的赌徒。那是一种近乎绝望的贪婪,就像沙漠里迷路的人看见水,经历饥荒的人看见食物。
“这些甲骨文……”埃伦念念有词,“真的存在……阿格哈塔真的存在!”
骆川想不明白,究竟是什么能让一个老教授如此痴迷。他刚想伸手摸一下面前的石头,舒月拉住他的手臂:“别碰!”
“怎么了?”
“我不知道,我觉得不对劲……”
“快告诉我!怎么开启这面石墙?”舒月还没说完,就被埃伦狂喜的声音打断了,“是机关还是咒语?让我进去!”
“你真想知道?”尼莫向前走了两步,猫着腰笑道。
“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钱吗?支票吗……”埃伦语无伦次了。
“我只想要一样东西……”尼莫突然猛地向前一冲,用身体使劲把埃伦向后撞去!
“你的命!”
埃伦一下子就被撞得几个趔趄,朝石壁倒去。
骆川还没有来得及惊呼,奇迹发生了—
那面石墙,忽然荡漾起一阵水波,埃伦就像掉进了湖里一样融进了墙面,一瞬间就消失了。
“这是怎么回事……”
舒月刚想抬起枪,只见地上中枪的“银项链”一跃而起,抬起手一拳打到舒月的头上。舒月向后摔倒,也坠入了石壁。
着了他们的道了!他们根本不是“被迫”带我们来到这里,而是巴不得我们来,当成祭品推下去!骆川瞬间反应过来,下意识地一把揪住尼莫:“我死你也要陪葬!”
眼前一黑。
这一切都是个梦。骆川迷迷糊糊地对自己说。
他想起八岁的某一天,他喜欢的那个邻居女孩一脚把他踹到了村口的水塘里。水面的冰还没有完全融化,弥漫着一种尿液和死鱼的味道。他挣扎着不让自己沉下去,可包裹他的池水冰冷又刺骨,他大叫着,却只看到岸上的她和另外几个大男孩指着自己笑出了声。后来他被路过的村民救了起来,生了一场两个月的伤寒,从此那种彻骨的寒冷再也没有消失过,他在每个夜里都打着哆嗦惊醒,肉体和灵魂都下意识地寻找温暖的地方。
后来他凭着优异的成绩离开了终年潮湿阴冷的滇山之南,到了城市,又到了美国。他喜欢马萨诸塞州夏季的干燥和炎热,白天在海滩上晒着太阳,晚上则拥着不一样的身躯入睡,那些女孩把温热和躁动传进他的体内。
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以为他身体里的寒冷早就被融化了,可这一刻,它们肆意占据他的每个毛孔,那种该死的感觉又回来了。
这会不会只是我的幻觉?人怎么可能从一面石墙穿过去呢?
可鼻腔里灌入的液体让骆川剧烈地咳嗽起来,他费劲地睁开眼睛,坐了起来。
他不知道自己在哪儿,准确来说,他看不清楚。这里很暗,可视距离大约是一米,四周笼罩着稀薄的白色雾气。
骆川看了看脚下,他正坐在一摊墨黑色的积水里,虽然水很浅,只没过他的脚背,但散发着一股无法形容的臭味,就像是几十年没维护过的下水管道一样。
这是真的,这不是做梦。
骆川的心狂跳起来,他摊开手掌,里面有半块撕裂的布料,他认出来那是尼莫的格子上衣。
从上一次到现在,自己有多少年没这么臭过了?骆川被熏得只想呕吐,他一边朝前走了几步,一边四周环顾着叫:“有人吗?舒月?埃伦?”
“咚。”一声很轻的响声,如果不仔细听几乎分辨不出来。
骆川隐隐约约看到,前面的水面上,绽出一片半径至少有十米的巨大圆形涟漪。
“谁在那里?”骆川喊道。可没有人回答他。
“咚。”又是一片涟漪。
骆川揉了揉眼睛,这圈涟漪,明显不是靠一块小石头能制造出的,这波纹更大更广,如果是在任何一个普通的湖或者池塘里,骆川都会认为涟漪之下有条非常大的鱼——可这里水深不过几寸,怎么会有大型生物呢?
骆川迅速脑补了一堆看过的恐怖电影,《天外魔花》《异形》……他周末的时候会开车去露天影院,他喜欢姑娘们尖叫着闭上眼睛扑进他怀里,他从来没觉得这些电影里面的怪物有多么可怕,有时候甚至觉得可笑,因为他知道那是假的,是树脂和硅胶的混合物制成的面具。可是在这一刻,他之前欠下的恐惧一次翻了几千倍报应在他头上。
人对黑暗有着本能的恐惧,就像兔子惧怕豺狼、麋鹿惧怕猎人,因为你永远不知道黑暗中有什么,你越拼命看,越是什么都看不见,可你就能感觉到,有什么在盯着你,在或远或近的地方观察着你、觊觎着你,趁你不经意的时候给你致命的一击。
骆川胡思乱想着,脚底突然被什么绊了一下。
虽然光线很暗,但骆川仍然看清了那是衬衫的纹路。
是柯林斯,那个失踪的地质学家!此刻他正面朝下趴在水里。
“哥们儿?”骆川蹲下身的一瞬间就后悔了——柯林斯被翻过来的脸已经成了一坨凹进去的肉酱,混杂着黑色的泥水,只剩一颗眼球耷拉在旁边。
骆川吓坏了,他想站起来,腰包却被柯林斯的上衣钩住了,他俩以一种很奇怪的姿势一起“站”了起来。骆川突然觉得柯林斯的身体很轻,他下意识地向下看去,才发现对方的下半段身体没有了,连带消失的,还有肠子和内脏。
那创口,就像是被什么猛兽一口咬掉半个身子,连骨盆也咬得粉碎。
骆川想不到陆地上有哪种野兽能制造这种创伤,事实上他现在根本无法思考。他猛地把柯林斯的身体甩到水里——他知道这样做对死人来说很过分,但他忍不住,然后他捂住嘴巴干呕起来。
他想叫,歇斯底里地大叫,可理智告诉他声音或许会引来不好的东西,它会一口咬掉他的大腿,再给他一个跟柯林斯一样的结局。
他摸索着衣服口袋,裤子里有一个硬硬的东西,那是他的银制Zippo打火机。
骆川不喜欢抽烟,他有时候甚至讨厌烟味,但他喜欢这个花哨的小东西,男人唯一可以拥有的几件装饰品之一。
他颤抖着掏出打火机,刚想打燃,一个熟悉的声音突然制止了他:“别犯傻!这里充满沼气,任何火星都能导致爆炸。”
是埃伦。
眼睛逐渐习惯了昏暗,视力变得清晰起来,前面的黑水里慢慢出现了一些不同年份的白骨。骆川勉强辨认着,有肋骨、大腿骨……唯独没有看见头骨。骆川终于明白了,他在遗迹里看到的那些头颅的躯干去了哪里。骨头渐渐堆起了一个小坡,埃伦坐在坡上,他旁边的白骨上,歪歪地靠着昏过去的舒月。
“舒月!”骆川扶起舒月,她仍昏迷着,但呼吸、心跳都还正常。骆川摸到她头上有伤,估计是摔下来的时候跌到的,伤口还在流血,他马上撕下一只袖子简单为她包扎了一下。
“这他妈的是哪里?”骆川一边包一边问。
埃伦看起来更苍老了,他极力控制着呼吸,但仍喘着大气。此刻,他的脸上写满了疑惑和不解。
“这里什么都没有,不应该呀……一定是哪里出错了……”埃伦喃喃地说。
“这里应该有什么?”
“不应该……和资料不一样……”
“到底是什么资料?!你给我说清楚!”
骆川终于发怒了。他一直尽力做一个彬彬有礼的人,他对很多事情都满不在乎,因而他几乎从不发怒。可是现在再不说清楚,连命都没了。
“喀喀,我知道这里有什么。”黑暗中,另一个声音幽幽地说。
骆川才发现他们的不远处,尼莫半趴在地上,他的手仍然被捆着,左臂形成一个非常扭曲的姿势,应该是掉下来的时候受力不均匀导致骨折了。
“把我扶起来好吗?”
骆川犹豫了一下,看了眼埃伦,像征询他的意见。可埃伦丝毫没有反应,仍皱着眉头想着什么。骆川只好蹚水过去,把尼莫拽起来。尼莫哼了一声,骆川才发现他的大腿也骨折了。
“我知道这里有什么,也知道它在哪里。但你要帮我一个忙。”
“你又想怎么样?”
“我的项链在T恤里,我掉下来的时候,链坠跑到背上去了。你能帮我把它捋顺,弄出来吗?”
骆川不知道尼莫想干什么,但这听起来并不是一个太过分的要求。
骆川把手伸进尼莫的后背T恤里,掏了两下,就摸到了一个吊坠,跟“银项链”的吊坠一模一样,是一根银制的长羽毛,大约有一根小拇指长。
尼莫抬起被绑住的双手,用没断的手抚摸着吊坠。
“这不是鹰的羽毛,它属于印第安蛇神。蛇神披着羽毛,能在地上游走,能在天空飞……它就生活在这里,从世界混沌之初它就存在于这里,等待着我们的祭献……”
“它在哪儿?”骆川一边问,一边捡起了舒月手边的枪。可他环顾四周,除了一片薄雾之外,一无所获。
“它就在这里,在我身边,可是你看不见它,只有被选中的人才能看见它……”
埃伦听到这句话,忽然抖了一下。
“我现在没空跟你扯你的那些见鬼的信仰,我们究竟怎么才能出去?”
骆川还没说完,就被埃伦打断了,神采再一次回到他苍老的眼睛里:“你能看见?你真的能看见?上帝保佑,我没选错人,告诉我它在哪儿?阿格哈塔的入口在哪儿……”
“没有人能到得了,也没有人能够出得去……”尼莫狞笑着,他突然举起羽毛链坠,一下插进了脖子里!
鲜血瞬间喷涌而出。
“所有人……都……祭献……”尼莫还没说完就倒了下去,链坠捅穿了他的大动脉。
骆川吓傻了,他从没想过一个链坠也能用来自杀。
血腥味蔓延开来,骆川似乎看见不远处的雾气动了一下,可他揉了揉眼睛又没了。
“好像,有什么在雾里……”骆川话音未落,突然尼莫的身体腾空而起!
就在骆川前方不到五米处,浓雾集结在一起裹住了尼莫,就这么短短一秒,他的身体重重地摔回了地面。
准确来说,是小半个身体。
尼莫的胸腔以下到大腿外侧,被某种尖锐的牙齿咬掉了很大一块,胰脏和小肠流了出来,流进黑水里。胸腔的起伏表明尼莫的心脏还在跳动,他还没死绝。
让骆川感到深深恐惧的,是尼莫脸上的表情。
他仍旧在笑。
跑!
骆川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
骆川抱着舒月一路狂奔,四周除了淡淡的白雾之外没有任何标志性的东西,他不知道自己该跑到哪儿去,也不知道自己在逃离什么。
他喘着气,一遍又一遍地回忆着尼莫被抛向空中又坠落,和他身上诡异的伤口——他无比确定他除了薄雾之外,什么都没看到。
就像是空气吃了尼莫,但他身上的咬痕是动物造成的。
难道那是一种会隐形的生物?
周围只有水花溅起的声音,骆川上气不接下气,他的手臂又酸又累,腿也开始抽筋。舒月说得没错,这个地方不正常,除了环境之外还有气压——他的耳朵嗡嗡地响起来,就像飞机降落前一样,脑袋涨得下一秒就能爆炸。
“等等我……等等……”埃伦也跑不动了,他一个踉跄跌坐在黑水里,剧烈地咳嗽起来。
骆川看向他的身后,除了雾,什么都没有。
“别丢下我……”
“你知道这他妈的是什么地方……”骆川已经到崩溃的边缘,他看着埃伦,语无伦次地说,“我没兴趣知道你那些龌龊的目的,但你知道这地方有入口,就一定知道出口,你知道怎么离开这个鬼地方,对不对?”
埃伦咳得两颊通红,他没说话,只是摇了摇头。
“中情局不可能没告诉你,臭老头!他们一定给了你资料,出口在哪里?现在说出来我还能把你带出去,我不管你为什么要到这里来,我没义务陪你殉葬!”
骆川边说边抬起脚,想把这个害了整个科考队的人踢飞,尽管眼前这个虚弱的老头,哪怕是一个耳光都可能要了他的命。
意料之外,骆川还没碰到埃伦,他竟然咳出了一口鲜血。
“我活不长了……”埃伦喘着气,抹了抹嘴角,“两个月前的诊断,呵,肺癌晚期。”
骆川的脚僵在半空中,他被埃伦的话搞得有点不知所措。
“很讽刺,是吗……”埃伦喘着粗气,他极力想让自己的声音平缓下来,“我知道癌症有可能会遗传,我的母亲是胃癌,舅舅也是胃癌。我从二十岁起就严格控制饮食,只喝清水,我参加有机蔬菜食疗,用西芹和玉米榨汁喝,四十多年的素食者,每年的胃肠镜复查,再加上一堆又一堆的保健品,天知道我遭了多少罪……可笑的是,我成功地避开了胃癌,癌细胞却出现在我的肺里……我从不抽烟,甚至连厨房都很少进,可医生发现的时候,它们已经向淋巴扩散了……”
“所以你想在你被癌症弄死之前干一票大的,让全世界都认识你?”骆川深吸一口气。
“不。”埃伦疲倦地摇了摇头,“你……你们在来的路上不是一直问我,到底在找什么吗?”
骆川点了点头。
“永生。”埃伦抬起头,混浊的眼睛看着骆川,“我不想死。”
“你说……你在找什么?”
骆川怀疑自己听错了,他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这个麻省理工学院的老教授。这位上过无数次专业杂志,可以被称为考古界泰斗的学者,竟然会相信三流科幻小说里才有的东西。
他更不敢相信的是,埃伦为了这么荒谬的追求,搭上了他们科考队几乎所有人的性命。
这太可笑了!
“我知道你不相信,你以为我疯了……起初我也不信,”埃伦又咳出了一口血,“中情局告诉我的时候,我和你的表情一样……可他们给我看了一些东西,一些二战时破译的解密文件和照片。纳粹在纳木托寻找阿格哈塔的地下王国,传说中的香巴拉秘境,原来并不是互联网上以讹传讹的奇闻逸事,它真的存在……他们找到了它的入口,地下王国的大门曾一度向他们打开。他们在那里目睹了早已灭绝的史前生物,和人类之前的辉煌文明……他们甚至带回了那里面居住的智能物种……它们比人类进化得更超前,基因更优良,那种生物身上有永生的秘密……”
“你在放屁!”骆川的声音颤抖着,“你,他娘的,在放屁!”
“我明白,单凭这些资料和照片也不足以让人信服。我是一个经历过二战的人,我知道中情局的这些人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即使伪造资料也轻而易举,直到,直到……”艾伦的脸上浮现出一丝狂喜,“他们带我去见了另一个癌症患者,他已经被医生宣告物理性死亡,当我见到他时,他的心跳已经停止了……可当那个中情局的人从口袋里掏出一颗蓝色的胶囊塞进他嘴里时,他的心跳在几分钟之内恢复了跳动!”埃伦的眼睛里绽放出希望的光芒。
“那种药的成分,就是从这里的智慧物种身上提炼出来的。”
“他们甚至还向我展示了一个孩子……至少他看起来是孩子,但他从1940年活到了现在,一直是八九岁的样子,他不但没死,还一点都没有衰老!”
“你的话简直是漏洞百出——你说在纳木托发现了香巴拉的入口,你知道我们现在在哪里吗?我不知道是你糊涂了还是我疯了,这两个地方隔着十万八千里,你不会想告诉我地球是空心的,这两个地方就像下水道一样彼此相连吧?好吧,即使我们假设这一切都成立,假设中情局已经掌握了你说的那个什么……生物的永生技术,还研究出了药物。”骆川摆摆手,“你让他们把药直接给你就好了,你为什么还要来这个地方?”
“拿菲利……他们称呼那种生物为拿菲利,《圣经》里拥有半神血统的巨人……”埃伦纠正道,他的眼神迅速黯淡下来,刚刚涌现出来的希望瞬间熄灭了,“可是那种药物并不完美,它的副作用远远比它的药效大。目前服用药物的人,最后都变成了怪物……我宁愿死也不愿意变成那种怪物!所以我一定要再次进来,我要比之前的人都更深入这个地方,我要找到比拿菲利更完美的永生物种!”
“先生,我再说一次,这里是亚利桑那州边境的峡谷地区,地球不是空心的,你没办法从地底穿去喜马拉雅山脉,纳木托只能坐飞机去!这里没有你的狗屁永生物种和史前王国,这里只有他妈的不知道哪里来的雾和狗日的吃人野兽!”
薄雾里回荡着骆川愤怒的声音,随即而来的是一阵沉默。
“以罗、耶和华、亚杜乃、弥赛亚、迦南神、伊利昂、以爱俄兰……”埃伦自言自语地沉吟着。
骆川盯着眼前这个垂死的老头。
“这些都是神的名字……《圣经》里的耶稣,为世人所知的就有七个名字,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称呼都不一样——他最早自称为迦南神,可在以色列人面前被唤作耶和华,巴比伦时期的人又称他为以罗……神有很多个名字,无论他走到哪里,出现在哪个时代,被称为什么,神本身的能力都是永恒不变的,变的只是时间、地点和一代又一代的人。”
“你究竟想说什么?”
埃伦看了骆川一眼,从腰间解下了自己的水壶——那是一只钢化玻璃材质的圆柱形水壶。里面的水几乎没喝,埃伦把它放在手上轻轻地转动,透过玻璃,只见里面的气泡随着水位的变化而从瓶口移动到瓶底。
“香巴拉就像这个气泡一样,它一直在地幔里移动,和耶和华一样,它在不同的时代和地点所拥有的名字都不同——它出现在纳木托地下的时候叫香巴拉,在玛雅文明的历史里被称为安莎儿,在欧洲的时候又被人们称为亚特兰蒂斯……无论它的名字变成什么,它都是同一样东西,都是同一个地方。”
“气泡……我们现在身处在某个存在于地幔中的气泡里?”
埃伦点了点头:“香巴拉,也可以称为阿格哈塔,没人知道它是什么时候出现的,也许是在这颗星球形成的时候就存在了。这座地下城市总是没有规律地出现在世界各处,没人能计算出它的运行速度和方位,那是非常庞大的计算量,目前人类的科技是无法算出来的……历史上踏足这里的人全凭运气,我们也不例外……要不是这次突然的地震导致这个遗迹暴露出来,我就算穷其一生都无法找到它。”
“我……”骆川还想说点什么,突然感觉到怀里的舒月动了动。
舒月捂着头痛苦地哼了一声:“我们这是在哪儿……”
“别动,你的头受伤了……”骆川刚想跟她解释,舒月眯着的眼睛突然瞪圆了,她几乎是尖叫着跳起来:
“这是……这里是哪里?怎么会有热带雨林……”
骆川惊讶地顺着舒月的视线看过去,可除了深不见底的白色雾气之外,什么都没有。
“热带雨林?”
“你……你也能看见?!”埃伦语无伦次地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