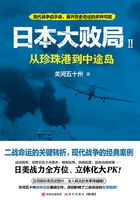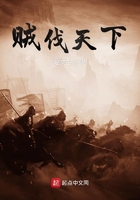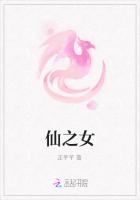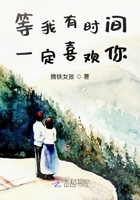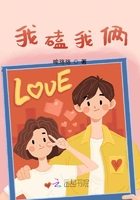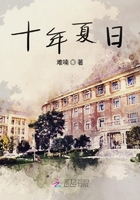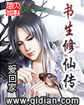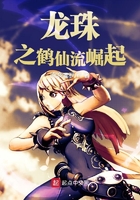文官不爱钱,武将不惜死。
这句似乎是南宋时期的谚语,在今天的早朝上得到了全新的诠释。
新平堡、嘉峪关二地守将轻率挑衅边境冲突,让朱由检不得不让节制边镇的巡抚加以严厉监督,严防此类事变的发生。
今天早朝刚开始时,朝臣们还是按部就班的讨论朝政。不久后,户科给事中韩一良出班:“陛下,臣有本启奏。”
“准。”
韩一良一开口就满朝震惊:“臣记得陛下曾在朝会时说过“文官不爱钱”这么一句话,但臣认为这话不对。如今的朝廷,哪个地方不是用钱的地方,哪个官员不是爱钱的官员。陛下只知道文官爱钱,但是否知道文官是不得不爱钱呢?”
韩一良停顿了一下,满朝大臣无人出声,就继续说下去:
“文官晋升都是用钱才能晋升的,升官后也只有爱钱才能填饱为升官借来的银钱亏空。向以钱进,必以钱偿,就是这个道理。内选、外选、升选,只有行贿才能被选中,不行贿就不能被选中。吏部筛选是如此风气,科道筛选、馆选等也是如此之风。
一说贪污,个个都指责府州县守令贪污,让小民误以为是。但府州县守令都是要迎来送往的,请问他们的俸禄能有多少?上司来到当地索取,理由不是‘不妨碍官银征缴数额’,就是‘填补往年积欠’。官吏出使在外,路过当地,就必须要拜访当地官员。但拜访当地官员,就必须要出书仪作为见面礼;要是遇到考满、朝见的时候,就是带上满车的金银,心里还是担忧被追责。
但官吏行贿的钱,不是天上掉下来,也不是地上长出来的,都是民脂民膏。今天的形势,让人想要做一个清廉的君子都不能,更多人只能是随波逐流了。臣建议只有抓捕几个贪赃数目巨大的官员,才能让天下的臣子把钱看作是污秽、把钱看作是罪魁祸首。只有这样,陛下期望的文官不爱钱风气才能到来。”
吏部尚书王永光出列请罪:“臣无能,不能制止部下受贿纳款,请陛下惩罚。”
朱由检开始本来只是觉得韩一良只是在危言耸听,后面越听就觉得越严重——吏部铨选官吏,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府、州、县三级守令都是直接面对普通百姓的官员,他们的能力和品格,直接关系到朝廷施政和百姓生活品质。
军队没有好的将领,就会吃败仗。府、州、县守令能力不好、品德差,受苦的就是当地百姓,也让朝廷税赋受到影响。
府、州、县守令是天下治理的关键,也是朱由检进行改革的基础。这是一件要严肃认真考虑的事情。
朱由检于是对王永光说:“先不说什么罪不罪,再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你来说说吏部是如何进行铨选的?”
“谢陛下宽容。吏部铨选由文选司负责,选择的对象有三类人,分别是进士、举人贡生、吏员,即所谓三途。
京官六部主事、中书、行人、评事、博士,外官知州、推官、知县,都是从进士中挑选。外官推官、知县及学官,从举人、贡生中挑选。京官五府、六部首领官,通政司、太常、光禄寺、詹事府等府属官,从官荫生中挑选。州、县佐贰,都、布、按三司首领官等幕僚,从监生中挑选。外府、外卫、盐运司首领官,中外杂职、入流未入流官等吏员,从吏员、承差中挑选。
内阁大学士、各部尚书等官职,由廷推或奉特旨产生。各部侍郎以下及祭酒等官职,由吏部会同三品以上京官共同廷推。太常卿以下,六部部推。通政、参政以下官职,由吏部在弘政门会选。詹事由内阁推选,各衙门人员由各掌印任命。
在外省的官职,惟都督、巡抚是由廷推、九卿参与而产生外,其余官职,包括知府、知州、知县等官职,都是吏部选定。”
朱由检说:“也就是说,进士出身,做官能升最高;举人次之,吏员就最低了。朕记得太祖皇帝驾驭奉天门选官,就谕令选官不得拘于资格,由才能者即可就任。当时就有人立即被授予侍郎官职。也不存在这个官进士能做,举人、贡生就不能做的说法。如今三途各有发展,拘于资格出身和年资,是否是违反当年太祖时的谕令呢?”
王永光:“陛下,这从何说起~~~~~吏部历来都是如此做法,至于为何太祖时是如此做法,而如今又是如此做法,臣实在是不清楚。”
来宗道出班:“陛下,吏部铨选之所以讲究资格、年历,原因大致有二,一是彰显身份,奖励荣耀,二是看得见、摸得着,其他不好操作。如果不限定三途,如进士能做的官,举人也能做,那殿试还有荣耀吗?三元及第出身,和举人出身一样,状元还有什么意义?如吏员能做进士、举人的官,那科举还能激励人心吗?”
来宗道刚刚说完,很多朝臣都附和来宗道。
朱由检就明白了,进士途、举人途、吏员图的做官限制,更多的是出于面子和官员利益,而非国家利益。
“首辅说的也在理。科举激励人心、选拔人才还是很重要的。”
朱由检话锋一转,说:“但科举只能是决定起点,不能决定终点。进士出身,就意味着初授官职高;举人出身,就意味着初授官职比进士低;吏员出身,初授官职最低。这样的做法是合理的,不需要改动。但升迁考核是,就不能限定进士、举人、吏员出身资格和年资,吏部在升迁考核时,不得以出身资格挑选,或否定,有违犯者一律罢职严惩。朕记得,隆庆年间,大学生高拱就在奏疏上说:
‘国初,举人跻八座为名臣者甚众。后乃进士偏重,而举人甚轻,至于今极矣。请自授官以后,惟考政绩,不问其出身。’
既然太祖时期举人成为朝廷重臣,如何今天就不能了呢?这是我们必须遵守的祖制——唯才是举!
内阁散朝后马上拟旨:自今之后,初授官员按照进士、举人、吏员三途各有高低不同,以示激励和荣耀;升迁考核,惟问政绩,不问出身,尤其是府、州、县守令、总兵、副将、参将、游记、巡抚、都督等军事民治官职的调任、升迁,必须要以政绩为依据。”
辅臣孙承宗出列:“陛下,所言甚是。举人中也是有能力卓越的。刑部员外郎陈新甲、辽南巡抚孙元化、山北巡抚茅元仪三人都是举人出身,能力都众所周知。进士中有能人,举人中也有能人,不管进士,还是举人,都是科举出身,不应该区分彼此。”
王永光作为吏部尚书,尤其担心:
“陛下所言,臣不敢不遵照执行。但大明两京一十三省,140府、193州、1138县,合计1472个,以每个3个官员计算,就是4476个官职,还不算监、司官吏人数。如此庞大的官职,臣怕是吏部人手有限,就算终日忙碌,也难以完成考核。尤其是以政绩考核,吏部就需要人手了解待考核官员的政绩资料。”
朱由检一听,就明显有撂挑子的意思,就有点动怒了:
“吏部就负责州府县守令的考核,就算加上监、司人数,就算6000个官职。知府、知州、知县等主事者5年考核一次,其余非主事者3年考核一次。吏部人手再有限,每日考核5人,每月考核150人总是可以的,一年就考核1800人。进入考核名单的官员以担任职位年资最长、年资虽不长但有卓异治理政绩为准进行考核。年资最长是按资历,政绩卓越是按能力,以此每年挑选待考核官吏,每年考核1800人,三年即可考核完成6000人,如此以来,还有什么不能完成的?”
王永广大是尴尬,大汗淋漓:
“臣蠢钝,还是陛下圣明。”
朱由检不理他,继续说下去:
“既然说到这里,朕就继续说下去。布政使、知府、知州、知县都是治民之官,负责民政。其政绩指标如下:
所辖区域人口户数增减、钱粮税赋完缴、田亩数和农户数是否平衡、衙门官司案件是否积累、民间官声清廉与否。
辖区人口户数增减,不以人口增减数字为准,因为各地人口人数不同,只能以增减成数为考核依据。钱粮税赋完缴,主要看是否如期完缴、多征少征,不如期完缴、多征收,甚至私下摊派,不经向上申请同意而少征,都为不能提升,甚至要降职。
田亩数增加而耕种农户不增加,说明田亩都是豪族占地为多,无地之民就多,而豪族侵占农户之田就越多,这也说明辖区官员不为小民做主,就考核不合格,不能晋升,严重的要降职,甚至罢职勘问。而朝廷就要迁移当地的无地之民迁移到地多人少的府、州、县。衙门官司累积,说明官员懒政。当地官声,是小民对官员的最直接评价。
吏部考核官吏时,除吏部亲自派员前往查访外,可以向户部索要待考核官员的每年人口增加户数、税赋完缴情况、每年田亩和农户增加数,也可以要求东厂提供待考核官吏的的官声情况。”
朱由检连怎么操作都说出来了,王永元没有办法:
“遵旨!”
兵部左侍郎兼京戎经理李邦华出列:
“陛下,文官不爱钱问题解决了,是否应该解决武将不畏死的问题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