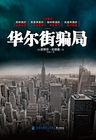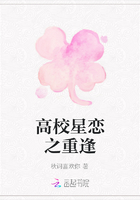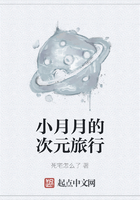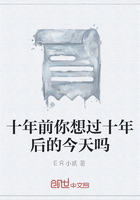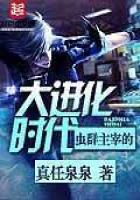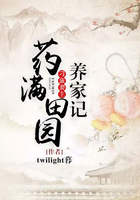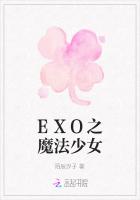随着中国商品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中国产品遭到来自世界各主要国家,尤其是欧盟和美国的倾销指控也越来越多。为了维护本国的利益,为了在世界贸易和经济中争取主动,同时为了与世界经济保持良性和谐的关系,为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中国也正在逐渐转变被动挨打的局面,对进口商品的反倾销管理工作正在得到重视。
实际上,中国的反倾销工作从1997年就已经开始。1997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颁布执行以后不久,同年12月,中国首次对进口新闻纸展开反倾销调查,并最终裁定原产于加拿大、美国和韩国的进口新闻纸属于倾销,对其征收反倾销税。随着中国反倾销实践经验的逐渐积累以及中国成功加入WTO,中国于2002年初重新制定了《反倾销条例》,作为反倾销的政府主管部门,原外经贸部和原国家经贸委也陆续颁布了一系列规章、措施。从1997年12月第一起进口反倾销案件――新闻纸案件(该起案件已于2004年6月30日得出结果,中国商务部公告对进口到我国境内原产于加拿大、韩国、美国的新闻纸继续征收反倾销税,期限5年),到2000年6月,中国已经发起了原始反倾销调查96起,被调查商品涉及到22个国家和地区(含中国台湾)的钢铁、化工、造纸等重要基础性原材料行业。
WTO的《反倾销协议》以及中国的《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和《反倾销条例》是我国在对进口产品进行反倾销调查的过程中主要遵循的立法精神,它们均要求在具备倾销、损害以及倾销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这三个基本条件的基础上,对倾销数量、对国内市场价格的影响及对国内相关产业和产品的影响进行科学、详细地审查,提供肯定性证据。
进口产品的倾销数量包括两层含义:一是调查期内进口的绝对数量;另一个是与进口国国内的生产与消费数量相比增加情况的相对数量。在我国首次新闻纸反倾销调查中,据中国海关统计,1996年,中国从加拿大、美国和韩国进口的新闻纸是中国进口总量的56.5%,而1997年,这一比例提高到61.8%,进口的绝对数量则分别为20.1万吨和28万吨。
进口产品对国内价格的影响也有两三种情况:一是进口使进口国国内市场上的同类产品价格大幅度下跌;二是进口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价格的上涨或本应该发生的价格增长。为了占领更多市场,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源自于美国、加拿大和韩国的大量新闻纸价格一降再降,这三国的新闻纸价格降幅分别高达15.3%、10.8%和7.8%,这使得国内9家新闻纸生产厂家的新闻纸价格逐渐下降。
衡量进口产品对国内相关产业的影响需要考虑很多的因素,包括产量、销售、市场份额利润……生产率、设备利用率及投资收益的实际和潜在变化情况,以及对流动资金、库存、就业、工资、增长率、筹资能力和成本及投资能力的实际和潜在影响。1997年,全国最具代表性的9家新闻纸制造企业(吉林造纸公司、广州造纸公司、宜宾纸业股份公司、江西纸业公司、岳阳造纸公司、石砚造纸厂、齐齐哈尔造纸厂、鸭绿江造纸厂和福建南平造纸厂)开工率严重不足,生产能力大量闲置,产量急剧畏缩,减幅达20%,销售量和销售收入下降22%,利润下降,多数企业陷入了严重亏损的境地,导致国内新闻纸产业的失业率大幅度上升,就业人员的平均 水平也不断下降。
出于慎重起见,中国反倾销调查机构还对需求变化、消费模式、国内外竞争和不可抗力等其他可能影响国内新闻纸行业的因素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国内9家新闻纸企业产量的收缩与销量的下降并非起因于需求变化,1997年,国内新闻纸总需求量为105.8万吨,而1996年和1995年分别为90.3万吨和82.7万吨。而且,国内并没有替代产品,也未发生会严重影响生产企业的自然灾害等其他不可抗力因素,而惟一的可能就是在质量和性能上与国内产品具有很大形似性和可替代性的进口产品。因而可以认定,1997年国内新闻纸行业全面崩溃的导火索是进口于加拿大、美国和韩国的同类产品。
反倾销调查开始后,中国对上述三国的进口新闻纸征收9%~78%幅度不等的反倾销税,具体是对加拿大和韩国实行差别待遇,对美国则实行同等待遇,即向加拿大和韩国造纸公司征收的税率不同(加拿大豪森纸浆纸业公司为61%,雄师集团为59%,太平洋纸业公司为57%,阿维纳公司、芬利公司、森林工业公司和其他加拿大公司为78%,韩国韩松纸业公司为9%,其他韩国公司为55%),而对美国所有造纸企业则一律征收78%的反倾销税,新闻纸的价格逐渐回升,加拿大、美国和韩国的新闻纸低价倾销行为基本停止。
自从这一例中国首次反倾销调查以来,根据我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的有关规定,冷轧硅钢片产业、聚酯薄膜产业、不锈钢产业、丙烯酸酯产业、二氯甲烷产业、聚苯乙烯产业和赖氨酸盐酸盐产业、聚酯切片产业和涤纶短纤产业先后对来自日本、德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的倾销进口产品提出了反倾销调查,反倾销措施为国内同类企业和行业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生存条件,来自外界的巨大竞争压力得到了很有效地控制,国内企业生产得到好转,产品价格提高,销售量和利润明显增加,上缴税收也随之增加,为国家财政做出了贡献。
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反倾销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保护了落后,保护了低效率的生产,导致了资源的浪费和全球范围内资源的不合理配置。企业经营应该是一种市场行为,企业生存是市场优胜劣汰的自然结果,人为的干预改变了市场规律,其使用必须是有限的。如果反倾销手段被滥用,那么其对整个社会福利的损害要更大。公共利益问题是反倾销工作中必须要加以重视的一个问题。根据公共利益理论,公共政策,包括反倾销措施的制定和实施,是为了应对市场失灵,当市场出现无效时,有关政府机构可以代表相关利益方动用有关政策予以制止和纠正。WTO《倾销与反倾销协议》在公共利益问题上也作出了相应的规定,该协议第9条第1款规定充分显示了较少征税原则的含义:“在征收反倾销税的全部条件都已经满足的情况下,是否要征收反倾销税以及征收反倾销税的数额是否按照倾销幅度的全部或者小于倾销幅度,均由进口成员当局决定。本协议所有缔约成员地域内的当局都有权征收反倾销税,如果较少的征税就能足以消除对国内产业造成的损害,则最好征税额小于倾销幅度。”该协议第6条第12款还规定:“当局应向受调查产品的工业用户提供机会,如果产品通常是零售渠道出售的,还要向有代表性的消费者组织提供机会,让它们提供关于倾销、损害以及因果关系的有关调查的任何资料。”而在中国的《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中,对“公共利益”问题没有作出任何规定,这种法律上的漏洞很容易造成抗辩不足,并且未能够为上下游产业和消费者的利益权衡问题提供充分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