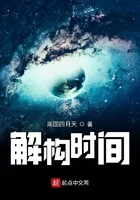1. 约会
罗小鸽出门前问他下午有什么安排,然后又责怪自己会问出这么多余的话。
“你还会有什么安排?”她不满地说。
马领说:“我有安排,我有一个约会。”
早上马领接到一个奇怪的电话,一个陌生女人约他下午三点在银座酒吧会面。
他把这些说给罗小鸽,罗小鸽不以为然地转身而去,她说:
“一个女人?要是真的如此,我倒会为你高兴的。”
马领躺在床上发呆,有一个词让他感到不安和难堪,他需要集中思想才能连贯地想出这个词的前言后语,它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句子:如果真的有某种艳遇发生,他会不会背叛罗小鸽? 而镶嵌在这个句子中的关键词是——背叛。这个词太大了,想一想就能让人顿感疲惫和厌倦。
走进西湖路上的银座酒吧,一个雍容的少妇抬手向马领打招呼。她穿一件赭石色的衬衫,头发光滑地绾在脑后,丰腴,幽雅,像一个古代的仕女。马领将信将疑地走过去,在她对面坐下。
女人替他叫了杯黑啤酒,然后自我介绍道:
“我叫唐婉。”
声音很动听,的确是电话里的那个声音。“唐琬”?马领首先想到“红酥手,黄滕酒”所描绘的那个古代女子,诗人陆游的表妹。他注意去看对方的手,它们有一只摆在桌面上,白皙,圆润,涂有丹蔻,衬托在古旧色调的桌布上,接近于诗里的描写。
“我是唐克的妹妹,”她进一步介绍道。
“你想干吗?”马领立刻变得粗鲁。
“我是替我哥哥来见你的。我哥哥和你妹妹,他们之间的事你一定知道些。”
“你直说吧,想干什么?”
“我哥哥说你是对马袖最有影响的人,他想请你劝劝马袖,重新回到他身边。”
“这简直是说胡话,你哥哥一定是个白痴。”
“不要急着拒绝好吗?”
唐婉优雅地呡口手中的红酒,相当沉着地看着他,递过来一张发黄的纸片。纸片上有蓝色墨水写出的几行字迹,十分幼稚:
妹妹,因为有了你
我开始喜爱大地上的一些事情
因为有了你
我开始能够忍受大地
“什么东西?”
“我哥哥十五岁时写给我的,他是一个诗人。”
马领心里莫名地迷濛了一下。这个唐克,他和他从未谋面,形象却一天天变得丰满:一个老家伙,有老婆孩子,瘸腿,现在居然发展成为一个诗人。
“你对我说这些有什么用?”
“他从没求过我,这次求我来见你,他真的很爱马袖。”
“这根本不可能,你劝他少异想天开,别再去招惹马袖。”
“我哥哥已经离婚了。”
“那是他老婆的幸运。”
“我以为会说服你,”唐婉看着窗外,声音仍然很从容。
“那我只有对你说——”马领努力控制,才没有让自己发出已经顶在舌尖的兰城腔儿,“错,错,错。”
一个多少令人想入非非的约会变成这种局面,使马领对今天剩下的时间感到难熬。推门离开酒吧时他就在想怎么打发这个下午。走到街上,他打电话给马袖,对方说马袖今天休息,不在银行。他只好打给家里。
“我寄了两万块钱给你。”父亲言简意赅地说,随时有挂机的可能。
“为什么?为什么寄钱给我?”
“你不是要结婚吗?”
马领愣住。
“本来可以多寄些,但我刚刚自费出了第四本书,没办法,只能寄这么多。”父亲接着叮嘱道,“你要计划着用,不要乱花!尤其不要买书,你的书太多了,买那么多书有什么用?书价现在这么贵!”然后就果断地挂机了。
马领心里想,父亲从陕北走出来,不是像毛泽东那样凭着枪杆子,完全是凭着厚厚的两册剪贴,那是他多年发表在报刊上的文字汇总。一辈子靠读书吃饭的父亲,刚刚自费出版了自己的第四本书,现在却对他说“买那么多书有什么用”。这时有人打进手机。
“干广告的,是我,李小林,我还记着你的号码。”
“你好,老婆找到了吗?”
“不急不急,我想向你咨询一下。”
“你讲。”
“上回你推荐给我的那个方式造价太昂贵,还有没有其他形式?”
“你想达到什么效果?”
“当然是范围广,密度大,最重要是得保证不易破坏。我贴出去的那些启事,很快就被人揭光啦,没有一点办法。”
“那你选择110报警牌吧。铁皮制作,指定悬挂,一半是110,一半可以上广告,五百个一组,主要悬挂在居民小区和商业街道。”
“听起来不错,什么价钱?”
“十万吧。”
“这样啊?我那种启事不太合适吧?110很严肃啊,还有没有别的?”
“那就邮政灯箱吧,一米乘一米,上面是灯箱,下面是信箱,有专人维护,可摆放在本市主要街道,一只七千。”
“这个很便宜呀!”
“但恐怕达不到你所要求的发布密度,一只七千,十只也需要投入七万。
马领机械地运算着。与唐婉会面带来的不适仍然在他的意识边缘游移,他隐约感到自己背叛了某种自己一贯暗自持有的标准,那是一种怎样的背叛呢?
“那我就要一只,只能量体裁衣,没有办法啊,就这我还得向人借。一只就一只吧,我准备把它摆在政府门口。”李小林并不气馁。
“先不要急,你先去找律师资询一下,看看这样搞会不会惹上麻烦。”
马领感到自己有些虚弱,整个人都因此变得温良起来。这让他很不适,情绪充满了毫无缘由的厌倦。
“有道理。你他妈真够哥们,改天我请你吃饭!”李小林猛不丁地质问了一句,“你怎么就不是个老板呢?”
2. 只有去公园了
马领听到有人在叫自己,是一种悲伤到无以复加的腔调,东张西望一番,却找不到。然后又听到一声,是从一辆擦身而过的黄面的上发出的。马领追了两步,黄面的似乎有意不让他找到答案,狠狠地喷出股尾气绝尘而去。后来他在路边公交车站的绿色坐椅上坐下,买了瓶汽水边喝边想:难道,那辆黄面的车轮碾过马路时,会发出“马领马领”这样的动静?
等车的人很少,只有一对男女坐在马领旁边,中间和他空着几个位子。这对男女都低垂着头,不时抬眼警惕地看看四周,然后又埋下头小声交谈。一辆公交车开过来停在站前,车门打开,但站上的三个人都不上去。司机从窗子里看他们,等待着他们上车,他的眼神并无热情,而是充满怨愤和威胁。他们坐在椅子上纹丝不动。车上几个稀稀拉拉的乘客都把脸贴在玻璃上,充满期待地看着他们。马领感到有些不好意思,不敢面对那些热切的眼睛,头低下去很认真地喝自己的汽水。司机终于失去耐心,愤怒地连揿了三声喇叭,车子晃晃悠悠地开走了。
一连过去三辆车都是这种情况。马领开始对身边这对男女发生兴趣,装作很随便地把屁股挪向他们,想坐得近一些听听他们在谈什么。男人警觉地发现了马领的企图,转头看一眼他,回身向女人使了个眼色,两人一起往开挪了一个座位,恢复了与马领原有的距离。马领当然不会甘心,又慢吞吞地挪近。他们又转移,他又跟进。这下他们无路可退了,已经坐到了最后一张椅子上。马领明显地感到了这两个人内心的不安,不觉有股几近邪恶的得意。
男人不安地扭着身子,声音微微颤抖地小声问女人:
“怎么办?快想想我们去哪里?”
由于距离近,马领终于听到了他们的对话。
女人从嗓子里挤出些声音:
“还能去哪?我们还能去哪?只有去公园了。”
马领感觉有某种可以被把握的玄机浮现了出来。他知道自己容易贸然下结论,于是仔细分析了一下这对男女:体形都具备了中年人的那种奇形怪状,小腹微微鼓突,腰和屁股浑然一体。这样一对男女坐在夏日街头鬼鬼祟祟地无处可去,说明了什么?这不是很清楚吗,能去哪,他们还能去哪?只有去公园!马领兴奋了,感觉自己不啻于掌握了一个真理。
于是,当这对男女逃跑似地冲上一辆停下的公交车时,他也敏捷地冲了上去。上车后他就后悔了,心想自己完全可以再等一辆,如此穷追不舍会给对方造成多么大的心理压力?他微微觉得有点愧对这对男女,他们站在车头,他就向车尾走去。但这种刻意的分散,已经让局面蒙上了一层斗智斗勇的气氛。售票员过来卖票,他尽量压低声音说买到公园站,没想到售票员响亮地报告道,公园站五角!马领自己都被吓住,前面那对男女当然更是慌乱,一起回头看他。马领只好把脸背过去。
下车后马领克制住迫不急待的心情,尽量让自己走得慢一些,心里不断地安慰他们,忍一忍,再忍一忍,进了公园我们就各分东西。但他们还是忍不住了,这对男女突然停下脚步,马领看到那个男人气势汹汹地转身向自己走来,走到面前,却勉强地微笑起来,露出一口小得出奇的牙齿。马领从没见到过一个成年人长着这样玲珑的牙齿。
“哥们,帮帮忙好吧?不要跟着我们了好吧?”中年男人讨好地笑着说。
马领觉得被他称作“哥们”很滑稽,说道:
“哥们,你不要误会,我也是去公园,我也没地方可去,你们走你们的,我走我的。”
中年男人半信半疑地说:“大路朝天?”
马领叹了口气,只得配合地回答:“各走一边。”
他就满意地走了,在转身的一霎那又换上了一副雄赳赳的样子,昂首挺胸地走向他的女人,在她身后一点儿时,悄悄摸出皮夹子盘点了一下自己的本钱。
进到公园他们就如约分散行动,马领和中年男人交换了纯属男人这个物种的短短的一瞥。他迫不及待地沿着湖边前进,但是临近目标时步子却犹疑起来,像一个在湖边想不开的危险青年。终于看到柳树下的那个茶摊了,一个枯瘦的老哥趴在冰柜上打盹,一排竹躺椅横七竖八地摆放着,其中一张上面端坐着一个小女孩,头戴一顶翻边太阳帽,两只脚在空中不安分地踢来踢去,但不妨碍她聚精会神地阅读手中的画书。
一切一如往昔,似乎时间在这里也无能为力。
马领把自己隐藏在一棵柳树背后,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