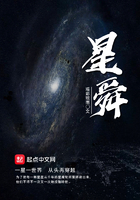你不妨像一出戏剧中的丑角,
按照我那个时代的趣味化装。
——纳博科夫《致未来岁月的读者》
民间有很多冥想的人。
——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
1.噩梦
那一年,在火车有节奏的晃动中,马领终于昏昏睡去。
经历了一场搏斗的他睡得并不踏实。在火车运行般的晃动的梦中,他一阵阵感到疼痛。他疼痛地梦到一只抽屉,这只抽屉在他愤怒地拉扯下,轰隆隆像一辆战车般地向他冲来。
一下剧烈的颠簸,马领陡然被摇醒。右肋尖锐的疼痛差点让他惊叫起来。他最终没有喊出声,只是大张着嘴,惊惧地看着车厢里陌生的景象。硬座车厢内拥挤混乱,深夜旅行的人疲惫不堪,醒着的神色木讷,睡着的姿态难看。在这新千年降临之夜,马领一下子想不通,此刻,是什么让自己一身疼痛地昏睡在火车上。一想眼泪就掉下来,急速地滑进大张着的嘴里。
对面坐着一个清醒的女人,很坚定地看着马领面无表情地掉眼泪。马领和她对视着,毫不顾忌地让眼泪往下滑落。
这样僵持了几分钟,马领突然把脖子向前一伸,对着女人使劲“嗳”一声:
“你看什么?嗯?看什么?”
女人并没有被吓住,仍然目不转睛地看他。马领立刻气馁,但依然坚持着让她多看了一会儿,然后才垂下了头。
女人递过一张皱巴巴的张巾,在马领低垂的头前来回晃,说道:
“不要哭,只是一个噩梦而已。”
马领哭得更倔强了,强辩说:
“没有做噩梦,我没有做噩梦。”
女人坚持说:“是噩梦,你是做噩梦了。”
马领说:“不是噩梦——我只是梦见了一只抽屉。”
“抽屉?”女人不耐烦地打断他,“梦见抽屉也是噩梦!不然你哭什么?”
马领猛地站起来,旋即像被电击了一般弓下了腰。他本来是想走开,但对面的女人可能误会他要动手,于是先发制人,用肘弯狠狠地拐了他一下。
马领哼一声,抱着肚子蹲在座位间。他听见有人冲着他叫嚷:
“不要打女人!”
马领抬起头,看到整个车厢的人似乎全部苏醒了,一双双神情困顿的眼睛盯在他身上。
两个乘警从车厢连接处冲过来:
“干什么?干什么?”
来到跟前,一个指着马领却向周围问道:
“他怎么了?”
“他要打人,”有人作证说,“他要打这个女人。”
马领被警察揪起来:
“你要打女人吗?”
马领痛苦地摇头,恐惧起来。
警察用一种商量的口吻说:“跟我们来一下喽?”
然后他们一左一右托在马领的腋窝下,搀扶一样地把他押向车厢一头。
马领心里忽然松弛下来,任由人挟持着。那个女人做为当事者,跟着他们一同来到乘警们休息的餐车。餐车里东倒西歪地坐着五六个列车员和乘警,见到他们进来,不约而同地表示出兴奋的样子。
一个胖胖的男列车员问马领:
“怎么了,你怎么了?”
马领想回答他,被一名乘警拽住胳膊阻止道:
“不许说话,你不许说话,我们问到你再说。”
胖列车员马上不满地哼一声,嘴里嘟哝着,忿忿不平地到一边躺下,又突然起身走了过来,那步态,就算说不上是傲慢,也实在够神气的。他从两个警察之间不大的空隙插进半个身子,伸出一根胖乎乎的中指说:
“神气什么嘛。”
然后他才心满意足地回去躺下了。
两个乘警不受干扰,开始询问马领。
一个说:“你拿出身份证来。”
一个说:“你想干什么?”
马领听到前一声命令,下意识地伸手往怀里摸,然后又听到后一声喝问,就以为是针对自己这个动作,于是手放在怀里停下,感到左右为难。他艰难地权衡着眼前的局势,有一点似乎很重要,马领努力提醒自己,那就是他没有做错什么,并且似乎更接近一个被横加干扰了的受害者,但面对两枚警徽——尽管它们的权威性刚刚在那位胖列车员卓尔不凡的插曲中打了折扣——他依然需要保持必要的服从。这两种自相矛盾的情绪让他感到更加不知所措。
两名乘警又同声重复了一遍自己的话。
马领手放在怀里说:“我没想干什么。”
一名乘警不高兴地说:“怎么可能呢?没想干什么我们为什么要带你来,你倒是说说看。”
马领说:“我只是站起来——”
“你还哭了呢。”
那个女人插进一句,声音小心冀冀,像轻声提醒。
乘警问:“你哭了没有,啊,你哭了没有?”
马领不安地看看周围,发现所有人都饶有兴趣地看着自己,就低下头承认:
“哭了。”
“你想干什么?”
问这话的总是同一个乘警,并且每问一次都很恼火的样子。
做为当事者的女人纠正道:
“你应该问他为什么哭,一个大男人为什么好端端的要哭。”
问话的乘警看看她,她鼓励般地冲他点点头,于是乘警就说:
“是喽,你为什么哭,一个大男人为什么好端端的要哭?”
马领感到自己随时会昏倒,一只手按在心脏上,不知如何作答。
女人在旁边拽拽他袖子,安慰道:
“不要害羞,说出来,说出来也没什么关系的。”
马领扭着身子,甩开女人的手,眼泪一下子又滑下来。
“你们看,”女人无奈地摊开手说,“他又哭了。”
两个乘警附和道:“是喽,又哭了,他又哭了。”
女人说:“他干吗总是要哭呢?”
乘警说:“是喽,干吗呢?”
女人轻轻推推马领,说道:
“你还是讲出来吧。”
马领摇头,像个赌气的孩子。
女人叹口气说:“还是我替他讲吧,他做了一个噩梦,所以吓哭了,是吧,是这样的吧?”
餐车里的人纷纷点头,原来是这样啊。
乘警如释重负地舒口气,说道:
“原来是这样,你承认是这样吧?”
马领摇晃着退开一步,突然激烈地陈述起来:
“是的,是这样的,我做了一个噩梦,我梦见一只抽屉向我冲了过来……”
2. 太憋了
回到车厢,马领发现全车厢的人都精神抖擞地引颈翘望着。在众人殷切地注视下,他回到座位上,艰难地弓腰坐下。他把一切都当成一个梦,一个在事后难以复述的梦。
女人并没有回到对面的座位,而是站在走道愉快地宣布道:
“他,承认了!”
她愉快的语调立刻感染了大家,大家都相视而笑,甚至有人鼓了几下掌。啊,啊,他承认了,他承认什么了?啊啊。马领在心里咒骂了一句。
女人站在他面前,大声问:
“你说什么?”
这一问差点让马领应声站起来。
马领支支吾吾说:“没有,我没有说什么。”
他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脱口发出了内心的声音。
女人问:“真的没说什么?我好像听你说了一句。”
马领急切地说:“我没说,真的没说。”
女人手一挥:
“那就是我听岔了,你不要紧张,看看你,脸都白了。”
她这么一说,马领立刻感到自己的确呼吸困难,脑袋里打着一阵阵濒于窒息时的呼哨。
女人把脸凑过来,在马领脸上仔细看,然后她转身道:
“他太紧张了,谁身上有药,镇静药,让他吃两片就没事了。”
马领绝望极了,困顿地看着她。这个女人,这么暧昧,年龄让人说不准,身份让人猜不透,一目了然的只是很白皙,屁股和胸都很丰硕,遗憾的是,她腰腹的尺寸抵消了这两部分的突出,整个人像一只浑圆的瓷器,器型饱满,上下基本没有流线型的起伏。就是这么一个女人,现在毫无余地的向大家响亮地宣布:
“他太紧张,需要两片镇静药。”
马领哀求道:“我真的没事,你不要再讲了好不好?”
已经有几位乘客送上药来。
女人回身胡乱抓过一把药片,递在马领面前说:
“吃下去,快点!”
马领看着伸在眼前的这只手上几粒花花绿绿的药片,泪水再一次模糊了眼睛。在这个女人莫名其妙的权威下,他无能为力地张开嘴,任凭女人把药片喂了进去。药片含在嘴里,苦味触动了舌蕾,马领感到口腔布满了强烈的血腥味,舌头发涩,并且肿胀得厉害,像叼着一截苦涩的橡皮。
女人向周围问道:“有水吗?给他口水喝。”
马领木然地注视着前方,越过女人的肩膀,他看到车厢尽头那两个乘警不时闪一下脸出来,然后又迅速地躲回去。几名乘客争先恐后地递过水来,罐头瓶,太空杯。马领正拿不准究竟接受哪一只,拥挤的水具中有一只掉在了地上,叭地一声,突兀得让人惊悚。
一个瘦高男人叫起来:“谁挤脱了我的杯子,是谁?”
他心痛地蹲下去看自己摔碎的罐头瓶,绝望地说:
“碎了碎了,还有两天的路程,我拿什么喝水?”
马领决定随便接过一杯水冲下嘴里的药片,却发现伸在眼前的手全部缩了回去。
瘦高男人站起来,扒开身边的人,不由分说,揪住一个穿红色高领毛衣的女人:
“是你挤脱了我的杯子!你,刚才就在我身边,这么快的缩回去不想承认啊?可是我知道是你,你的这件毛衣太红了,像猪血。”
这次几乎是全车厢的人都放开了他们扩音器般的喉咙:
“不要打女人!”
两个乘警如神兵天降,从车厢一侧迅速地挤过来。马领置身事外,他开始陶醉地咀嚼嘴里的药片,牙龈在松动的牙齿坚定地咬合下漫溢出腥咸的血水。他吞咽着自己的血,看着瘦高男人被乘警揪走,心里安逸极了。
药劲很快占领了马领。现在他真的感到昏沉,头像一颗成熟的果实,别无出路地向下沉甸甸地低垂,低垂,一派要落地的趋势。马领用双手扶住脑袋,梦再一次走进了他的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