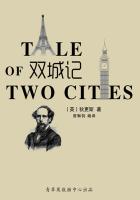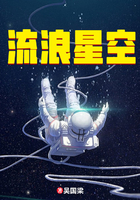三十年的作息习惯已经成了惯性,想要改变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习惯是一种很难改变的东西,包括思维习惯,包括生活习惯,有时候身不由己的就顺从了习惯的人,这个世界到处都是。也有的人很想改变习惯,就像铁红。铁红已经习惯了每天早出晚归,突然间打乱了原有秩序,让她浑身别扭无所适从,就像真的得了大病一般的难受。每当这个时候,她都会把自己骂个狗血喷头,她骂自己长了一身贱骨头,不干活就浑身发痒;她骂自己不知好歹,不用上班都能拿到工资还满心的忧怨,多少人为了弄到一张病假单,还给大夫送礼呢,真是天生的劳碌命,有福都不会享。
铁红就在对自己的责骂与安慰中改变着,她已经有些适应弟弟妹妹重新布置的房间。她虽然嘴上依然强势,但内心里也承认新的房间装饰确实赏心悦目,她由此也感受到了弟弟妹妹对她的疼爱与惦记。为了让铁红一个人的日子不至于太寂寞,铁明把自己的VCD连同一大包碟片送给了姐姐,中国的外国的碟片,都是铁明看过的、淘汰下来的。铁红发现这些故事片比电视节目好看多了,尤其最近她的睡眠出现了一点障碍,调养身体的同时,这些故事片占据了铁红大量的生活空间,让她对弟弟生出了感激与感谢。
闲下来的这段时间,铁红发现自己除了上班之外,竟然没有任何可以让她打发时间的爱好。从前忙忙碌碌的时候,铁红连电视节目都很少看,更别提别的娱乐形式了,因为她要抓紧时间休息,以便有足够棒的体力来应对十几个小时的工作。现在不一样了,铁红这辈子都没这么清闲过,似乎是要把三十年的假期全部找补回来。偶尔,她也会到街上去,买一些生活日用品,但她很少去百货大楼和超市,她只买过日子必不可少的柴米油盐酱醋茶,买菜也只买大陆菜,精细的菜价格太高了,她舍不得买。余下的时间,她把自己一个人关在家里,一张接一张的看弟弟送来的碟片,电视机便也从早开到晚。她发现那些故事片真是比电视节目好看多了。曾经,她最讨厌港台剧那些肉麻麻软绵绵的娘娘腔对白,现在竟然可以让她泪水涟漪,都把自己的心浸泡的柔润起来,气得她直骂自己越来越没出息,但她不否认自己对看碟片太着迷了,对那些爱恨情仇的故事充满了期待与渴望。那个夜晚,铁红照例拿出一张碟片,想都不想就放进了DVD,熟练地操作起来。很快,屏幕上的雪花就变成了清晰的画面,可是画面上的情景一下子让她傻眼了。
电视屏幕上出现了一对赤身裸体的男女。他们只用肢体语言交流,用眼睛说话,他们互相抗衡对方的身体,然后非常夸张的交姌,并且伴随着在铁红听起来像被蝎子蛰了一般痛苦的呻吟。
这张碟片是铁明的疏忽造成的,铁明家里这种黄碟挺多,但他都是和故事片分着放的,铁明以为送给姐姐的都是故事片,哪里会想到有一张黄碟挟裹其中,而铁红现在看碟片是不加选择的,她是按照码放的顺序一张接着一张看,无意中就碰到了这张黄碟。铁红十分恐惧看着屏幕上的画面,她的血液像喝了酒一般的加快了流动速度,心跳也完全乱了套。对于铁红而言,这一切来得太突然了,突然的让她措手不及,一下子晕失转向。她意识到,自己无意中闯入一片禁地。她想闭上眼睛,她想停止播放,可是她的意志不听她的大脑的指挥,身不由己的看了下去,直到画面上出现了雪花,她依然呆呆的看着电视,大脑出现了短暂的空白。
从看了那张碟片开始,铁红的眼前总是晃动着那些男人和女人在一起时的情景,甚至吃饭的时候走路的时候,男人的裸体也会在她的眼前晃来晃去。鬼使神差一般,她又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把那张碟看了好几遍。尽管那些画面让她浑身特别不舒服,像得了皮肤病一样的难受,她还是忍不住好奇的想看,尤其特特别想知道,男人和女人在一起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这个问题像是一只无形的钳子,紧紧的抓住了她。铁红在这张黄色碟片的引领下,不经意间推开了一扇叫做情欲的门。门里的世界光怪陆离,把铁红的生活搅动的波涛汹涌。她就在这波浪中沉沉浮浮,拼命地挣扎着想爬上岸来,可是,岸边太滑了,任她怎么努力,手都够不到岸上的栏杆,她以为抓到栏杆也就抓到了希望。与此同时,铁红作为一个女人,开始对自己的肉体萌动起来最原始最纯粹的觉醒,她知道这一切来得太迟,她不知道自己是应该欣喜还是应该悲伤,或者羞愧。她开始以一个女性的眼光看待自己,她就在这一刻发现,自己的血肉之躯燃烧起了欲望的火焰。
出走
铁红从午睡中醒来。病床上躺了十几天,她的伤病已经彻底痊愈了,人却瘦的脱了形,似乎从前那个走路一阵风,说话高门大嗓的铁红已经离开了她的身体飘然远去,剩下的只是一个空空的躯壳。铁红翻了一下身,以便让自己更舒服一点。在她挪动身体的瞬间,一种痛感顿时袭击了她身体上的每一个部位,最后在心脏里聚集。铁红一直弄不明白这是一种什么感觉。刚刚,在她睁开眼睛的刹那间,她明白了,那是一种疼痛感,是一种被某种东西连续打击后形成的钝痛,这种东西却是无形的,是肉眼凡胎看不见的。这种痛感已经在她身上持续很久了,好像从她父亲伤亡以后开始,好像从她母亲疯掉以后开始,也好像从她还是一个小小的胎息、她的生命刚刚形成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那么这种由来已久的痛是铁红是怎么忍受过来的呢?连她都吃惊自己的耐受力,她对疼痛太不敏感,但是今天,她强烈的前所未有的感到了疼。铁红抬眼看一下窗外,天有些阴沉,似乎正在酝酿一场秋雨,这样的天气是最合适睡觉的天气。另一张床上,陪伴她的王玫玫睡的正香,铁红试探性的发出一点声音,并没有把王玫玫惊醒。一个念头快速的在她脑海中形成了。
铁红脱下医院的病号服,换上自己的衣服,悄悄地溜出医院。她并不担心自己一走了之会给医院留下什么后遗症,她知道小菡和小程会替她办理好各种出院手续。她现在最想干的事情,就是赶回家里去看一下。从来都舍不得打车的她,今天破例叫了一辆出租车。十分钟后,铁红走进自己的家。
离开家几十天的时间,让铁红突然产生了一种既亲切又陌生的感觉。家里的一切还是她离开时的样子。许是空气不流通的缘故,屋子里弥漫着一股子陈腐的味道,一层薄薄的灰尘覆盖在家具上,地面上,床单上,甚至灯泡上,这让铁红感到特别不能容忍。她一个人干净利索惯了,见不得自己把日子过得这么邋遢。她想收拾一下房间,但又不敢耽搁太多时间,她知道,如果小菡发现她不在医院,马上就会找到家里来,她不想面对她们,只想一个人悄无声息的离开,相见不如怀念,免得彼此尴尬。她本来也没有多少痕迹留在世上,也就没有必要刻意的去消除。她以最快的速度收拾了几件衣服,并且把家里的现金都拿出来带在身上。出门总是要花钱的,虽然她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地。
铁红背着包刚刚走出家门,就看到唐小菡和王玫玫朝这里走来了,她知道她们一定是来找她的。她既不想和她们碰面,当然也不能返回家中。急中生智,她躲进了另一个楼门。唐小菡和王玫玫径直来到铁红的家,她们不停敲门的声音清晰地传进铁红的耳朵里,让她心中愧疚不已,但她努力克制着自己的情绪,让自己镇定下来。她知道,用不了多长时间,她们就会到别的地方去继续找她。果然,几分钟以后,小菡和王玫玫急匆匆的去了。铁红望着她们远去的背影,从她的内心深处分泌出一种毒汁来,这种毒汁的名字叫绝望。她的绝望像一种还没有被命名的漂浮物质,在矿区阴云密布的上空飘来荡去,很快,就被汽车的马达声、小商小贩的叫卖声、夫妻吵架时的对骂声、孩子的哭闹声、偷情的呻吟声给淹没了,给消解掉了。
铁红来到长途汽车站,一辆有些残破的中巴车停在她身前。个体客运的女乘务员一边问她到哪里去一边动手要拉她上车,铁红有些反感的挣脱了女乘务员的手,自己登上客车。到了车上铁红才知道,这是从矿区发往遵化县城的最后一趟班车。铁红想,到那里去都可以,只要离开矿区就好。她买好车票找个靠窗的位子坐下。天空越来越暗了,车开出矿区没多远,就飘起了细密的雨丝。在这样的一种环境当中,铁红觉得自己应该思考一点什么问题,比如,她这算不算离家出走呢?她出走的目的是什么?她应该在何处落脚?再比如,她可以回首一些往事,回忆一下曾经的辉煌,或者回味一些童年旧事。可是她什么都没有想,她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两只眼睛呆呆的望着窗外的秋雨绵绵中掠过的一个又一个村庄。
到达县城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铁红拎着包站在陌生的街道上长长地吁出一口气来。她知道这里离矿区有100多里了,她已经很成功地把那个熟悉的地方给甩到身后,她现在可以自由自在的在街上走而不用担心碰到探询的目光。原来,陌生的地方是可以让人放轻松的,陌生的地方可以给人一种别样的美好啊、
铁红是个干惯了力气活的人,十几天的病床时光,她像被判了监禁的囚徒,每一根骨头都变得酥软了,她强烈的渴望在自然的环境里走一走,用她的话说叫接地气。她并没有散步的习惯,只是想活动活动筋骨,让身上的细胞喘息一下,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恢复原有的力量。
初秋的天气就像一张娃娃脸,白天的时候被人们叫成秋老虎,让人汗水淋漓,到了晚上却是凉风习习。这个有着微微细雨的傍晚,铁红一个人在陌生的街道上走来走去,小雨淅淅沥沥的下着,纵使不打伞也不会淋湿衣服,铁红第一次知道原来雨中散步竟让人这么舒服,连呼吸都觉得畅快。她发现遵化县城比矿区繁华许多,县城的主要大街上店铺一家挨着一家,各种彩灯不停地闪烁着,把五颜六色的光打在行人的身上,使县城的傍晚色彩斑斓起来,有的店铺还用录音机高声叫卖着。站在这个声光音频交错的县城里,铁红清凄楚地发现,她的生命历程只能用苍白两个字来形容来概括。那所谓的荣誉称号,早就在无情的时光流逝中退尽了颜色,改变了容貌,她却浑然不知。一种无法言说的酸涩和悲凉,从她的内心渗透出来,很快就蔓延到了全身,那是生命中难以承受的轻,被刮了亿万年的风吹得瑟瑟发抖。
矿区是铁红无法割舍与忘怀的地方,不管她情愿与否,她已经被矿区吃定了,她可以想象得出,自己的不辞而别将会造成什么后果,她知道小菡会为她焦急,她更知道自己现在又一次成了矿区人们茶余饭后的热门话题。她害怕了,她真是是害怕矿区那些熟悉的人和物。矿区是她生命之源,是她的光荣与梦想的发祥地,有着她最深切的怀念与眷恋,可是她却发现了自己已经失去了矿区,她把自己的灵魂拿出来供矿区的人们阅读,而矿区的人们却把她的生命一眼望穿。留下来的,是质疑,是耻笑,是嘲讽,是探询。铁红知道,出了节能灯破障事件以后,她做任何解释都没有用,语言在这种情况下太过苍白无力,只能越描越黑,离开,是她认为目前最明智的选择。
如果说铁红离开矿区的时候还没有下定最后决心的话,现在她已经清醒了,她彻底明白了自己此行的目的——她是来了结自己生命的。当然,这个县城并不是她最后的归宿,她对这里并不满意,之所以来到这里,是顺其自然的结果。当了多年的先进人物,铁红也是见过一些世面的,她对一些常识性问题的认知程度有了相当大的提升。她也非常珍惜生命带给人的快乐与荣耀,但她也深深的感知了生命本身带给人的痛楚。她想,人们为什么常说一了百了,就是为了摆脱痛苦的折磨吧。她甚至想起了十多年前自己第一次面对死亡时的坦荡与安然。她突然想,其实所谓的害怕都是假的,如果大家都认为死亡可怕之极而你却与众人背道而驰,你就会被认为是另类。有些约定俗成并不适合所有的人,比如自己现在内心深处并不惧怕死亡,既然这个世界存心想要抛弃你,你又何苦死皮赖脸的难以割舍?
突然,一阵隐隐约约的乐曲穿过秋风秋雨飘了过来,铁红仿佛一位盲人见到了太阳的光芒,顺着歌声寻找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