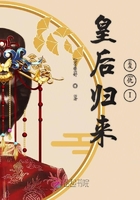荀寅舞完剑一身热汗,想也没想就推门而入,见到的就是这样一副场景——
明俏百无聊赖地托着腮嘴里含着蜜饯优哉游哉地晃着白玉似得纤长笔直的小腿,袭来细细风仍含着丝丝寒意,明俏下意识地紧了紧锦衾狐裘,她这人生来怕冷怕凉,即使是在春风摇曳的三月里也要穿得厚厚实实得才算安心。
雕花西窗迎着朝阳,斑驳碎影照射在明俏如花似玉的一张俏脸上,似是打上一层浅淡的嫩黄光晕缭绕在身旁,团扇半掩着菱唇,眼睫长而密低低垂下微颤,一双沁水杏眸若有所思地盯着屋外艳阳天的景色。
“到了敬茶的时辰了,夫君我们走吧。”
明俏堪堪回过神来,瞧见荀寅的目光正一瞬不瞬盯着自个儿,面上带着笑意起身走过去,唤着小厮驾起马车去了尚书府的正院,长安城的街道仍旧是熙熙攘攘,车水马龙,人声鼎沸。
她穿过吊脚楼的亭台楼阁,望见不远处漆红的朱墙,有片刻怔愣出神,再回过神来,已然到了府邸,二人早早便见到家中女眷已等候多时,陈夫人,连晴愫,还有一个前几年连宜昇收入门的白姨娘。
白姨娘和陈夫人恭恭敬敬地喊了句姑爷,而连晴愫则是怯生生喊了句三姐夫,随后惨白着一张脸深深埋头不言不语。
明俏兀自念着,这个四妹妹似乎还没从荀寅之前给的惊吓里恢复过来,但那天百花宴上那般趾高气扬不屑一顾的态度,明俏都怀疑这姑娘是不是精神不好,小丫头有两幅面孔?
不多思索,明俏觉得表面功夫还得做足了,有丫鬟端着茶盏过来,明俏和荀寅接过来,跪下敬茶,喊了句:“爹爹,请喝茶。”
“钰儿来了,爹爹祝你们百年好合,早生贵子,白头偕老,举案齐眉。”
连宜昇笑呵呵地一饮而尽,说了几句话,明俏则是端正矜雅跪着垂下眼眸,尔后左耳进右耳出,内心分外无语,这老匹夫装什么装,天下乌鸦一般黑,这个被陈夫人玩弄于鼓掌之间的便宜爹,之前对自家闺女的态度不冷不热,现下荀寅来了便要给几分薄面,当真是亲生的吗?
明俏接过空茶杯道谢温婉低眉,按照礼数一个个向众兄弟姐妹问好,有机会就随口闲聊两三句,向七大姑八大婶依次慰问,折腾了整整一个上午。
一箩筐凡俗礼节都尽数弄完后,明俏只觉得越发地力不从心起来,素手扶着墙壁弯着腰微微喘气,也不知道这几日是偶感风寒还是怎么的,许是昨夜被风吹着了?
隐隐约约老觉得额头那一块莫名很疼,身子很重如千斤,始终迈不开步子,脑海里晕晕乎乎的。
果不其然,在心荷院里过了晌午来连家正堂一起用过膳,遂要启程回太傅府后,明俏不负众望地发高热了。
*
“夫人怎样了?”
荀寅望着明俏烧得通红的面颊染上病态的绯色,昏迷过去不省人事的可怜兮兮的模样活脱脱像一只嗷嗷待哺的小奶猫般乖巧伶俐,蹙起眉头薄唇抿成一条直线,暗自思忖,昨日不是还好好的吗?怎么今天就突如其来地病倒了,晓得她身子骨不比旁人弱得很,但这也没有一丁点预兆。
“太傅大人,夫人应是昨夜天气冷着了风寒,她本就身子虚弱,况且……”
窦太医摸着银白胡须的手微微一顿,不动声色地瞥了眼旁边的侍卫小厮丫鬟们,荀寅倏地了然,冲袭风使了个眼色吩咐道:“袭风,你们都下去吧。”
“况且,昨夜房事太过激烈,我先给尊夫人开两贴补气养元的方子,按照这个去抓药,不出两日就痊愈了。”
窦太医低声结结巴巴地说完,小心翼翼地觑着荀寅此时此刻的脸色。
荀寅处事不惊的面容上有了一丝显而易见的裂缝,面上无光一阵白一阵红,神色晦暗不明,抖了抖嘴唇并未多说些什么,只得弯腰作揖谢礼:“窦太医辛苦,我已派人备了马车送太医回宫。”
“老朽告退,这几日切莫再让尊夫人受累了。”
窦太医一溜烟跑得飞快,荀寅站在原地良久未动,耳边全身刚才太医说过的那番话,修长十指揉了揉额角,双目发愣怔怔盯住明俏酡红的脸庞,想起来昨夜荒唐春宵帐暖,颠鸾倒凤的种种场景,只觉得嗓子眼越发地干燥口渴,随手拿起木桌上的一杯凉透茶水尽数喝下,才觉得那股子火逐渐平息。
椿浣试探性地询问一声让他如梦初醒:“姑爷,我今夜帮姑娘擦身子。”
“不用了,你放下吧,我今夜照顾夫人。”
荀寅沉声道,拿来了椿浣递过的手绢帕子和盛满清水凉凉铜盆,解下厚重的玄色绸缎束腰外袍,一下又一下仔细为明俏擦拭灼热烧红的脸蛋,只见她昏迷着还不忘蹙起好看的远山黛眉,神志不清地嘟囔着什么。
俯身凑近,才真正听清楚小姑娘说得究竟是什么——
她正在无意识地喊着荀寅的名字,那个称呼很早很早以前了,早到她还是个刚刚金钗之年的姑娘,而他被先帝派来教导皇子公主,做了一阵子的帝师,她唤着荀夫子,偶尔叫他太傅。
椿浣在一旁默不作声地看着,悄悄告退关上门扉转眼间笑靥如花,夫人和太傅感情真好啊,三姑娘现在,也是有人疼有人爱的姑娘了。
怀着欣喜的心情,一蹦一跳着往前哼着小曲走,感觉路上的花香都比平常香了那么一点点。
却不料,碰上了袭风。
“主子……”
袭风刚想踏进门,便被一个娇小的身影拦住了去路。
“夫人和大人都在里面歇息,你进去作甚?”
椿浣冷着脸阴测测问,她决心不能让别的闲人打扰到荀大人和三姑娘二人独处时间的谈情说爱。
“我当然是有事找主子。”
袭风白了他一眼,撇撇嘴。
这豆蔻年华的小姑娘,本应该是一生最美的年纪,但眼前这个瘦瘦小小的小丫鬟,怎的这般凶巴巴地质问别人?
何况,是他这个绝世的俊逸美少年。
椿浣全然不知道他到底在想什么。
只是觉得这个人看起来长得挺聪明唇红齿白的,结果是个傻子——十分地不懂事,连自家主子的好事都敢去打扰,连看也不看地就要进去,当真是个没眼力见的。
“不行,荀大人正在给夫人抹药,你待会再来吧。”
椿浣不容置疑地说道,狠狠不留情面地拍掉了袭风想要开门蠢蠢欲动的手。
霎时间,袭风的手便有了一道子明显的红印。
椿浣微张嘴巴诧异,这男人不是习武的吗?怎么还这般皮肤白嫩,像个姑娘家家,一点男子气概也没有。
“你这小丫头怎么这么凶?知不知道如果太凶的话老了会长皱纹?”
袭风嘶地一声倒吸一口凉气,迅速甩了甩受伤的手背,回头看向椿浣这个始作俑者,没好气地扔下这句不耐烦的话走远了。
椿浣凝视远处逐渐走远消失在地平线的红衣少年,左肩扛着一把几十斤的墨黑长刀,月光皎洁明亮,发出令人胆寒不已的锋利刀尖光影,衬托袭风整个人英姿飒爽少年郎。
难道真的是自己太凶了吗?
椿浣不解,拄着腮帮子撅起小嘴来。
*
抱节居内。
明俏醒来,已然是深更半夜,听着外面的阵阵打更声,觉得嗓子干燥得很,迷迷糊糊下意识地掀开锦被想下榻找水喝,却发现自己身上未着寸缕。
再转移视线看向床边,是坐在小杌子上攥着一方手帕趴在明俏跟前沉沉睡去的荀寅,潮湿的棉布上面还往下嘀嗒着水珠子,应是睡了还没一刻钟。
明俏披散着头发,发丝渐渐漫过脸庞,她低下头看向荀寅的脸。
那双凉薄看不出深浅的深邃眼瞳闭上,少了几分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淡泊,多了几分人间烟火气的温润如玉,随着他均匀的呼吸声胸膛上下起伏着,眼底却是有着淡淡的乌青。
许是今晚睡得过晚,照顾她了半夜。
明俏颇为心疼地用指尖晕染着粉嫩的丹蔻昳丽,轻轻摸了摸他的如瀑墨发,却发现手感顺滑柔和不错,又趁机上下其手捏了捏他的脸蛋,手感出乎意料的细腻好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