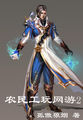“此人也是能耐,采花采到我这儿了!”
穆菁拧着一双柳叶眉侧眸看一眼床上好不容易被寒东雪哄睡的女子,有些困惑:“今夜来肆的女子不下十人,为何那个采花大盗就偏偏要采这朵看着样貌平平无奇的娇花呢?”
“穆菁。”寒东雪责怪地朝穆菁使个眼色,不太喜欢她评论他人的外貌。
穆菁说话虽直,但却也不无道理。若“以貌取人”,那穆菁可就是当之无愧的美人,采花大盗放着穆菁这等闭月羞花之姿不采,唯独去了……
寒东雪垂眸看着榻上睡容并不沉稳的女子,也有些不太理解。
“你也觉得不对头是不是?”穆菁挤到寒东雪身边去,“会不会是她……”
“她如何?”寒东雪瞥她一眼,将跟前这个凑近又凑近的脑袋推远些,“无凭无据的事情不要乱说。”
“我就说说而已嘛,你做什么这么凶?”穆菁扁扁嘴,气鼓鼓地很不高兴,“你就不能好好跟我说么!”
唯有小人与女子难养也!古人诚不欺我。
寒东雪目光不动,却在心中暗暗腹诽。
她懒得跟穆菁计较,起身去开了门。门外方序似乎已候多时,顾云朗不在,他只好等着她们出来,见了寒东雪,连忙上前低声将重要的捡了几句给她听。
“酒里下了毒,那人怕是救不了了,”方序谨慎地环顾了眼四周,随即偏头凑近寒东雪,在她耳边轻声又说:“雅间确实有人进去过,会易容术,混迹到了常来的熟客之中,所以我们的人没发现有陌生人,官府已经把我们这儿封锁了,仵作正在验尸。”
“我方才无意看了一眼那尸首的喉部,像是直接捏断的。”寒东雪肃容与方序对视一眼。
方序为人最是通透,星眸略沉,“不仅如此,颈部是有两道卡痕的,说明第一次没能把人掐死。”
“他既在酒里下了毒,为何又亲自动手?”寒东雪有些不解。
“是不是为了预防……”
方序皱着眉正欲说出自己的看法,却在不经意间瞥见了对面雅间里正倚着椅背,一脸看热闹表情往他这边看来的成锋,顿了顿。
寒东雪也察觉到,顺着他的视线抬眸看去,在看见成锋不成样地拿起酒壶就往口中畅饮的举动后挑挑眉。
方序面色有些不愉,扭头对身旁穿着短打的小厮问:“他什么时候来的?”
那小厮见方序表情凝重,不禁困惑不已,一看他指的是成锋,不敢怠慢:“你说成公子?一早就在了啊,这会儿官府不允出入,他一时半会儿也走不了。”
方序难得的有些脾气,还在耿耿于怀那夜成锋轻薄他之事,“我是说,谁放他进来的!”
“顾大哥允的啊!”小厮一脸疑问地挠挠头,不知道怎么就惹他不高兴了。
寒东雪却意外地看见方序耳根红了个遍,不免好笑,“你怎么比我更不喜欢他?”
“哼!”方序偏头,“如此轻佻之人,自然无人愿意与之往来。”
“那小美人倒是说错了。”
成锋不知道何时已经来到他们近处,面上是一贯的调笑,目光直勾勾地看着方序白皙如玉的面容,话中带笑,“我虽比不上我姐夫人脉广,但也是很得人心的。”
他说着,倾身凑近方序,神神秘秘地在他耳边道:“特别是女人。”
自打认识方序这么久,寒东雪还从没见他跟谁红过脸,他年纪虽小,却因早年受尽欺负而养成了忍气吞声的性子,即便是再生气,他也不过是沉默不语。成锋此人倒是个能人,能把人调戏成气粗颈红,也是有本事。
“要找女人上旁边怡花楼去,”方序推他一把,语气中连自己都未察觉出带了一股不知名的怒气。
“怡花楼有什么可玩儿的,”成锋顺着他的力道在原地转了个圈,俊美的眉眼间尽是风流,“哪比得上你这儿有意思,有好酒吃,还有好戏看,快活得很。”
他趣味儿地看看寒东雪又看看方序,牵着嘴角笑得好不怀好意,“我不仅看到了,还有幸目睹了全过程。”
***
昭华寺里,陆沉躺在廊下石椅上,正枕着一只手臂阖眸假寐,右手指间夹着一片被火烧得所剩无几的纸片,没烧干净的泛黄纸片上只剩寥寥无几的几个字,但却是他极其熟悉的笔迹:江河的亲笔。
自上次菁州官道一别,他们没再相见,江河修葺了堤坝,抓了贪官破了人命案,可以说是“大获全胜”,回京少不了又是封赏……
此番亲笔与他,一方面是担忧叔父的病,另一方面简概说了一番如今得了圣心的他处境更为危险,手上没有可以信任的人可用,这也就是为什么会造成此封手信被烧毁的原因。
陆澈出来时,见他还是保持着这个姿势未变,不免有些担心,上前询问:“兄长,天色已晚,怎不回房里去休息?”
陆沉睁开眼,须弥后直起身,抬手揉了揉泛酸的眼睛,“叔父怎么样了?”
江河的手信是送到昭华寺的,陆沉白日里没在,寺里的住持见是京都送来的,便交给了陆汶洲。陆汶洲怒气未消,又看了江河明里暗里想让陆沉去京都帮他,不免火气中烧,一气之下把信丢进了香炉里,好在陆澈眼明手快,虽挽救不及时,但也留下了一小块。
“睡了。”陆澈就着灯笼的昏光看他,上阶站着,只看一眼陆沉指间夹着的纸片,便知晓了自家兄长的心事,“兄长还在想江大哥的事?”
陆沉还未回答,陆澈又问:“兄长会答应江大哥吗?”
陆沉见他面色凝重,不免扬唇一笑,往身边让了让,“哪有什么可想的,我要是想再入朝做官,也不必等到此时,不是答不答应他的问题。”
陆澈乖乖在他身边坐下,余虑未消,“那兄长会恨叔父吗?”
“不会。”陆沉想了想,抬手揉了揉陆澈的发顶,笑得依然温和平静,“我在这世上只有你跟叔父两个亲人,不管何事何地,你们对我而言都是最重要的。”
陆澈这才放心,忽然又想起了个人,不禁扭头往四周张望,问:“成锋呢?”
“八成是去玩儿了,”陆沉却不在意,“不用管他,跑不远。”
“谁管他了,”陆澈皱了皱眉,“蛮俗一个。”
“是了,他又蛮又俗,”陆沉没好气,“你们俩自小就看对放不顺眼,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我回去看书了,”陆澈不想多谈,便跟兄长道别,“兄长也早些回去休息。”
“去吧去吧,”陆沉颔首,看着弟弟离去的背影,眉宇间不免又添了丝丝哀愁。
陆澈这傲娇的性格,也不知道像谁,明明很关心,却总是欲盖弥彰地表示鄙夷,其实内心是个柔软的人。
陆沉想起,他所认识的人里面,似乎还有另一个的性子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