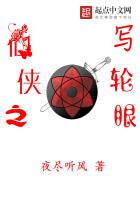尚且一面初见,清平乐便觉此人怪异诸多,细细琢磨只见但凡宫中女眷瞧着那孩子模样,都是爱怜十分,唯恐他再遭半分委屈。
纵是觉着这小表弟不同寻常,清平乐却不露声色,平素玩乐也都捎上他,没想倒是惹得清平毅不甚痛快。
“哪来的小孩儿?”见她带着个面生的小孩儿,清平毅语气有些不善,凌冽的目光在那白瓷玉面上掠过,倏尔挑眉道:“偷来的?”
清平乐鼓眼瞪他,带着几分嗔怪道:“没见过吧?这也是你表弟呢,叫崔洛。”
清平毅没有接话,看着这个半大的孩子目光瞬息万变间多了些深意。
纵使是熟稔之后,崔洛依旧如初见那般,永远一副笑脸盈盈、不争不闹的乖巧模样,根本堪不破他心中最真实模样。
不论是从心智还是行为上来看,他都与同龄人大不相同,更为奇怪的是自从他到来之后,宫中总有骇人听闻的怪闻传出。
一夜之间,池面上浮满了翻着肚皮的鱼群,远远望去铺天盖地的一片白,伴随着腐肉的腥膻刺鼻袭来。宫女、后妃们无不惊慌失措,不敢踏足宫门半步,就连加派看守的侍卫里三层外三层地侦查都未能逮住犯人。好在此事之后,终于有了几日的宁静,众人虽心有余悸却不敢多言,不管怎样这骇人的怪事总算是偃旗息鼓了。
可惜好景不长,不日沉寂过后,夜里荒芜的废弃冷宫禁地,总有守夜宫人听到此消彼长抓心挠肺的猫叫声。要想这冷宫里关着的无非是前朝今代罪大恶极的废妃,在这诺大的皇宫,无论是谁都心知肚明的禁地,谁又敢明目张胆的闯入?这可是要掉脑袋的活儿啊!宫人们权当是幻听,时间久了捱捱么总会过去的。
有人的地方就免不了有七嘴八舌,这些怪闻不胫而走,到最后都演变成了脱离实际光怪陆离的神话。直到有人指着那一片冷宫禁地连爬带滚、屁滚尿流道:“猫,一地的死猫,一地的皮毛。”
事情变得越发的不可收拾,先是一池的死鱼,到后来是一地的死猫......到底是何人胆大包天,竟真真在天子脚下犯了这般丧心病狂的罪责?此人又是拥有如何的本领逃过了重重追查?如若放任而为之,那么谁又能说得清下一次他又会使上何等残忍可怕的手段呢?如若不是凡人所为,那么是否会是上天降罚呢?
一时间众说纷纭,处处皆是流言传说。
圣上勃然大怒,首先便要众人缄口不言,私自议论者,斩!妄图堵住悠悠之口,反而激得人人提心吊胆、苦不堪言,唯恐怒触圣上、怒触苍天。
“如我所料,果真是你!”
找到崔洛时,他正坐在清平乐平日喜欢玩耍的秋千上,扳着手指扬唇浅笑。
按理说他这般大的孩子,看似天真活泼,岂会有人将他与这些骇人之事勾稽联系,想着此前的种种怪异,清平乐忍不住心下生疑,故出口试探。
崔洛昂起头看向比他略高的清平乐,表情闪过一丝错愕,随后他忽然放声大笑起来,看起来不急不慢,丝毫看不出什么破绽来:“表姐怎么会认为是我做的?我可是个手无寸铁的孩子呀。”
他一改以往甜腻无害的笑,换上一副清平乐也不曾见过的讥笑,这模样像是地狱里遣来的童使,一瞬间恶鬼上了身般。
清平乐被震慑住了,倒吸一口凉气,对这背后的罪魁祸首更加笃定了,说起来她的直觉可真不是一般的准:“我记得第一次见你时,你有礼有节、衣不染尘、面露笑意,这一切似乎都在你的运筹帷幄之中,乍一看你带着能让众人怜惜的纯善胆怯,可眼里唯独没有丧母的悲伤,那时我便觉得怪异,如今看你这副模样才恍然大悟,大家都被你的伪善面目蒙蔽了。我不知晓你是用了什么手段犯下了那等劣事,但你为何要这样做?”
他认真地想了想,抬起头看她时,眼眸之中近乎痴迷癫狂的笑意充盈。他道:“原来乐儿表姐那么早之前就揭穿了我的面具,妄我佯装了如此之久,果真不愧是我看上的人。至于我为何要这么做么,当然是因为好玩儿啊。”
好...玩...
知道真相之后,她曾与父皇母后委婉述说过此事,可无论父皇还是母后皆是一副揶揄玩笑之态,认为她是头脑不清胡说八道,再将崔洛招来一问,后者一副不知所云,泫然欲泣的模样又着实惹人爱怜痛惜,故皆以为清平乐过分欺压表弟,反而使她因此白白遭受谴责,而后这样的惨剧再无发生,父皇母后也未再做追究,那崔洛反而因祸得福备得宠爱。
清平乐只觉挫败无力,连亲生女儿所言都不相信的父母,又如何换得回真相大白?所幸便纵有千万人不愿信她,也还有一人义无反顾信任她,那人便是清平毅。
“既是你之所言,我又何必生疑。当初见那小崽子便觉有难言的诡异,如今你说这些都是他犯下的,倒也不难信服。”
清平毅伸手在她眉间一点,替她抚平微蹙的眉心,只道:“事已至此,你又何必因他黯然神伤、处处纠结。此人年纪尚轻便通晓此般阴毒之措,想来成人之后也非常人能比,断不能贸然让他再跟着,我怕他伤会你。”
清平乐微微颔首,想起他对她宣布主权的那副不容置疑的霸道表情,心头又是一怵,只想着以后若是冤家路窄碰上了,哪怕是绕着远路自己也要躲着些。
大概也就是那之后,面对她时崔洛便不再掩饰自己的真实之面,对她的痴缠也只增不减,以至于到了后来癫狂病态的地步。
与崔洛渐行渐远的清平乐又做回了曾经那个恣意潇洒的少年。一身月白风清男装,一副玉树临风模样,端的是翩翩公子少年郎,闲暇的日子里同清平毅纵马远游,偶然结识了几个同样年纪的少年。
其中一位少年名叫安乐,表字无忧,因其名中带“乐”,性格又幽默风趣,同清平乐一见如故,相处得最为融洽。
此人尚不知清平乐的真实身份,只以“乐兄”称呼,因着愈渐熟络起来,清平乐便亲昵以其字“无忧”相称。
两人平日里称兄道弟谈天论地,小到人家大到乾坤,无不相谈甚欢,在清平乐看来安乐便是那百年不得一遇的知己好友,却不想却因此将他带到了万劫不复的境地。
这日,崔洛差人给她送了一份信帖,信上所言无非是如常般哭诉清平乐绝情绝义,毫不顾忌幼年总角之交,视他为无物两不相往来。
每每收到这样的信,清平乐只会冷冷一笑,随后递与小厮烧掉。
目光随意往信笺上一扫,便要唤人来,乍一看信上最后一段小字很是令人在意。
“表弟日日忧心,彻夜难眠。怎知表姐有了新人笑,便忘了旧人泪,实在是可恨可恨。”
清平乐将这段话来来回回念了又念,只觉得极为不妙,只道那崔洛对她的事似乎了如指掌,她念想着那崔洛该不会只是来埋怨她这般简单罢?
莫非......
无忧他们?!......
她抓起袖衫来不及披上,就往府门外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