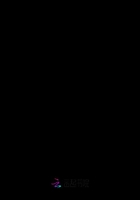忘记是几点才睡着的,却又早早醒来,看见陶灼华跑步刚回来。小佟一早也来了,她这两天调休,说是今天和大家一起去拜访那对老人。小蓓招呼吃早点,申克也没什么心思吃,就和她说“不饿”。
饭后休息一会儿,人们准备出发了。今天的活动申克本无心参加,但不想让别人觉得太反常而胡乱猜忌,只能勉为其难。他甚至在为见到肖莲时该做什么样的表情、说什么样的话而纠结。可当真正在院子里撞见时,却来不及思索就木讷地打了招呼。肖莲如是。
肖莲和老耿去探望姚渺,她推说昨天着凉受惊还没缓过劲儿,想留下来休息。老耿安慰了她几句,反倒让两个人都有些不自在。最让人感到意外的是,陶灼华居然也要和大家一起去。
“你这是……出关了?”
陶灼华看着申克满脸疑惑的样被逗乐了,“出什么关?我压根儿也没闭关呀!学这么多天脑袋都木了,明天就该回去了,今天也给自己放个假吧。”
肖莲提前准备了些米面粮油、蛋肉果蔬,两男四女乘船前往一个叫“盼夫洲”的水乡小村。听肖莲说要去拜访的是一对有着八十年婚龄的老夫妻,小蓓惊呼:“妈呀!八十年?”说着掰手指头数开了,“一年是纸婚,两年是棉婚,三年皮革婚……到六十年才是钻石婚,这八十年该算什么婚啊?”一旁陶灼华说“我记得国外好像叫‘橡树婚’吧”。
男人姓潘,今年九十五岁;女人姓傅,今年九十七岁。男人十五岁时娶了同村的女人,婚后不久就被日本鬼子抓了壮丁,一走数年杳无音讯,女人一边侍奉公婆,一边等他归来。好容易挨到日本投降,男人九死一生总算跑回家了,谁知没过几个月安生日子,又给国民党抓走充了苦力。女人伺候走了公公、婆婆,就一个人守着家继续等他。一直等到新中国成立后的第十年,男人才辗转返乡,这个家算是完整了。其间人们有的说他死了,有的说他在外安家了,她从没相信过。多少次媒人登门都被她赶了出去。算算到两个人团圆时已经结婚二十年,可实际在一起的日子还不到一年。这个村原本叫“潘傅洲”,随着时间推移,这对夫妻辈分、岁数已是村里最高的,加上人们推崇他俩这坚贞执着又富有传奇色彩的感情经历,干脆把村名改为“盼夫洲”。
船上的人听得感慨万千,议论纷纷。小蓓发现申克默不作声,一副无精打采的样,问他:“你今天怎么蔫头耷脑的?像只泄劲儿的鸡……”
旁边老耿搭茬道:“什么叫泄劲儿的鸡?你是想说斗败的**?”
几个人掩面偷笑,申克没笑,肖莲也没笑。小佟冷不丁冒出一句:“师兄你真操蛋!”
老耿赶紧解释:“明天就该回家了,他那是舍不得走……”说罢又看看肖莲,不想她却把脸扭向船外,让老耿很没趣。
老两口一辈子没儿没女,居所有些故旧。土坯垒的矮墙上间或生着杂草,木栅门没锁。人们离老远院里的黄狗就开始叫,这会儿见了肖莲却摇起了尾巴。院子不大,除了三间正房、一颗老枣树、一个低矮的茅厕和一个简陋的狗窝,就没什么多余的物什了。红砖瓦房是后来乡里出资、村民出工给翻盖的,屋里还算有几件老家具。家里没人,大家帮肖莲把带来的食材拎进屋,几个人就在小院门口张望。
不久,远远地看见有个坐轮椅的老者,被一个身材瘦小、步履蹒跚的老太太推着,向这里走来。肖莲喊着“潘爷爷、傅奶奶”跑上前去,老者和她摆手招呼,老太太一边握住肖莲的手,一边抚摸着她的头,亲切地说着什么。
俩老人走近了,才看出他们都穿着旧式的薄棉衣裤,黑里透红的脸上满满镌刻着岁月的沧桑。潘爷爷摘下毛线帽子,示意大家进屋。他没什么头发,年轻时做苦力腿受过伤寒,已多年走不了路,傅奶奶只要好天气都会用轮椅推老伴出去晒太阳。她盘着银灰色的发髻,也稀疏得可以看见头皮。
肖莲掌勺,小蓓、小佟、陶灼华帮厨,给大伙做饭。老耿和申克陪老人聊天,老人虽口齿已不太清晰,好在说话慢,能听明白。说起他在日本鬼子和国民党部队里受的苦、解放后享的福,以及他毅然选择随解放军支援新中国建设,直到受腿疾困扰不得不回乡的故事,精神越发矍铄起来。
吃饭的时候,肖莲、小佟、小蓓还陪潘爷爷喝了两盅。几杯下肚,他又提起傅奶奶这些年、特别是他不在家的二十年一个人苦苦支撑的种种不易,说着说着夫妻俩老泪纵横,勾得几个人也黯然沉思。
饭后大家帮着收拾了屋子和院子才离开。直到走出老远,申克回头看,两个老人仍在那儿,一个坐着轮椅、一个扶着木栅门,手挽着手目送他们离去。
船上,人们还在感喟这对老夫妻八十年的情感历程,申克依旧独自倚着船篷,仍在痴痴望着盼夫洲的方向。肖莲忍不住问:“你在想什么呢?”
“我在想,要修多少年才能修来他们那样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