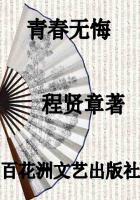狂风席卷,暴雨捶打,夜幕侵袭,它们是自然的怒焰,它们虽然可怖,但对人类社会的规则运转,却也没有改变什么。
楚王宁愿举世皆敌,也要一意孤行;
大臣坚持苦口婆心,期望回心转意。
人情冷漠於此时,体现得淋漓尽致。
没有一位合格的大臣,会为了自己对君王的“忠诚”出卖自己的家族;更不会有一位合格的君王,会为了自己的仁心、名誉,出卖自己的江山社稷,子孙后代。
......
一夜不知不觉间,又匆匆流去,没有人去关心时间的流逝,更没有人去关心景象的变迁。
该关心的,是楚王的态度;该关心的,是每一个人在楚王态度的最终表达后的决定。
...
於景氏家门中。
景鲤、昭封和屈翎三人密会,他们和当初咸尹子思和太卜红意那般,聚众‘议事’。
当然,他们也是为了表达表达自己对楚王的一些看法,仅此而已。
三人已经於密室枯坐了一夜,没有任何的对话,也没有任何的暗示,他们只是在等待,等待从宫中传出的第一手消息。
...
片许之后,
“蹬蹬!噔噔噔——!”
一阵阵急促而有力的脚步声响起,打破了好不容易才营造在密室中的阴翳气氛。
在紧张地奔跑过后,一位身着凤袍的中年男子披着疲惫,快速走到三人面前,拱手说道:
“大王依旧重病卧床,不愿上朝理政。”
“善。”
景鲤得到消息,发出一声回应,接着,又回归沉默。
而昭封性情直率,抢先对回报的三族之人问道:“如今郢内舆论如何?”
“市井中早已一片哗然,而吾等公族之中,在经过一时的激动后,许多旁支,庶脉之人亦陷入缄默。”
“善。”
三人对话,身为屈氏的代表,屈翎坐於旁,面情悲伤,无法言语。
因为他,就是当年楚王熊戆还未继位,从小陪太子读书的学伴。
昭封和景鲤都知道屈翎的往事,他们也知道屈翎的选择,所以,就不必强迫屈翎的表态了。
景鲤年轻,无忌,毫不忌讳地问道:“如今入宫?”
“可是太师......”
景鲤摆了摆手,阻止了昭封的下话,他明确地说道:
“师尊性情随和,不愿掺和政事,离郢之时,早已明明白白告与吾等,就不必忌讳此事了。”
“可其终究是太子之师乎!届时太子哭诉,太师护犊,何人可拦?”
景鲤了解广霖的性格,他也仍然记得广霖对楚王‘刍狗’二字的评价,他接着冷笑道:
“届时?木已成舟矣。师尊也瞧不上大王,只要吾等扶太子继位,师尊也不会过多指责。”
“可是,吾等既扶太子继位,待其羽翼丰满,秋后算账,吾等如今作为,可不是与自己为难?”
景鲤一时语塞,陷入一种难以言喻的尴尬境地。
......
“对了!!”
突然,
阴翳的环境中突然迸发出一丝活力,景鲤绽放笑容,有点小人得志的味道,原因就是,他想起来谢益的一席话,一席专门讲给他,专门给他上的一门‘课’。
“何对之有?”
“哈哈——!”
景鲤开怀大笑,联系到今日之事,他终于知道了谢益的意思,其解释道:“谢氏益曾言:以权君王,则权无限;以虚君王,则权有限。”
“如今不是已设立法院乎?立法限其权,定其责,以为虚君,垂拱而治,何患之有?”
昭封听闻此言,眼前一亮。
“听君一席言,茅塞顿开乎!!”
“哈哈——!”
二人相视大笑,独剩屈翎面觑不已,暗自抑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