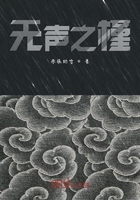周日,我早早起床,去楼下超市买来家里已用完的剃须膏,还挺惊讶,这玩意儿小超市里居然有卖;较之自动我还是更偏爱用手动,其中有种神秘的仪式感,对十六岁的我来说。今天比较不小心,刮刀蹭出了血,想起小时候父母的玩笑话。
“新年第一天如果不吉利了,那接下来一年里每天都会不吉利哦。”
仿佛今天也笼上不吉利的色彩,但总归是决定出门,就算对着镜子把嘴往上拉也得挂个笑。
我极度偏爱“仪式感”。不是逢年过节都得无端庆祝的仪式感,是理智的“仪式感”。比如今天要去见个平时不经常联系的朋友,我知道以后如果和他,和她经常联系的话,我们的关系会愈加亲切。但过去一段时间后,几个月,几年,我是否会后悔今天出门。07年7月11日,《变形金刚》第一部在国内上映。那年我9岁,看着荧幕上大黄蜂对山姆打开车门,身旁的女伴还在犹豫着,山姆对她说:
50年后当你回望今生,你会后悔没胆上这辆车吗?
我不后悔今天去了Jason的生日聚会。当然,去也不能空着手,借着传统与仪式感,和一些矫情,给他写了封信。拿了包前些日子亲戚取给我的烟。打了通电话告知父母今天聚会,推开稍稍吱呀的防盗门,出小区左拐走到三岔路口,随后转向沿左侧的餐厅门市走,到Zilde家楼下,待他出门闲逛片刻,一起等Jason放学。学校不一放假时间也不同。
我们当过初中同学,到初一上学期Jason转学,约莫初二Zilde转班。高中时我未从本校直接升学,成绩太差。倒是Jason拳击学完后,兜兜转转又回了这里。高中时我常显得和Zilde格格不入,较之同时期的我们,Zilde要成熟得多。我幼稚得很,好在话不多,还算省事。
我们坐在校门口的店里喝奶茶。听抽烟时火星烧着烟纸的滋滋声,等待着下课铃声。
“准备了什么礼物?”
“没准备,实在窘迫的很。”我笑,写信的事实在难以启齿。
“其实我也,那待会儿订个蛋糕?”其实他包里放着送Jason的电子烟。
“今天的蛋糕可能不是用来吃的吧。”
“你是个明白人。”他扬扬下巴。
“卫校平时忙么?”我有些在意。
“不是很忙,但漂亮姑娘挺多。”
“确实,很契合你换女朋友的频率。”
“需要教学么?现在限时免费。”他咪眼,看着我笑。
高中的男生总是很难把恋爱当回事,甚至于欺骗,只要当下有个异性,生理或心里上发泄荷尔蒙即可。我一直这么想,所以自己怀着“期望与相信”尽量不去碰,当然,也不歧视贬低别人的生活方式。可能只是觉得高中时期就和别人睡过觉,我称之“堕落”。Zilde这时与我怀着完全相悖的想法,我曾以为这是种炫耀,譬如谈过多少恋爱啊同多少人睡过觉啊,实际上他从未视之为“功绩“,也很少谈起。听过太多“喜欢”会贬值,在不断的游离中也更加不相信。不相信不是好事,相信也不是好事。
阿紫问姐夫“她有什么好,我哪里及不上她,你老是想着她,老是忘不了她?”姐夫平静的答“你样样都好,样样比她强,你只有一个缺点,你不是她。”彼时我怀着这样的感情憧憬。
“我仍认为向人诉苦不过是徒劳,与其如此,不如默默承受。”Zilde给我这一感觉。这却成为我身边“最后的90后”的共性;原来睡觉是常态,后来我明白了。
因为这也是“当回事”。
我与Zilde目视着Jason走过来。
Jason这个名字在希腊语里意为“医治者”。Rey转学后,我一直觉得Jason和Zilde治愈了我,以一种不可名状,像早晨阳光透进窗户照见的尘埃一样细微不可寻的方式,在不合群的年龄让正处于”假丧颓废”的我感到友谊。
我悄悄把信塞给他,示意他回家再看。
“今天应该是看不成了。” Jason小声说。
“怎么了?”
“今天谁还准备清醒着回家?”
“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我偷笑。
“借你吉言。”
和设想一样今天很开心,到火锅店时有些朋友已经候着了,饭后去KTV喝酒,打场激烈的蛋糕战,Wang顺便弄丢了他的zippo。直到衣服脏到洗不干净,喝到人仰马翻,凌晨勾肩搭背在街上瞎逛,在街角抽了支烟。Zilde说他即将回学校,下次见面应该是新年了。再骂骂咧咧两句,昏沉的大脑转动,嘴里蹦出些矫情话。打车回家。
“吃饭坐你对面那女生就是上次你说的内个?”我问。
“嗯,就是不晓得她送我钱包有没有什么意思。”Jason拍了拍口袋,脸上难掩笑意,怀揣一点少年的,藏不住货的欣喜意思。
“祝你开心,明年的开心明年我再来祝。”我有些醉了。
Jason开着窗吹风。Zilde已打车先走。
“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