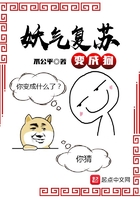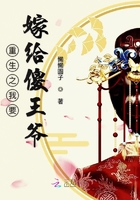舅舅的婚礼准备到万事俱备的时候,突然发生了一个小插曲。那是放寒假我从学校回家的一天晚上,我们全家都打算去睡了,突然间门铃乍响,不是礼貌性的一声声响,是不甘心不罢休的一串串响。门开处,站着陈妮,她还是无懈可击的漂亮,浅灰的窄裙,水粉的贴身毛衣,紫红的大披肩和长靴,艳光四射,那么娇媚的可人儿,脸上却带了点豁出去的愤怒。
舅舅见到陈妮颇意外,“妮妮,什么时候从北京赶回来的?”
“刚下飞机。”陈妮居然没顾全礼貌和我们家人打招呼,直走到舅舅面前,抬手欲掴舅舅一掌,却被舅舅抓住她的手腕。陈妮挣扎无果,红了眼眶。
和多年前飘着茉莉香的一个夏夜一样,舅舅温柔地环住陈妮,让她靠着他的肩膀哭,嘴里轻哄着:“好了,冷静一点。”
陈妮声泪俱下:“你要结婚,也是先轮到我,怎么是别人?”
这个场面太惊人,外公外婆,我爸我妈全傻在当地做声不得。我纯粹福至心灵,抓起舅舅的钥匙外套拿给他,舅舅感激地瞥我一眼,把陈妮带出去了。
陈妮走后,我妈惊诧,“我们家明在外面过的什么日子,好像很乱是不是?”
我爸百年不遇地责备我妈一句:“少胡说,家明不是那样的人。”
春节,舅舅的婚礼在没有受到任何外力的影响下顺利进行,然后结束。
“圆满漂亮。”外公是这样说的。
我不甚了然圆满漂亮到底是怎样,我只像提线木偶一样,人家拨我一下,我动一下,自己做了些什么我是不知道的。不过我知道自己见了好多不认识的长辈,见长辈的好处是,我的荷包变很满,这一点很重要。
上飞机飞温哥华办另一场婚礼的途中,我和舅舅狂睡,好像刚做过很多天苦工,筋疲力尽,睡得昏天黑地。下飞机的时候舅妈一路笑,说我和舅舅一大一小,睡得像两个孩子。与舅妈相处这些日子,我有点喜欢她了。她漂亮,高贵,有学识,谦逊,人也会说话,这些优点在她身上表现得十分得体,不会让人有压力,假如一定要找她的缺点,那就是太合理了,她是个合理的,中规中矩的女人,她的身上缺少生动与惊喜。
温哥华的冬天有雪,铺天盖地的雪花棉絮样撕撕扯扯地落着,我长这么大没见过如此壮观的雪,只觉稀奇兴奋。去了几天没帮婚礼任何的忙,尽和舅妈哥哥姐姐家的小朋友瞎闹,滚雪球,打雪仗。舅妈家一家人都是好人,和我爸妈一样,有点?嗦,是老百姓都有的那种?嗦,?嗦得让你安心,消除了我不少身在异乡的恐惧。
玩过几天,很喜欢温哥华,这是个美丽干净的城市,交通方便且简单,比我待的那个城市住起来舒服很多。曲冰舅妈说,以后可以来这边修学位,有亲戚在这里,申请学校很方便。我当然同意,我喜欢温哥华。
舅舅对温哥华似乎不陌生,他说他以前曾到这里旅游过。来温哥华后,他对曲家的亲友,保持着一贯温文有礼的态度,对身边的人也都体贴亲厚,闲的时候他看看报纸,静静地听MP3。我有一次拿他的MP3听,其中一曲《这么远,那么近》居然歇斯底里地录了十遍,黄耀明无休止地唱,张国荣则没完没了地念着广东话的旁白。这是首我听一遍就会被憋得想扁人的歌,完全不知道歌手到底在唱什么,可我亲爱的舅舅一听就是一个钟头,他行径有够另类。
舅舅婚礼前夜,我用舅妈的电脑上去自己的邮箱,发现里面有小舞给我的一封信。她寒假没回家,努力打工,试着筹足自己下半学期的生活费。小舞在信里说,我的男朋友令狐冲前些天,在一家电影院前面与肖瞳瞳当街拥吻,场面惊天地泣鬼神,当时围观者众,且给予吻者如雷掌声。
我对着电脑呆怔良久,回信给小舞:“现在这个结局也不错,或者可以符合某些人的期望,只要不是大家都不高兴就可以,我无所谓。”
晚上,大雪,我坐在窗前看着飘雪的温哥华看到半夜。嗯,我有点点受伤,一点点而已。没像偶像陈妮说的那样,感受到爱情有多绝望,之所以没绝望,或者是因为,我未曾深爱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