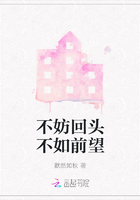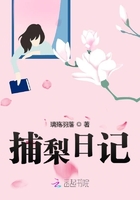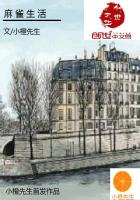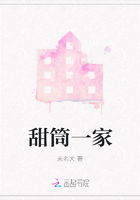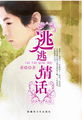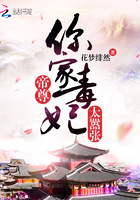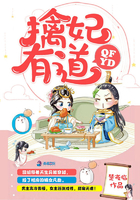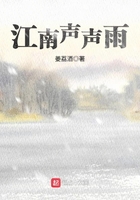李建东后来一直不敢回忆这段时光。对他来说,这段时光太痛苦了,每次回想起来就头疼、自责、心情落入谷底,好像从那时就有的灰暗从未消逝。毕竟,自己曾经离梦想这么近,离“改变命运”的机会就差这么一点,而所有的这一切,又都葬送在了自己手上。
得到孟老师的肯定答复后,李建东就安心准备复试。他想找朱师兄问问复试的情况,朱师兄是本校保研,说自己没参加过不太清楚,建议他找另一个去年考研进来的王师兄,并给了王师兄的QQ号。王师兄出国了,就在QQ上跟李建东交流了几句,他说你不用紧张,排名第二被刷下去的可能性不大,老师问什么你如实回答就可以。李建东问那老师们会问专业问题和英语吗?王师兄说专业问题是主要的,也有一些个人问题,英语去年复试没考,你情况特殊,是英语没过线,不好说。问过王师兄后,李建东把笔记又看了一遍,在京华图书馆找了几本学科内经典原著大致浏览了一番,准备了一篇英语自我介绍,他觉得自己更有信心了。
3月23日下午2点36分,李建东推开了复试室的门,迎面而来的是一张巨大的椭圆形办公桌,桌边密密麻麻围坐着大概十几个老师,还有学生在做记录。李建东感到压抑,但坐在桌子另一头的孟令柏老师让他别紧张,老师问什么答什么。
3月23日下午3点08分,李建东从复试室里走出来,他没有流汗,没有悲伤,也没有欣喜,而是一片茫然。老师们没有让他用英语做自我介绍,几个专业问题也一带而过,问他的更多是“你为什么要考这个专业”“你在大学里有没有看过与专业相关的书”“为什么毕业几年了还要考研”“你去年有没有考研,考的什么专业”等。他记得最清楚的是孟老师拿着他的本科成绩单,欣喜地发现上面有一门“中国伦理与人生教育”的公共必修课,他问李建东“你们这门课是谁教的?”。这门课是大二开设的,那时候他整天沉浸在网络游戏中,虽然没挂科,对任课老师却没有任何印象。李建东临时想编一个,但王师兄和孟老师都给他说要如实回答,他怕出什么乱子,便照实说我忘了。话一出口,他听到有几个老师发出了“呃”的声音,但孟老师什么都没说,接着又问了下一个问题。
复试完的头一两天,李建东感觉还好,但时间越久,他的心越慌。他越来越意识到了自己在复试中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他在复试前、复试中,乃至整个考研过程中都没有意识到,也不可能意识到。他逐渐明白了孟老师为什么这么看重学术背景,为什么要问他去年有没有考研,考的什么专业,为什么他回答教那门课是哪个老师时说“我忘了”其他几个老师的“呃”声。确实,他对于什么是学术没有一点概念,他“投机取巧”般考了个专业第二老师们并不特别看重,甚至他考研的动机,选择这个专业的动机从某些角度看来都不那么“正当”。他不是一个好学生,从来不是,他接触过京华的大神,朱师兄只是其中之一,他也看过孟老师批判功利化、浮躁的文章,复试时,被迫或半被迫,他把自己完完全全、毫无遮掩地袒露在了老师们面前,也把自己虚无、堕落、毕业后才无比后悔的大学生活袒露在了他们面前。
当教务办公室杨老师打电话给李建东说很遗憾你复试没通过,可以早点找调剂学校时,李建东的反应已经不像他想象的那样大了,这几年来所有的努力功亏一篑,他就这样看着京华大学在自己眼前滑过。他也不想再三战了,在第二次考研过程中,他已经用尽了全力,也充分证明了自己的能力。对于去年一年的经历,他不后悔,他想自己或许可以不去上班,早点复习,英语也许不会考45分,也就不会有破格,不会得到老师的重点关注,很多问题就不会暴露。但是不上班就没有钱,他没有别人那样的家庭能直接支撑他,而又不想把父母逼得太苦。他后悔的是大学四年,如果不沉迷于游戏那今日的问题都不会是问题,他后悔的是高中前两年,就像得知自己只差四分就能上一本名校时那样后悔,如果本科时积极一点,如果高中时就努力,没有如果,没有奇迹,一切都是理所应当的,京华啊,始终只是一个梦。
接到电话时表现得还算平淡,接下来的几周里,他却无数次地哭,失望、灰心、沮丧、后悔,所有之前有的或者没有的情绪,全部涌向了他,所幸他还有喻小晗时,每次他哭时喻小晗都在旁边陪着垂泪。喻小晗让他问问详细情况,他开始不想问,但后面还是问了。他发邮件给孟老师,孟老师仍然没有任何遮掩,他说你是有点悟性,但基础太差,学术积累太弱,你说自己一直很感兴趣,工作与这个无关,去年考的也不是这个,我们无法确定你进来后会把心思花在学习上,他非常诚挚地给孟老师回了句“对不起,麻烦您了”。他QQ上问朱师兄,朱师兄说孟老师和其他几位同道感于自利的市场经济使社会道德滑坡,一直试图推动各高校将伦理学教育纳入公共课范畴,以培养有“圣贤之德”的学生,你上了课却连老师是谁都不知道,自然惹他不太高兴,他说“朱师兄,谢谢您,我无缘成您师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