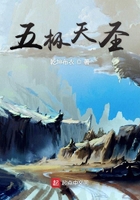李昪当年将国都从扬州迁至江宁(金陵),是一个绝妙的主意。
先不说风水龙脉之类的玄说,从战略上讲,比起位于大河(长江)下游且居北岸的扬州,江宁拥有着易守难攻的绝佳地理环境。依靠前方难以逾越的长江,结合连绵起伏的钟山山脉,“凭高据深,形势独胜”。
从上游而下,“其隘可守者有六:曰江宁镇,曰冈砂夹,曰采石,曰大信,其上则有芜湖、繁昌”,其余地段都是“芦蓧之场,或崎岸危矶,水势湍悍,难施舟楫”。这六道关卡,就犹如一道长链,环环相扣地锁住了江北顺流而下的要道,堪称南唐的命脉。
是夜,采石军营。
夏夜湿气重,江面上漫过来的白纱,层层罩盖在军营上。
营门望台上的新兵刚打了半个哈欠,立马用手捂住,把剩下的半个给憋了回去。因为他听老兵说了,营里的陈厉将军可是个严苛之人,要给他抓住了,非得被吊起来抽掉一层皮。
刚给了自己两个耳光清醒了下,那新兵忽然隐约忘记不远处,一个身影正从雾气中走来。
“诶,你眼神好,看看那儿是不是有个人?”
新兵身旁望着另一侧的同伴。
“哪儿?”
同伴转过身来,把身子探前一望。
“啪!”
新兵愣了一下,直直地看着眼前的无头身体一边颤抖着,一边把滚烫的血扑头罩脸地喷向自己。
片刻后......
“什么事?何故喧嚣?!”
陈厉穿着单衣从营帐里走出来,大声质问道。
“将军,好像有人来袭!”
一旁的亲兵赶紧应道。
“敌袭?”
陈厉眉头一皱,心头泛起一丝异样的感觉。转身入账取了口单刀,拉上亲卫,便朝传来喊杀声的营门方向奔去。
还没到现场,一股浓浓的、催人作呕的血腥味便顺着江边漫上来的水气扑鼻而来。
亲兵在人群中排开一条路,陈厉持刀上前,只见被上千士卒层层围住的场地中央,无端地立起了四堵高高的土墙。土墙围成一个封闭的、十步见方的立方体空间,上面插满了箭镞和刀枪。
虽然周围密密麻麻的火把在江风的摇曳下都无法将光线透进土墙之中,但从土墙的上方,惨叫声、厮杀声却绵绵不断地传出,围观的众人听得心惊胆战,却好丝毫没有任何办法。
“这究竟怎么回事?!”
陈厉拉过一个什长大声问道。
长官的威严让这个似乎掉了魂的士卒瞬间回过神来,连忙回道:
“将军,小的也不晓得咋地。兄弟们刚围了上去,就突然从地上升起了四堵墙,将他们困在了里头,我们帮也不是,不帮也不是。”
“敌人呢?有多少?!”
陈厉喝问道。
“敌人?”
什长犹豫了一下,竖起了一个指头。
“什么?一个?!”
陈厉刚想一巴掌把这犯浑的士卒抽醒,突然场中“啪啦趴啦”一阵巨响。
一阵夹泥带沙的风朝着包围的四周涌开。
陈厉眯着眼,望向场中央,即便这位戎马半生的厮杀汉,也心头陡然一震——
刚才还伫立如山的土墙已经分崩离析,从地上层叠的碎土下,鲜红的血就跟凿开的泉眼一般流淌而出。而原本的土墙之中,近百具尸体层层叠叠地铺满地上,碎裂的脑壳、残缺的肢体,还有翻出的内脏散落四周;而在尸体中央,一个矮小的身影正在擦拭着脸庞。
周围的士卒鸦雀无声......
每个人的心头都只听得见自己剧烈的心跳,每个人的脑海只浮现着一个词——怪物!
一个军营,一千多人,就这样地被一个人给......包围了。
“愣什么?放箭啊!放箭!”
陈厉首先警醒过来,大声一喝。
多亏了平日里的严苛训练,士卒们很快便反应过来,纷纷张弓搭箭。
可尸堆当中的矮个身影却似乎不见一丝慌张,只见他掌心淡淡泛出黄光,然后单膝跪地,两手一按,咧嘴低低一声暗喝:
“艮!”
“轰隆——”
整个军营的地面瞬间摇晃起来!
包围的士卒被震得脚下踉跄,像风卷过的麦田一般,瞬间倒下一片,就连手上的箭也不知飞向了何处。
陈厉灌注灵气于双腿,堪堪站稳,可忽然感到脸颊一凉。
“砰!砰砰砰!”
几声炸响,身边几个亲兵脑门、胸前被飞箭般的石弹凿开了大洞。
紧接着,“咚咚咚”的震响,一排排入春笋半的土锥从地上猛地冒出,戳穿了一个个还被震得躺倒在地上的士卒。
一瞬间,如同血肉糖葫芦一般的土锥从满是尸首的场地中央到陈厉跟前,直直地铺开了一条血红的地毯。
那矮个身影顺着这“地毯”,一跃落至陈厉面前。
还没等陈厉回过神来,“唰唰唰”地几下,四面土墙从自身身周拔地而起。等他定下心来,这才发觉——
自己竟然被困在了一个土制的牢笼之中!
而这牢笼之内,除了他,还有另外一人......
矮个身影抹了一把被血糊住的脸,露出一张微胖,但五官清秀的面孔。
陈厉望着这张脸,之间即便见着满地尸首都未曾动摇的心神,竟然这一刻有些发颤:
“怎么,怎么可能是.......你?!”
“老狗,你还认得我?”
矮个身影裂嘴一笑,端正的五官竟然愤怒地有些扭曲起来,甩动着手中滴血的铜锤,
“那还不跪下来——受死?”
......
同一时间,更上游的芜湖大营。
“好了,明天的训练就按这个计划进行吧。”
张德抬头看了一眼点头应是的副将,挥了挥手,
“那你先下去吧。”
等手下退出了营帐,张德摊开一张宣纸,挑高了油灯的灯芯,写起家书来。可没写几个字,他便停住了笔,自嘲地笑了笑,自言自语道:
“都忙晕乎了,下月初就回京述职了,还写什么信?”
说着,他伸了个懒腰,对着帐门外喊了一声:
“给我倒壶茶来。”
可等了片刻,账外都没有响起亲兵的应话。
他又喊了一声,依然没有回音。
张德眉头一皱,心中猛地一紧,起身抄起账内的长枪,掀开帘门,走了出来。
账外的军营里......静悄悄的一片,笼罩在江边渐起的雾气之中,只有火盆在哔哔啵啵地在作响。
虽然现在是夜禁时分,但也不至于安静得如此诡异。而且......周围一个人都没有。不仅本应守候在营帐外的亲兵不见了,就连巡营的卫兵也不见了。整座军营就像是在一瞬间......死了一般。
就在这时,一个身影在迷雾中走来。
张德定睛一看,原来是刚刚向自己请示完的副将:
“你怎么还在这里?这周围的人都到......”
张德话还没说完,只见眼前寒光一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