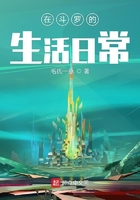人多了事儿就多,随之而来的各式各样的麻烦搞的杨冬青焦头烂额,抱着脑袋直喊头疼。队伍一下猛增到八百多人,越来越多的溃兵受到这支队伍那整齐的队列,强大的自信,充足的弹药以及偶尔闪过的几挑沉甸甸的粮食担子所吸引,自觉不自觉地加入进来。接踵而至的就是装备的补给,职务的任免以及最令人头疼的食物分发,一向甩手掌柜当惯了的杨冬青再一次对自己的能力产生了怀疑。
默默地走在队伍中,杨冬青一言不发的想着心事。说句实话,自己当兵以来一直都在最底层担任着低级军官,管人最多时候也就是因多出走那会儿手下的两百多号人。虽说在部队里也曾参加过团里师里组织的军官速成班,可那里面也只是教了些日常操典,战术动作而已。更多的经验和灵感还是来自战斗中的总结和对长官们指挥的模仿。
从一个连到一个营,听着只是管的人多了,可近千号人的吃喝拉撒,跑路回家全扔给他一个人担着,他自认自己没那个能力。一路上的所见所闻,特别是看到成千山万同一血脉的战友暴尸荒野,任凭风吹雨淋成为孤魂野鬼,无时无刻不让他的心里始终在隐隐作痛。自己死了也就死了,身后越来越长的队伍怎么办,万一有个闪失,害这么多人到最后也会变成那样的话,真的就算死了也会无法原谅自己的。
知道自己正在向远征军主力靠拢,恐怕是匪兵们此刻听到最好的消息了。或许是因为明白二当家的脾气秉性,知道他此刻承受的压力吧,匪兵们老老实实地管束着自己的手下,跑前跑后力所能及的不再惹是生非。新加入的溃兵看着这些平级或者高级的军官们,如此心甘情愿地听命于这个坐在担架上的年纪轻轻的上尉调度,而没有丝毫一句怨言或拖拉,或多或少从心里开始重视起他来。
队伍里这个满身硝烟,破烂的衣服上溅满了血迹,一脸的倦色的年青军官,能让这么多一看就不省油的家伙们如此信服,如此敬畏,有经验的老兵开始暗暗在心里庆幸自己的选择,考虑今后自己的所作所为了。
不为别的,凭着那双与倦容相背的干净、清澈而又透着点淡淡忧愁的眼睛,以及消瘦的脸颊上温和、真挚而又令人舒服的笑容,就让他们感到放心——这样的人不会像自己以前的长官那样,丢下大家不管害自己的。能有这样一双眼睛的人绝不可能是坏人,这也是这些没文化的兵痞子们心甘情愿努力融入匪兵连充当狗腿子的重要原因。
“咱们不能再这样继续走下去了,命令弟兄们得离开大道,跟着它的方向走,看能不能与大部队汇合。”杨冬青终于下定了决心,叫过不远的张振清说出自己的想法:“咱们的物资本来就不多,根本管不了那么多弟兄。再这么下去别说救不了其他人,恐怕连咱们自己的吃喝都成了问题。况且队伍里面到底能有多少人是铁了心跟咱们吃苦卖命的,真要打起来靠得住的恐怕还得咱们以前这些老人。别的人咱们也管不了那么多,得先对得起打开始就走在一起的老兄弟。其他的人只好说声对不住了。”说完盯着张振清等待他的意见。
前后看了看一眼望不到头的队伍,张振清咬了咬牙同意了杨冬青的决定。背着行军锅路过的王胖子恰好听见赶紧停下脚步阻止:“啥意思,路上还这么多弟兄就扔下不管了?好俺嘞二当家嘞呀,你可不能这么做哇,这不是眼睁睁看着他们去死嘛。再说,走一起大伙也好相互有个照应么,中不?”
杨冬青扭过身子没有说话,其实他何尝不想带上所有人一起走呢?
张振清看路过的人已经在支起耳朵探听消息了,怕王胖子的话动摇军心,暗暗骂了一句将拽他到一旁小声说道:“你老兄老糊涂了是吧,没看二当家的心里有多难受吗?有办法谁愿意出此下策,咱们又不是观世音菩萨。现在队伍里上千张嘴等着吃饭,你有办法给大伙搞来粮食啊?好,就算弟兄们一人省一口,凑合着跟长官部他们合到一起。他们有吃的吗?到时候联系不上国内,搞不到吃的,你他娘的把自己贡出来给几万绿了眼儿的饿死鬼当饭吃吗?你能救得了多少人!”一番话说的王胖子哑口无言,默默地背着锅看了一眼还在路上摇摇晃晃拼命挣扎的溃兵们,流着眼泪哭着走了。
张振清下令加快行军速度,迅速离开大路开进丛林间的小道直至半山腰,从这里另辟蹊径沿着山下大路的方向继续前进。从这里,杨冬青他们可以看到溃兵们的一举一动,可山下的人却并不清楚刚才还和自己一起并肩而行的匪兵们此刻去了哪里。
由于是另辟路径,行进的速度很快便慢了下来,花了整整一天的时间才走了十来公里。好在草上飞的侦察队此刻已经招进不少前身是挺进大队的新二十三师的老兵,干惯了逢山开路的营生。队伍走着走着就开进了一条不知是何人修建的便道上来,撵着天黑之前进入到一座古树参天的密林之中。
抬起头仰望那些大树,东北佬兴奋地拍打着巨大的树身仿佛回到了大兴安岭的深山老林之中,回到了背井离乡阔别了二十年的东北老家:“好久没见过这么多成材的大树了,这要是放在俺们那疙瘩,林子里面肯定到处都是人参、靰鞡草这些好东西,天天都是‘树倒了’这样的喊山声。唉,也不知道家里现在咋样了,自己还能不能够回得去。”匪兵们行进在高大的乔木林里,也觉得视线开阔了很多,省去了砍刀开路苦差事使得气氛也活跃了许多。
眼看着就快走出这片古树林的时候,队伍的前头突然传来急促的鸟鸣声,早已经习惯了丛林作战的人们当即趴下隐蔽,同时迅速找寻着可以藏身的隐蔽之所。
和杨冬青交换了下眼神,张振清带着几个匪兵快步离开了人群就往前冲,只见王成龙领着广西老兵气喘吁吁地跑了回来:“报告张连长,这老哥发现前面有情况,飞叔让我领着向二当家汇报下情况。”
让开路放过两人,张振清几个弓着身子轻轻摸到队伍的前面,只见乌龙和草上飞一动不动地蹲在一丛茅草里。
示意其他人留下,张振清匍匐着向两人的位置靠了上去。
发觉身后有动静,草上飞警惕地回过头,同时举起早已上膛的百式冲锋枪的枪口。见是张振清这才一言不发的转过脸去,打了个安静的手势,指了指前方。
顺着所指的方向,张振清竭力压低着身子举起了手中的望远镜,原来,草地中间的一道溪流旁边居然出现了一座村子。村子的周围,斥候们伏在不同的方位观察监视着。
与其说是村子,实际不过是几根木头和长草搭起来的类似于茅屋的建筑。而这样大概十几座的茅草房都不是很大,地板距离地面大概半米左右的高度,彼此间隔的也不是太远,房子外面的墙壁上还挂着些兽皮之类的东西。
闭眼想了想,张振清决定先进村子去看看情况。悄声在草上飞和乌龙的耳边一说,两人不约而同的点了点头表示同意。整理了一下自己的武装带,草上飞头一个蹑手蹑脚地朝着村子潜了过去。张振清带着一部分人拉开散兵线,利用茅草和地形的掩护,也慢慢地靠近了村子。剩下一部人在乌龙的带领下,各自端起枪瞄准了自认为可能出现目标的位置警戒着。
距离村子还有些距离的时候草上飞不动了。张振清慢慢爬到他的身边,疑惑的用眼神询问着。草上飞趴在一个低洼处低声说道:“悠着点,晚饭时间了村子里还啥声音都没,可能有情况。”
张振清侧过脸仔细听了听,朝四周做了个‘注意警戒’的手势,匪兵们小心地慢慢散开,相互掩护着朝村里爬去。。
“没人?”靠在担架上的杨冬青自言自语地奇怪着,努力想找出个头绪。急性子的高大炮扔下其他人,甩开两条大长腿没几分钟就把村子转了个来回:“还真没人,奇怪,村里的人都跑哪去了。”
整个村落干干净净却见不到一个活物,地上没有一点血渍,就连见多识广的草上飞和东北佬也迷惑不已。几个头头站在村子中央的空地上面面相窥,不明白是什么原因让村民们如此决然的放弃了这里,又逃往何方。
“大家快来看,这里有情况。”二尕子嚷嚷着跑了回来,离了老远叫了一声又朝村外树林跑去。
“下令队伍退出村子做好战斗准备,飞叔领着人把周围再仔细给我捋一遍。记住,特别是村子的两侧,一小时后回到这里集合。有什么情况就赶紧撤回来,实在不行就鸣枪报信,明白了吗。”杨冬青一面果断的下达着命令,一面领着身边的几个头头向二尕子的方向追了过去。
快到村边的时候,一股熟悉的臭味传了过来,所有人的脸色都是一变。这些整日里接触死亡的家伙明白,这是尸体腐烂的臭味。大伙朝着风吹的方向快步赶了过去。
村子后面不远的一个大坑里,人们见到了十几具已经腐烂的尸体。从那些简单的服饰看的出,死者都是些当地的缅甸土著,也就是人被山外的缅甸人以及远征军称作“野人”的克钦族人。看到这些土人的尸体,杨冬青不觉有些奇怪,这里已经是野人山的腹地了,谁没事了跑来杀这些手无寸铁的土人干什么?
高大炮像是发现了什么指着其中一个土人:“你们看,这家伙的脚好像是被炸掉的,就剩下半只脚掌了。”秀才蹲下身子,强忍着扑鼻的恶臭拨弄着那土人的尸体:“好像是手雷之类的家伙炸得。要是地雷或者炮弹的话,整个腿就应该没了。你们看他身上的这些小伤口,应该是手雷的弹片搞的。”
“少扯了,村子里根本就没有爆炸过的痕迹,你们大家谁见着了。”东北佬不服气的反驳。
“邪了门了,村子里没有战斗过的痕迹,这些人是怎么死的。还有人被炸伤过,到底什情况。”这下连张振清也挠起了头。
看了几眼坑中的尸体,杨冬青叫过二尕子追问:“你是怎么发现的尸体,除了这里还看到有啥不对劲的地方了吗?”
二尕子摇了摇头回忆着:“别的啥对不对劲的我不清楚。我是尿急找地方撒尿的,没想到脱裤子的时候就觉得很臭,闻着味过来一看才见着的。”
点了点头,杨冬青指挥大伙埋葬了土人们的遗体,围着坟包弯腰致哀,点上了三支烟权做敬香。祭奠完一行人重新回到了临来的树林里等候消息。现在这种情况也只能这样了,原始森林里危机重重,随便一个大意都可能要了你的命。特别现在是在土人的地盘上,杨冬青不想替人背黑锅顶缸,被躲在暗处的土人要了自己弟兄的命。
等了不到一个小时,远处响起了细碎的声音,好像有东西过来了。所有人立即举枪瞄准,做好了战斗的准备。很快,一顶德式钢盔进入了大家的视线,原来是草上飞他们搜索了一圈,没发现什么异常回来了。
“安全起见,还是趁天还没黑往前走点再扎营。”杨冬青看了看眼前略显诡异的村庄做出了决定。
人们重新扛起家伙起身了,只不过每一个人都警惕地观察着四周的动静。路上的蒿草是越是旺盛,最长的都快有将近两米左右了。要不是队伍一个挨着一个的话,人一进去就失去了踪迹。连林子里的树木也一棵比一棵的高大,粗大的树冠像巨伞一般,把整个森林遮挡的密不透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