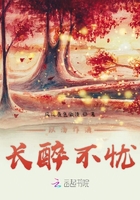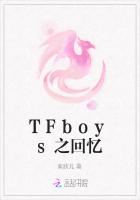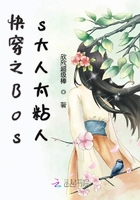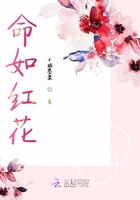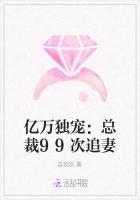苗苗看着身边的漫漫姐语气平静,眼泪却不停地向下留,默默地拿出纸巾递给她。
她接过纸巾,擦了擦,笑着说:“你看,我就是眼窝浅,过会儿就没事了。”
因为我知道,我再哭她也看不见,再哭她也不会回来,再哭也没人会心疼我。
苗苗默默地陪着她站在那儿,等她心情平静。
许漫很快就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问她:“还走吗?”
苗苗赶紧摇摇头。她不知道怎么安慰许漫,又怕她再触景生情,现在只想让她早点回去,交给唐妈去安抚。
“那回去吧。”
于是,两人才走出100、200米又往回走。
往后侧门过时,听到一个背对着她们的妇人说道:“先前在灵前哭的是老太太的什么人?”
“第四的儿媳妇。”另一个妇人回道。
“啧,我还以为是老太太的闺女或者侄女呢!哭成那个样子,看来婆媳关系很好呀!”
旁边几个女人都笑而不语。说话的那个妇人觉得有点莫明奇妙,不过看她们的表情很微妙,便知道自己说错话了:“不好?”
一个女人刚想说话,眼神余光扫到许漫二人,便住了嘴,再一看许漫身上的孝服,知道是事主家,便使了个眼色给旁边的人,对着她们点点头就走开了。
苗苗有点明白又有点糊涂,只是担心许漫有什么想法,不由望着她。只见她面无表情地越过这些人,苗苗赶紧跟上,那些闲聊的妇人也发现了她们,眼见自己当面说主人家的八卦,还被当事人正好听到,不免有些讪讪的。
唐妈一见她们进去,就迎上来。苗苗对唐妈使眼色,可惜她跟唐妈并未心有灵犀,唐妈一头雾水地看着她。她急得直跺脚,又不敢当着许漫地面直说,在许漫背后比比划划。
许漫像是看的见她的动作一样,拉着唐妈的手坐下:“小姨,我没事。过了这几天就好了。”
流泪,只会让爱自己的人心疼。而她,舍不得。所以,思念也好,怀念也罢,都好好的收藏起来。这些就是以后支撑她走下去的力量。奶奶,也只想她笑,不想她哭。
漫漫,你是大人了。她对自己说,大人就应该有大人的样子,别哭,一切都会过去。现在,让奶奶安心地走,让她放心,你一个人也可以照顾好自己,也会好好生活。
******************
吃过了豆腐宴,吴家兄妹就要先行离开,等到晚上守灵时再过来。苗苗一是担心表姐许漫,二是不想走路,就让她们先回去,她晚上再跟着一起回去。
唐妈想着天气热,再说离得也不远,自个娘家就在河对面,她就同意了。临走之前拉着女儿再三交待:“你记得自己的体质吧!记得就好,护身符戴好别丢了。要不,你现在跟着一起回去,晚上就别来了?”
一提起女儿这体质,她真不知道有多糟心。其实苗苗这丫头来不来都行,按她的想法是不让她来的。可她说担心表姐,又说很久没见面,这次不见面谁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面?一想,也是,反正只在白天,来就来吧。谁知道这丫头就赖着不走了。你是个什么体质,你自个儿心里没数吗?唉,这孩子真废了,真是哪哪都不能让她省心。
苗苗一看唐妈的表情越来越不善,晴空万里当场要表演成晴天霹雳,马上机灵地拉着大舅说道:“舅,你快跟我妈回去吧!回去休息会儿,晚上还要熬夜呢!回去走树阴里面,别晒着了!”
吴大舅没注意自个妹妹和外甥女的眼眉官司,就摸了摸她的头说道:“跟着你漫漫姐,别给人添乱。”然后又对许漫说道:“晚上我们再过来,先回去了。”
唐妈瞪了一眼苗苗,就跟着吴大舅出去了。
其实苗苗也不是非得留下。主要还是看到表姐许漫这个情况,走到哪儿都是失魂落魄的,总是晃神,未免有些担心。
不过也是,许漫自从离家出走后,只要回来,多数都是呆在奶奶家。这座老宅有太多太多回忆,只怕一桌一椅都藏着故事。更何况,她奶奶现在就躺在那儿,就象睡着了一样,只要一晃神,就觉得她会再醒过来,说:“漫漫呀,回来看奶奶啦?”
*****************
天黑透后,吴大舅和唐妈就打着手电筒过来了。夏天天黑的晚,他们到的时候已经接近九点。
稍坐了一会儿略寒暄几句,一过九点,那边执事先生安排灵前念经的、敲木鱼的都暂时停下来。取了一斗米,一个大的圆竹簸箕,把亲戚们都聚拢:“炒米啦!”
“炒米”是当地的一种丧葬风俗。它指的是,由念经师傅一边念经,一边把倒在圆竹簸箕上的米画圆圈反复做炒的动作。
“炒米”是要付钱的,给多少钱,师傅就念多久时间的经书。念经时间越长,即老人生前罪孽去得越多,走的也越安详,子孙得到的福报也越多。而且,这个付钱的还不能是主人家,必须是舅娘家、媳妇娘家。
这也是为什么吴家兄妹一定晚上过来的原因。
按理,许老大的二婚妻子娘家那边也要出面。可别说娘家,那个女人连同他继子今天都没看到。一打听,那个女人倒是出现了一会儿,早走了,说是老太太生前不待见,就不在这儿添乱,省得老太太走了还生气,继子呢又说反正不姓许,出不出现的没必要。
这样一来,许老大这枝就只有许漫的舅家。也幸好吴家舅舅出现了,不然他真的要被三亲六故唾沫腥子淹了。
许奶奶的娘家侄儿也来了。当初第一天,许漫回家没看到许老二和许老四,就是因为他们要分开去报丧。娘亲舅大,去娘舅家报丧是绝对不能马虎的大事。只是不知道是许老二去的,还是许老四去的。
吴家大舅准备了八百块钱。这个数额不算少了,一般有个四五百都可以的,有些兄弟多的,拿两三百也没人说话。
第一个给的是许奶奶的娘家侄儿,拿了六百,比平均水平高了一点。这下,吴家大舅不能把八百块钱全拿出来。这儿媳妇娘家越过舅娘家,那不是给许漫长脸,那是打许奶奶的脸。哦,舅佬爷家才600,你一个舅舅家拿800?你说合适吗?这就不合适。
行吧,五百,比舅佬爷家少一百,也在平均水平之内。
接下来,许二婶、许四婶是一个娘家,也来了一个大舅,拢共掏了600,一户300。
许三婶娘家来了个侄儿,原本想着五兄弟给200不算少,可见到前面几个这样,给了添了100也给了300。
许老五下午才到的,许五婶压根就没回。许老五少小就离家,对这些也不熟悉,一问还有这么个风俗,连忙自个儿掏了300块,说是许五婶娘家那带过来的。
念经师傅当然希望越多越好,也不管什么说辞不说辞,不客气地把钱收了,执事先生就一家家地唱报:“老太太娘家念经钱600!”
“大儿媳妇许吴氏娘家念经钱500!”
“二儿媳妇许万氏娘家念经钱300!”
“三儿媳妇许左氏娘家念经钱300!”
“四儿媳妇许万氏娘家念经钱300!”
“五儿媳妇许何氏娘家念经钱300!”
这办白喜事是要请人通宵守灵的,人越多越好,按例还要给每人准备红包,香烟。
许家在当地也算是大姓,遇到这种白喜事,这同姓族人能来的都会自发过来。红包也不要,就一包烟。毕竟家家都有老人,今天你要红包,明天你家老人老了,你要不要给?还不如大家都不给,拿包烟算是意思一下。至于你说不来?除非你家从此不死人!不然,你做初一,别人做十五。你倒是省事了,先人的脸都丢净了!
这就说远了,说回许家。
许家现在就很多族人守在现场。这也是执事先生为啥要唱报的原因,意思是:上慈下孝,因为儿媳妇尊重老人,所以媳妇娘舅家也尊重老人,把老人当回事儿,这钱呀就是他们的孝心。
所以,这种情况下,谁家儿媳妇娘家能说不出这份钱吗?
毕竟像许老大那种不以为然,认为人一死百了,没必要走这种形式主义的棒槌真不多!这先人是走了,你还要活着呀,人活着不就是为了张脸吗?
这执事先生唱完念经钱,那些念经师傅们就开始念经了。一本经书、一个木鱼,用当地方言带着自己的节奏又是说又是唱,唢呐铙钹挑着节奏不时掺和进去,大堂一下热闹起来。
孝子孝孙们就跪着围在旁边听。娘舅家倒不用跪着,坐在一旁的条凳上看着。等着什么呢?就等炒完米之后,还要分米。
像许奶奶这样年过七十之后走的老人都算是喜丧。只要是喜丧,这炒过的米就会分给子孙后人,据说是老人对后人的福报,吃了对身体好,特别是小孩子。
所以,一般炒米结束之后,几个娘舅也会带一些米回去,做熟给家人吃,粘点福气。其他的一般是平分给孝子们,或者直接做一锅饭大家一起吃。
再有那些家里有孩童身体不太好,夜里爱哭闹的人家,也会厚着脸皮讨要一点。关系好的人家也会给,但份量都不多。福气嘛,总是不嫌多的!
苗苗跟着看了半天热闹,这经文因为口音的问题是半句也没听懂,还没念完呢,她就瞌睡来了,靠在唐妈身上头一点一点的。那边跪着的许老大看到了,就指着苗苗那边跟许漫说了几句。许漫起身跟唐妈说了,陪着苗苗先去睡。
苗苗和许漫去睡了,唐妈和吴家舅舅却被接下来的事情气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