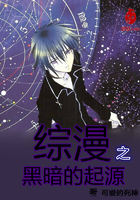河水湍急,小船的速度极快,转眼出了树林。河道蜿蜒向前,两岸开始出现高山,一座座沉默的矗立着,像一个个巨人俯视着那一叶小小的扁舟。
月亮不时被挡在群山之后,又一次次不屈的探出头来,时隐时现,星光却如银河,挥洒自如,落在河面上。
顾亭西想,沿着这条河,可以去宾州城,可以去清河城,或者一路沿着水路直进西陵港,入西海,去西黎国。
听阿娘说过,西黎很美,有很多大玄见不到的景致和产物。想到阿娘,他的心又有一丝低落。
他确实不知道要去哪里。
他的计划很周密,唯独没有想好,逃出城后,应该去哪里。
若大将军对他全郡通缉,他又能去哪里?西川郡虽大,却又有哪个地方是宋长昆的手伸不到的地方。
他看着两侧高低起伏的群山,不由的想,或者应该到山中躲个一年半载。
思绪起伏间,突然船身一震,星光下,明明前一刻还一无所有的船头,遽然多了一名玄衣男子,竟不知从何处而来,凭空出现。
顾亭西心神大震,船桨迅速横起,挡在身前。
玄衣男子身材极其高大,负手而立,一头黑发极长,在星光中随风飘飞,有一种名为潇洒的意味。
此时顾亭西却没有任何心情可以欣赏体味。
他一惊之下,便是冷静了下来,冷冷的看着出现在船头的男子,对方无声无息的出现,绝对不是普通人,想不到将军府的追兵竟然还是追了上来,一时心头涌起一阵苦意。
玄衣男子见他不过只有短短的一瞬失神,便立刻恢复宁定,明明不过是个十一二岁的孩子,竟有如此心性,心中暗暗赞叹,说道:“你果然很好。”
这句话没头没尾,顾亭西不知他所言何意,脸上现出一丝疑惑。
玄衣男子道:“沈军师说刺客是个孩子,我还不大相信,现在见到你,果然如此。你小小年纪,就敢刺杀将军府的小公子,还能全身而退,若非我在城西林里发现有人出逃的痕迹,一路寻迹而来,怕是让你就这么拍拍屁股走的干干净净。你有这份胆气和心性,我很喜欢。”
顾亭西心中疑惑,难道他不是将军府的人,莫非事情还有一丝转机?心中暗暗盘算,一时阴晴不定。
玄衣男子叹了口气,道:“只不过,你杀了大将军的小儿子,便是我再喜欢你,也没有办法。将军府的命令是生擒,但我可以给你一个痛快,带你的尸首回去,省的你在将军府大牢里生不如死,你觉得如何?”
顾亭西没有想到这名将军府的修行者竟说出这样的话来,心中又是惊怒,又感绝望,却又马上生出一股不屈不挠的倔强之意,他喝问道:“在你们这些贵人眼中,别人的性命就当真可以随意践踏吗?”
玄衣男子看着他的脸,又望了望天,说道:“这个世界上,弱者,很多时候连选择生死的权利都没有。”
这个回答并不新鲜,并不标新立异,并没有任何的出乎意料之处。
这个道理很简单,但正因为简单,所以显得那么的必然,那么的强大,强大到无法反驳,也无处可以反驳。
但是顾亭西不能接受,他承认这有道理,但就是不能接受,他的语气很坚定:“这不公平。”
“苍鹰搏兔,饿狼扑羊,强者自然为尊,这便是这个世界的公平。只不过,不是你要公平罢了。”
玄衣男子极其认真的说,他确实发自内心的欣赏顾亭西这个孩子,所以此刻才愿意在杀他之前,跟他多谈几句。
然而说再多的话,又有何用。
顾亭西明白这个道理,虽有不甘,却又有一丝行将解脱的欣慰,终于要跟阿爹阿娘团聚了。
然后他的心再一次变得绝对的平静,莫说来的明显是个深不可测的修行者,即便是普通的武者,又岂是他能抗衡的?
在真正的死亡面前,一个十一岁的孩子理所应当可以感到恐惧,但恐惧又有何用?那便不要恐惧!那便横眉冷对,那便不计生死的反抗。
顾亭西没有被死亡吓倒,等待着对方出手,而是挥动木桨,用尽一生最大的力气,向玄衣男子拍去,风中带起一声呼啸,竟有几分威猛的意味。
玄衣男子又是一声叹息,身影如旧,一动不动,然而当木桨靠近他身前一尺之地时,突然间,木桨从前端到末梢,开始寸寸爆裂,木屑激飞,再化为粉末,散入空气之中,这一切发生的极为诡异,没有任何征兆。
那是一道黑色的剑光,以顾亭西的双眼根本看不到的恐怖速度,在空气中不断震荡,斩碎木桨,然后刺进他的胸膛,切断了他的心脉。
剑光实在太快,以至于数息之后,鲜血才喷了出来,落满船头。
顾亭西没有感觉到疼痛,只是觉得无力,意识开始消散,天地一黑,身体直直向后倒了下去。
最后的一刻,他想着,原来这就是死亡的感觉啊,似乎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玄衣男子看着他软到在船上的尸首,早先有的一点欣赏和喜爱的情绪,也随之消散了。
对于一名修行者而言,这样的一个孩子,哪怕有点资质,终究还是太过微不足道,不足以令他心间有丝毫波澜。
没有了船桨,然而小船却沿着来路,逆流而上,无帆自动,往奉安的方向归去。
玄衣男子凝立船头,气度娴雅,衬着山水,像一名仙人,偏生脚底竟有一具死尸,他有一丝嫌弃。
……
……
左右不过是死个人罢了,这世间,天天时时刻刻都有人在死去。
就好像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奉安城西河里死个人,左右不过是死个人罢了。
玄衣男子心情突然又有些不错,虽然他不太在乎大将军小儿子的死仇,但若这个刺客始终抓不住,将军府天天折腾,大将军和沈军师天天板着个脸,作为将军府麾下最强的数名供奉之一,那么他也不得安生,这实在是让人心情不佳。
为了让自己可以舒服一些,他只好再认真一些,找到这个刺客,一剑杀之,解决掉这个麻烦。
他确实非常懒,非常散漫,非常害怕麻烦。这个世界上除了修行,除了证大道,其他的事情他本就不想管,懒得管。
所以他很年轻,但境界已然很高,比山门中的那几个活了数百年的老祖还要高。
然而一个修行者想要尽可能减少修行上的障碍,走上前人无法企及的高度,确实需要非常多的条件和资源,所以他尽管没有攀附权贵的野心,也只好依附在镇西大将军门下。
供养这么一位大修行者,将军府需要付出的代价可想而知,然而这一切显然都是值得的。
小舟逆流而行,却比来时更快,奉安城已然遥遥在望。
夜色的深处,开始出现一抹红艳,挣扎着想要撕开夜幕,奉安城黑色的城墙,像一只潜伏的暗鬼。
就在这时,玄衣男子看到了一辆马车,就停在前方的河岸边。
这是一辆制式很奇特的马车,车帘的绣工很奇特,车厢的型制很奇特,他确信他没有见过这样的马车,无论是在大玄王朝,还是境外诸国,甚至是山门里翻阅的滚瓜烂熟的典籍之中也没见过。
然而更为奇特的是那个坐在车前拉着马缰的老者。
他从未见过这么老的老者,他的皱纹很深,层层褶皱在一起,像山川,像被上古神灵的开天巨手挤压在一起的山川。
他的头发很白,像雪一样白,不,比雪还要白,没有一丝杂质,绝对而纯粹的白。
最奇特的还是老者的眼睛。
他的眼睛异常明亮,湛湛有神,透着无限的神采,有一种俯瞰万忆生灵的气度,浑然不似一个垂垂老矣的老人。
这样的眼神,玄衣男子从来没有在任何一个人身上见到过,哪怕是他曾经见过的,那些处于这个世间之巅,屈指可数的大修行者。
玄衣男子停了下来,准确来说是他身下的小舟停了下来,于是任由河流如何涌动,小舟都像扎了根一样凝立不动。
虽然他没有从这个老者身上感觉到一丝一毫的天气元气,但他绝对不会因此而认为,对方会是个普通的老人。
老人就这么静静的看着他,说道:“这个孩子就留下吧。”
他的声音很淡漠,很平静,没有一丝强势威胁的味道,就好像在说,该吃饭了,该睡觉了这样再寻常不过的小事,然而落在玄衣男子耳中,却自有一股凛然不可违逆的力量。
这便是宗师气度,渊停岳恃的气度。
一瞬之间,他心里不断的推算着一切的可能,比如这个老者是这个小孩的老师,比如这个老者是西川郡哪座大山里不世出的强者等等。
他隐约有些后悔,他突然发现这件事没自己想的那么简单,暗杀镇西大将军小儿子这种事背后又岂会没有主谋,难道这老者就是这个孩子的主使。
虽然没有感觉到从对方身上流淌出任何的杀意,但他没有任何道理的感觉到,自己的生死,就在对方的一念之间。
顷刻间,如芒在背,他的后背被冷汗浸透。
能让他有如此强烈的生死危机感的人,会是什么样的境界?是灭境?还是传中说的虚境?他不敢想象。
带着有生以来从未有过的凝重,他低下头来,向这个老人行了一个晚辈礼,以晚辈自居,便是尊重,也是服从。
小舟向岸边靠拢,离马车越来越近,离老者越来越近,玄衣男子的心早已提到了嗓子眼上。
他下了船,横抱起顾亭西的小小尸身,犹豫了一下,不敢放在地上,而是向马车走去。
他走的不快也不慢,一步一步走的异常的稳定,以至于小腿肌肉都有些轻微的颤抖,然后躬身把尸首交到了老者的手中,退后两步,又向老者行了一个礼,颤声问了句:“您还有什么吩咐。”
尽管极力控制,但声音还是压抑不住的有些颤抖。
老者看着怀中的尸首,头也未抬,淡淡的说道:“你可以走了。”
玄衣男子的心瞬间暴跳如雷,他不确定老者说的可以走了,是哪种形式的走?
是活着走,还是留下性命魂归幽冥的走。
但他不敢有丝毫犹豫,向着老者又行了个礼,迈开有些不受控制的双腿,向奉安城的方向走去。
不紧不慢走了十多步,在确定老者并没有对他出手的打算时,他的心再一次暴跳如雷,这一次却是因为劫后逢生的狂喜。
他展开几乎平生最快的身法,瞬间消失在他如飞步伐扬起的茫茫烟尘之中。
老者没有去看他狼狈逃去的身影,自然也是不屑,杀之亦不屑,所以玄衣男子没有死。
他只是看着怀中的小孩尸身,看着他透着死黑之色,犹带着倔强与不屈的小脸,感受着他身上全然断绝的生机,陷入思索之中。
他不太确定,车厢中的那位会怎么做。
在玄衣男子下手之前,救下顾亭西,这只是举手之劳,为何要让顾亭西身死?
哪怕以他的境界和思虑,一时也想不明白。
车厢中传来那名女子的声音,“把这孩子抱进来吧。”
老者转身,将顾亭西的尸身递进车厢,他眼中的神光与威势不再,显得极为恭敬。一双女子纤细的手,将顾亭西接了进去。
过了一会,老者突然脸色一变,他的手轻轻一挥,周围的空气骤然有一瞬间的凝滞,一道无形的屏障将马车周遭的空间包裹了起来,断绝了这片地带与天地之间的联系。
在这里发生的事,将没有任何人可以察觉到。
之所以展开结界,是因为老者闻到了一种气血的味道,一种无穷无尽广阔无垠般的味道。
用广阔来形容气味实在是很不贴切,但在老者的感知里,此时此刻他仿佛置身于无垠星河之中,漫无边界,跟这片星河相比,他所在的这片大地,一瞬间渺小的仿若空气中肉眼难觅的一粒纤尘。
一种浩大磅礴的气息充斥在整片天地之间,让他生出一种无比卑微的感觉。
就好像井中的蛙竟然有机会来到井沿,向那片完整的星空望上一眼,那是何等惊心动魄的体验。
更何况,他知道他所看见的这片星空,比井沿上的青蛙所看见的,更要浩瀚千万亿倍。
那份发自灵魂深处的敬畏,充斥着他的整个胸臆,没有任何语言可以形容。
仅仅是一滴气血,就让自己的识海里产生如此翻天覆地的感知,若是让这种气息散发到天地之间,让那几个老家伙察觉到,怕是会引来无穷的麻烦。
老者微微收敛心神,在这种玄奥的气机里醒转过来,他终于知道车厢中的女子要做些什么,震撼无语。
他问道:“这个孩子,竟然值得您用一滴心头血吗?”
“唯有度过生死玄关,方能承受我一滴心头血,这便是我与他之间的缘。”女子的声音从车厢中冷淡无比的传来。
老者默然。
此时,那轮红色的朝阳早已迫不及待,挣脱夜色的束缚,探出头来,将炽烈的光泽撒下人间,晨光跳跃在小河之上,也抚摸着远处刚刚苏醒的奉安城。
车厢中,传来女子压抑的咳嗽声,声音虽不大,却透着一丝痛苦。
强取一滴来自神魂真魄里的心头血,对女子而言是一种极大的损耗,老者清晰的感到她的气机瞬间变得衰弱而不稳定。
而有那么一个瞬间,顾亭西的身子竟微微颤动了一下。
死亡,从来都不是一种结束,而是另一种开始,这便是向死而生。
马车再度启程,老马依旧无力,而两行车辙渐远,蹄声踢踏,瞬间远去,消失在朝阳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