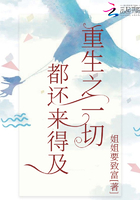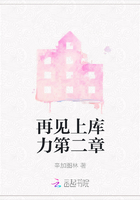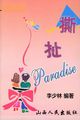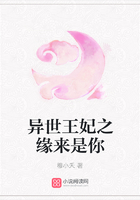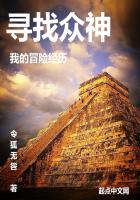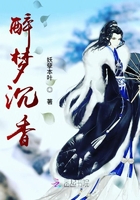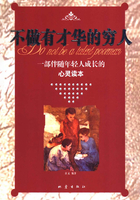妈妈那天到家里来,我开车带着她去市医院拿了她的体检报告,只有些高血压,心里比较安心,挽着她一起去逛街。中午饭点了,想带妈妈去吃川菜,又怕太辣;想吃火锅,又怕天气太热,吃的大汗淋漓反而不美;想吃烧烤,又怕吃的过于油腻了,俩强迫症沿着商场来来回回溜达,终于敲定下来去吃南京菜。
点了半份的南京烤鸭,一份桂花糕,还有一砂锅的鸭血粉丝汤,烤鸭不腻不肥,桂花糕清凉泛甜,粉丝汤鲜美醇正,我俩吃的相当开心。
说话间妈妈接了一个同事的电话,我便与她聊起来她学校里同事的近况来。她突然想起来,面露感慨地说:“你看你二楼王阿姨,前几年还教着课,现在就成了教体局的工会主席了。”我点点头,这确实升的有些快了,但实在事不关己,妈妈也一笔带过,高高挂起了。在平凡的人家里,只要雄心壮志还未赶得上自身的水平和条件,实在也生不出那许多嫉妒心来。
晚上妈妈泡完脚以后把水盆让给我来泡,等到脚都伸进热水里去,才发现电脑和手机都放在房间里了,实在自己懒,又不想麻烦妈妈,只好作罢,靠在沙发靠背上放空大脑。不知道怎的,201这一家的事情浮现在我的脑子里。
我从未见过那家的孩子,除了旧时定的报纸和如今的公众号推送。如果说102那家孩子是学霸级别,那么这一位便可称得上学神的层次了。最初的印象便是来自于大街小巷里她的事迹:什么一年之中只有大年三十的晚上是不学习的,而且在守岁完后还要再补上几套练习题,活像赎罪;什么寒暑假预习完下学期所有课程完成所有学校制定练习题;什么时时刻刻都拿着英语单词背诵,听的也是英语美式发音原声;什么大小英语作文奖项掰指头数都数不过来......
想当年我第一次听说她的事迹时,又是崇拜又是感叹:比起努力程度来,所有我见过的学生当真是无出其右的。松懈和懒散在她身上绝缘了。
妈妈把一杯牛奶放在我手边的茶几上,不知是感叹还是感慨地“哎哟”一声,竟也不约而同提起201来:“这下琳琳终于工作了,你阿姨和叔叔终于可以把钱花在自己身上了。”
琳琳便是201家的孩子。名字很简单,报纸上打印出来都是正正方方的。
她的父母虽也是社会地位差不多的职业,但都有自己隐晦的来钱的地儿。于是当这个灰土土的小县城的孩子们还在灰土土的高中里井底看天苦苦挣扎时,琳琳的父母就已经用钱上下打通关系,把女儿送到了市里最好的在我们看来是“贵族高中”里,又据她爸妈说“花了六七十万”寻到了自招这条路上,顺理成章地琳琳就进了在世界都算排的上号的(这里不便说明)大学殿堂,实实在在给家里争了光。
我仔细听我妈说着,其实心不在焉:说是争了光,这么隐晦的上学方式如果连我妈都已经晓得了,那哪一个但凡知道他们家真实家庭收入的人背后也不知嚼多少舌根子去。怎么能说不优秀呢,只不过人们心里所期望的便是一个“官二代富二代走后台给孩子买学历”的说辞,而非“天才少女通过自己的智慧与努力,又有雄厚的家庭背景做支撑,实现理想”。世间的好多恶意总是停留在人和人之间的诸如此类的各种不对等上,却最终无奈地归咎于先天环境的缺失。可讽刺,也可现实。
不知道怎的,我突然想起琳琳在报纸上的样子:那篇报道应当是讲某场比赛,最后的决赛是她和另一个男孩子角逐,在右下角的左端放了她的照片,黑框眼镜,梳着马尾的黑发,刘海整齐干练,眼里有那时候我看不懂的光彩,显然当时我还不明白什么叫做索然无味。
在她在某电视台实习的时候,她的妈妈专门跑到楼上来炫耀——也许也不是炫耀,只是母亲对女儿的一种发自内心的骄傲,并不具有恶意,再加上我的妈妈始终心态平和,便跟着一起看琳琳在许多台摄像机的记录下被知名主持人专门介绍——“这是我们台新来的实习生”,那孩子在离家几千里的地方,眼里有无法忽视的光芒。
她已经知道了自己是谁了。报纸会发黄发旧,变脆变薄,最终一触就碎或者另作他用;证书和奖状永远都锁在柜子里,贴在墙上,和金钱一样,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却总令人耿耿于怀。天才之名在人人相传中三分热度,但是“自己”这个东西可不一样,灵魂和身体一样需要找到生物钟和生命节点,不论是否有人赞美,诽谤或是抹黑。
妈妈戳戳我,示意我泡脚水都凉了,再添点热水。
第二天我们在超市采购水果和零食,恰好碰见了201的女主人,琳琳的妈妈,见她一个人走路来的,妈妈便提出捎她回家,她欣然同意。开车走到半路,听见妈妈说路边有便宜的鸡蛋,索性把车子停下来,让她俩去挑挑拣拣。
我把鸡蛋和葡萄都放进后备箱里,瞥见琳琳妈妈看着那个卖鸡蛋的摊主一家在出神。摊主家的小女孩穿着一条俗气的粉色裙子,皮肤黝黑,抱着个手机在刷短视频,妈妈略有不满地要拿过手机来,小女孩一个躲闪,跟着视频里的音乐蹦蹦跶跶起来,一旁的中年男子跟着她的动作小幅度地摇摆着手臂,女人在一旁开心地笑。
尽管我想告诉这个妈妈让孩子从小接触手机和这种视频会影响孩子的身心健康,尽管眼前的这幅画面和我描述的画面以及以前在书上看到的“一家人和和睦睦”的场景极其相似且无知,这依旧像极了童话故事,像极了在一片震后的废墟中翩翩起舞的人们,乐观地可爱,幻想地令人心疼。
琳琳妈妈很久都没有说话,我对她笑了一下,关上了后备箱。
等红绿灯的空隙,我突然想到,琳琳研究生毕业后,一直在北京发展,至今已经三年没回过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