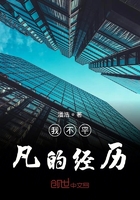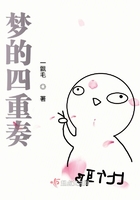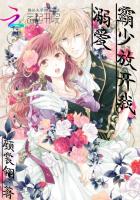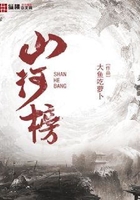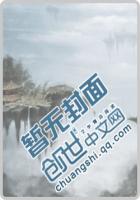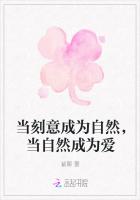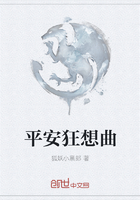和101户的闹心相比,102户对我的生活来说简直是要和善了太多太多。男人是公务员,女人是我们这儿重点初中的语文老师,孩子是个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瘦瘦高高安静又开朗的女孩子。
为什么说是安静又开朗呢:安静是因为每次她跟着我们出去吃饭,在饭桌上对着那么一桌子的大人,总是面带着好看又不逾矩的笑容,嘴角往上一分嫌多,往下一分嫌少,一言不发地听着我们说天谈地;开朗是因为每当他们说起一些职场声明场上我插不上话也不愿意参与讨论只礼貌地侧耳倾听的事情来,这时候她的眼里总是有一些过分璀璨的光芒,我把这些归咎于她作为一个学霸的求知欲。
当然,一切有可能是。也有可能不是。我希望她保持这样的求知欲,当然,也有些不愿,只是一瞬间而已,说不清道不明的。
那时候我还跟着他们一个爬山队一起早起去爬山,对我而言早起简直是折磨,但是对于他们家来说只是一项应有的习惯而已,尤其是当我头疼欲裂趴在方向盘上的时候,他们一家把车子稳稳停在我的旁边,招招手冲我问早,说一声活力四射的“走吧?”。不过说实话,他们一定没有我睡的晚吧,我总暗暗想。
而当她的爸爸在队伍前面和男人们一同说话,我就会跟着她和他的妈妈在队伍中间,母女俩偶尔还会在复习古汉语注释——上了高中以后她的妈妈没有办法辅导了,就变成了她戴着白色耳机用VOA默念着英语,我和她的妈妈说话的时候,总是悄悄看她认真的样子,带了些感叹,果然是别人家的孩子。
快要爬到山顶时总有一个坡度较大的走坡,这使我总是顺利到达山顶以后气喘吁吁,而看她总是神色轻松的,偶尔用手去扶一扶旁边扶着膝盖的妈妈。我们一起在山顶的一块石头上向下望。
我在这个小城里长大,自然知道这里有什么样的风光,他们也定然是看了无数次的,但是不知为何,就是看不腻。每次当我借着这个风景深呼出一口最后一点的清晨的睡意,精神抖擞地转头,总能看见她眼中倒影出来的闪闪发光的小城,那里定然有高耸入云的建筑,灯红酒绿的街角,天空映照着写字楼的玻璃蔚蓝又清澈,一如她的心底,有晶莹的钻石深埋在泥土和石隙中,等待着重见天日。
每当这种时刻我就会停下继续前行的脚步,头转回去看脚下的小城,心里不知是欣慰还是沉重。沉重也大概是沉重的欣慰吧。我这样想。于是后半段的路程都往往是在心不在焉中度过的。
回家以后我坐在餐桌上慢慢地吃着早饭,把煎的两面金黄的鸡蛋塞到嘴里,听着楼下叮叮咚咚的开始传来《致爱丽丝》的从她手上弹出来的钢琴曲,总是觉得无比的安逸和平静。我从来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学的钢琴,仿佛从一开始她就拥有这样精湛的琴技,或许她拥有这样的琴技也本来不是多么令人吃惊的一件事情。
很快她便上了高中,去了一个寄宿制学校,我们便很少再见面了,再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她的爸妈也不再去爬山,夫妻俩在家里养了一只小泰迪,天天早上原点起床在小区里散步带着小狗溜圈。不久以后,在一次聚会里听她的妈妈说她不满于现在的学校学习风气过于懒散了,想要去上面的市里的重点高中上学。夫妻俩心里是同意的,家里也并非没有那种条件,但是还是说,她如果在联考里考全市前几,才能进那样的学校。
这样的故事结果当然不言而喻。我自然也不知道她到底考的怎么样,等七拐八拐地从别人的口里听来的时候,她已经在那里安定了下来,在全新的环境里继续千篇一律又丰富多彩的学习生活。
良好的教育、丰厚背景和她认真勤勉的态度简直让人能一眼看到了她的未来,而她的未来也确实是跟着我所想的,随着时间的推进循序渐进:重点高中,重点高中重点班,全国作文奖英语奖,自主招生,高考发挥正常成功进入中政法学国际法,现在据她的妈妈说,还当着学校里的学生会主席,但是大三想要辞退了安心准备就业或者考研。
她终于走出了这个小城。
每当她的妈妈在人前听到无数的夸赞的时候,脸上平淡的就像听见“今天天气真好”这样的话一样,等人都走净了,她才会轻声跟我怨道:“世事无常无风也有雨,又哪里都是一帆风顺呢。”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她也像她这个年纪的女人一样,眉间有了蹙起来的褶皱,夹着不知道忧愁什么的忧愁。每当这时,我总是讷讷地无法说出什么话宽慰她什么,也深知我即使说出什么来也并不能宽慰这个母亲什么。
我和大多数的人一样,希望下一代,下下一代,他们都能拥有在暮年时仍然能沸腾的鲜红血液,有比在苟且当中生活更无价的信念,从未纠缠着迷于那一点点萤火,而在黑暗中匍匐着漂泊,从漫天大雪和布满尸骨的荆棘上攀爬而过,为世代传承的光做一点守护延续的薪火,等待着世世代代在等待的黎明。
而不是像那些和我一样停留在柴米油盐的安逸里一样的平淡一样,疲惫是生命中的全部,没有源泉,却似深渊,从未仰望天空。
我在这个小城长大,自然知道那个小山上有什么样的风光,这是个破旧的小城,从山上往下看,看不见高耸入云的建筑,看不见万家灯火,看不见一星半点的灯光,只能看得见常年灰蒙蒙的天气,旧红色的楼说高不高说矮不矮零七八落在城里,中间穿插了无数的临时蓝白色板房,手脚架搭着暗绿色的正在修建的残楼,无力,尚且无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