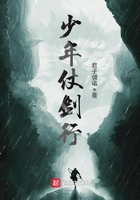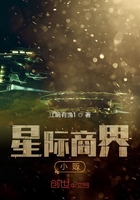第二十四章:会议
就像是古老中世纪的模样,一间小到可能“它”自己都会质疑自己是否有资格承载所坐诸位的房间。
分明是四周都有窗,阳光穿进,却是看不清屋中每一个人的脸。
“所以,为什么,你这么在意这座城市呢?”
一号位置上坐了个中年男人,不算高也不算矮的身高,一头在他这个年纪还算是茂密的头发,至少看起来,一点也不强。
“关键,十分的关键,”站在围桌的中央,光照不进的地方。
从剪影上来说,Ta的身材很是匀称,声音中性而富有磁性。
“长江支流口,名山所镇处,夺一处而江西可得,保江西则江南可守……”坐在六号位置的老先生羽扇轻摇,“这些我都知道,说些新鲜的。”
“气运在那里,”Ta说,“就像是我所布置的其他的‘那些’要守住的城市一样,气运在那里。”
“封建迷信吗?”三号位的女人肥大的双手交叉,托着自己下巴,“倒是新鲜。”
“虽说我一定支持你的选择,但是毕竟是责任太重大了,所以我还是想要问问,”,四号的声音动听,至少从可见的部分判断,她的身形十分较小。
“为什么不能交给王国军去占领呢?为什么必须要我们出手?而且为什么要出动这么多的精锐力量,上千名的五段,这是小一些遗党势力都拿不出来的巨大筹码,”叹了口气,说,“不是还有更重要的战略地带吗?”
“还是气运,”摇了摇头,“已经有人在我之前就在那片土地上做出布置了,如今气运已定,势已经到了那一步,我能做的只是拿出所有的底牌,一把梭哈。”
“尽管说的确是有些太过分了,”嘻嘻一笑,“但这就是乱党的核心精神呐!不愧是……”
没有理会女孩(?)的话语,打断道:“别忘了,各位派首们,至少在目前我们乱党的目标还是一致的,”顿了顿,“无论是建制派的三位日思夜想的旧世界,还是狂派三位要的乱世,本质上都是一样的不是吗?”
“……”
叹了口气,终究,零号位旁站着的老人发话了:“从乱党的建党基础上来看,他说的是对的。”
“所以不要质疑我,我是零号选中的人,”Ta的声音显得那么的坚定,“我不会背叛Ta的选择,我不会辜负Ta的教导。”
“那为什么你要亲自去那里呢?”二号也说话了,问,“君子不立危墙之下,何况乎是为主帅。”
“我要去见见‘王’,”虽说是看不见,但可以肯定的是Ta确实是笑了,Ta说,“在‘他们’离去的世界里,唯一仅存的王。”
“嗯……这倒也的确是个紧要,”零号老人说,“早去早回,这里离不开你,最后的决定也要你来做出决定。”
“嗯,”轻轻点头。
风和日丽,天空晴朗,似乎一切都是那么的美丽。
海鸥展翅飞翔,在那蓝到令人不禁怀疑起自己存在性的海洋之上。
一艘带有明显的现代科技成果游艇上。
“真美啊,”戴着中性面具的人说,“原来这么美丽的吗?也倒是难怪。”
“但天天看,不管多美不也都只剩下了乏味吗?”身边是一只口吐人言巨狮,“一十八天了,还没有看腻吗?”
“耐心是很重要的,”Ta说,“钓鱼的乐趣要是只剩下了得到的那一瞬间,不也是未免有些太无趣了吗?”
“这么久没有相见了,”狮子伸了伸自己发懒的身子,“有什么话要说就快点说吧……趁着我还有资格称‘王’的时候。”
“这话哪里说的,”摇了摇头,说,“哪怕就算是魔君降世,王,终究也是王,就算天下不在,王,终究也是王。”
“哈哈,”笑了,“小子,你说的话我真的很爱听,但还是说些实际的吧,你不仅仅是来安慰老头子我的吧。”
“魔君降世,您说他到底会降生在哪里呢?”回抛了个问题。
“不知道,但即使是不知道,到了他该回来的时候,他就会回来的,”狮子舔了舔自己的手爪,朝着太阳所在的方位眯着眼,望了望。
“但也还是要给自己找一片安身立命的所在的吧?”自问自答,“乱世就要来了,您的确是看淡了风云,但也仅仅是现在吧?”
“有意思,”狮子眼中凶芒暗闪,“你是什么意思?”
“您不会想要屈居人下的,哪怕是魔族的神,哪怕魔王的称号被他独占,不是吗?”
“我问你,你什么意思?”嘴中低吼声声不断,“如果我要杀你,你撑不住一秒。”
“庐峰,九江庐峰,”面临着死亡的威胁,也是那样的镇定自若,“就算只是用于隐居,也是一处极好的地方不是吗?既不声张,又很有用。”
“我为什么要听你的?”将自己抬起的头重新的垂下,按在自己双手交叠的肉垫上。
“应为您还有至少五个百年,而魔君……”
半恼的打断:“至少我还是魔族的人。”
“而且在您与我的第一次相见的时候,”耸了耸肩,“您可是亲口称我叫——当世诸葛的。”
“我是说,”嘴里啧啧了几声,有些犹豫,“……”
“如果那时我还在的话,”回过身去,恭敬的垂下腰身,“我愿为您车前卒。”
“不愧是当世诸葛。”
天边是红霞万朵,照在海水之上,粉色,这是此刻唯一的主题。
“粉色是一种很奇妙的颜色,”Ta说,“既不同于大红色落入俗流、还带着一些些的杀伐之意也不像是纯白色,初看之时纯洁无暇可惜却是经不起触碰的只可远观。”
“就像是你一样,对吗?”狮子王说,“你到底在想些什么呢?”
露在下半端的嘴巴明显的笑得洋溢:“在不黑不白的世界里熊猫笑了,在这树欲静而风不止的世界里——我却是只想把树给砍了去。”
“有一个传说是这样说的,原来的世界上是没有颜色的,后来,异常吞噬了所有的可见光光谱,”裂开了嘴,“我想推倒再来一次!”
“给世界涂上自己的颜色吗?”迟疑了一会,却也摇头说,“我有容得下你的气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