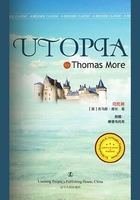韩驹也曾学习晚唐,《艇斋诗话》载:“韩子苍少以诗见苏黄门,黄门赠诗云:‘我读君诗默无语,恍然重见储光羲。’人问黄门:‘何以比储光羲?’黄门云:‘见其行针布线似之。’”曾季狸《艇斋诗话》,《历代诗话续编》,第321页。《艇斋诗话》又说:“人问韩子苍诗法,苍举唐人诗‘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几回惊妾梦,不得到辽西’,予尝用子苍之言,遍观古人作诗规模,全在此矣。如唐人诗‘妾有罗衣裳,秦王在时作。为舞春风多,秋来不堪着’,又如‘曲江院里题名处,十九人中最少年。今日风光君不见,杏花零落寺门前’,又如荆公诗‘淮口西风急,君行定几时。故应今夜月,未便照相思’,皆此机杼也,学诗者不可不知。”同上,第294页。 可知韩驹是师法唐人的,尤其是喜好民歌一类。吴曾的《能改斋漫录》说韩驹的诗有从韩偓、陆龟蒙、皮日休而出者:“韩子苍《谢人惠茶》云:‘白发前朝旧史官,风炉煮茗暮江寒。苍龙不复从天下,拭泪看君小凤团。’自注云:‘史官月赐龙图’,意虽本致光而语工。”吴曾《沿袭》,《能改斋漫录》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220页。 “韩子苍作绝句:‘天寒候雁作行远,沙晚浴凫相对眠。松醪朝醉复暮醉,江月上弦仍下弦。’陆龟蒙《别墅怀归》云:‘题诗朝忆复暮忆,见月上弦还下弦。’韩所出也。”同上。 “皮日休《谢人送酒》诗:‘门巷萧条空紫岩,先生应渴解酲杯。醉中不得亲相问,故遣青州从事来。’韩子苍《谢信州连鹏举送酒》诗云:‘上饶籍甚文章伯,曾共紫薇花下杯。铃阁昼闲思老病,故教从事送春来。’韵意皆同,当有辨其优劣者。”吴曾《记诗》,《能改斋漫录》卷十一,第305页。
除张耒、徐俯、韩驹这几个苏、黄内部的诗人学晚唐诗外,北宋中后期尚晚唐诗者尚夥。文同《问景逊借梅圣俞诗卷》便说景逊:“实亦郊岛徒。”文同《丹渊集》卷二十五,四库本。苏轼也说邵茂诚“诗尤可爱,咀嚼有味,杂以江左唐人之风”苏轼《邵茂诚诗集叙》,《苏轼文集》卷十,第320页。,所谓“江左唐人之风”,就是晚唐诗风。此外,强至(1022-1076)诗也颇近晚唐。王得臣也说他的“里人”史思远“从令狐先生学诗,有唐人风格”王得臣《麈史》卷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48页。张邦基(1131年前后在世)更是记载了许多“近人”接近晚唐体的佳句:“七言绝句,唐人之作,往往皆妙。顷时王荆公多喜为之,极为清婉,无以加焉。近人亦多佳句,其可喜者不可概举。予每爱俞紫芝秀老,《岁杪山中》云:‘石乱云深客到稀,鹤和残雪在高枝。小轩日午贪浓睡,门外春风过不知。’舒亶信道《村居》云:‘水绕陂田竹绕篱,榆钱落尽槿花稀。夕阳牛背无人卧,带得寒鸦两两归。’崔鶠德符《秋日即事》云:‘秋草门前已没靴,更无人过野人家。离离疏竹时闻雨,淡淡轻烟不隔花。’又《黄州道中》云:‘莫愁微雨落轻云,十里长亭未垫巾。流水小桥山下路,马头无处不逢春。’刘次庄中叟《桃花》云:‘桃花雨过碎红飞,半逐溪流半染泥。何处飞来双燕子,一时衔在画梁西。’僧如壁德操《偶成》云:‘松下柴门昼不开,只有蝴蝶双飞来。蜜蜂两脾大如茧,应是山前花又开。’吴可思道《病酒》云:‘无聊病酒对残春,帘幕重重更掩门。恶雨斜风花落尽,小楼人下欲黄昏。’又《春霁》云:‘南国春光一半归,杏花零落淡胭脂。新晴院宇寒犹在,晓絮吹风不肯飞。’赵士掞才孺《登天清阁》云:‘夕阳低尽已西红,百尺楼高万里风。白发年年何处得,只应多在倚栏中。’李慰去言《春晚》云:‘花瘦烟羸可奈何,不关渠事鸟声和。无人扫地惊魂在,吩咐轻红上碧纱。’赵箎之子雍《春日》云:‘拂床倚枕昼初长,好梦惊回燕语忙。深竹有花人不见,直应风转得幽香。’曾纡公衮《江樾轩书事》云:‘卧听滩声流,冷风凄雨似深秋。江边石上乌桕树,一夜水涨到梢头。’胡直孺少汲《春日》云:‘风云吹絮柳飞花,睡起钩帘日半斜。四海随人双燕子,相逢处处作生涯。’曾绎仲成《还家途中》云:‘疏林残岭起昏鸦,腊尽行人喜近家。江北江南春信早,傍篱穿竹见梅花。’刘无极希颜《漾花池》云:‘一池春水绿如苔,水上新红取次开。闲倚东风看鱼乐,动摇花片却惊猜。’王铚性之《山村》云:‘家依溪口破残村,身伴渡头零落云。更向深山拾黄叶,姓名罕有世人闻。’陈与义去非《秋夜》云:‘满庭淡月照三更,白露洗空河汉明。莫遣西风吹叶落,只愁无处着秋声。’如此之类甚多,不愧前人。”张邦基《墨庄漫录》卷六,笔记小说大观本。从这些“近人之诗”可以看出,晚唐诗并不缺喜好者。虽然人们没有像宋初人那样完全模仿晚唐诗风,但偶一为之,或是有限度地汲取其中的元素,在北宋中后期的诗人中还是很普遍的。
南宋以后,人们开始为学习晚唐诗歌寻找理论支持。很多人在苏轼、黄庭坚诗歌中寻找晚唐诗的因子。比如曾季狸就找出了许多苏轼、黄庭坚学中晚唐人的地方:“东坡‘江上秋风无限浪,枕中春梦不多时’,盖用白乐天诗。白乐天云:‘秋风江上浪无限,夜语舟中酒一樽。’”曾季狸《艇斋诗话》,《历代诗话续编》,第306页。 “东坡《梅花》诗云:‘群腰芳草抱山斜’,即白乐天‘谁开湖寺西南径,草绿群腰一道斜’是也。”同上,第309页。 “东坡‘纤纤入麦黄花乱’,用司空图‘绿树连村暗,黄花入麦稀’之句。”同上,第310页。 “山谷‘百年中半夜分去,一岁无多春再来’,全用乐天两句:‘百年夜分半,一岁春无多。’”曾季狸《艇斋诗话》,《历代诗话续编》,第315页。 “山谷‘平山行乐自不思,岂有竹西歌吹愁’,出杜牧之诗‘平生五色线,愿补舜衣裳’。”同上,第317页。 “山谷《清江引》云:‘全家醉着蓬底眠,家在寒沙夜潮落’,‘醉着’二字出韩偓诗‘渔翁醉着无人唤,过午醒来雪满船’。”同上,第316页。这些“发现”消解了苏、黄对中晚唐诗的严肃态度,苏轼说“元轻白俗”,但自己却学习白居易、司空图;黄庭坚说不能学晚唐人,自己却暗中化用晚唐诗。既然苏、黄都学习晚唐,后生小子当然也可以。因此,人们开始重新审视晚唐诗,于是不久,南宋诗坛便掀起了为晚唐诗平反和学习晚唐诗的运动。
§§§第三节 对晚唐诗的肯定与对江西派的批评
北宋末到南宋前期,替晚唐诗说话的人逐渐多了,一些论者开始从总体上给晚唐诗以肯定。首先,他们认为唐人“工诗”是普遍现象,李之仪说:“唐人好诗乃风俗,语出功夫各一家。”李之仪《德循诗律甚佳,方幸拭目,因作拙句以勉之》,《姑溪居士前集》卷七,四库本。洪迈说:“大率唐人多工诗,虽小说戏剧、鬼物假托,莫不宛转有思致,不必专门名家而后可称也。”洪迈《容斋随笔》卷十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92页。其次,认为他们之所以“工诗”,是因为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李纲(1083-1140)说:“自唐以来,卓然以诗鸣于时,如李、杜、韩、柳、孟浩然、李商隐、司空图之流,类多穷于世者,或放浪于林壑之间,或漂没于干戈之际,或迁谪而得江山之助,或闲适而尽天地事物之变。冥搜精炼,抉摘杳微,一章一句,至谓能泣鬼神而夺造化者,其为功亦勤矣。以此终其身而名后世,非偶然也。”李纲《五峰居士文集序》,《梁溪集》卷一百三十八,四库本。陈善(1176前后在世)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唐人多以小诗著名,然率皆旬锻月炼,以故其人虽不甚显,而诗皆可传,岂非以其精故耶?”陈善《扪虱新话》上集,卷三。
既然肯定了唐人普遍“工诗”,那么这种肯定自然也就可以落实到具体个人。于是贾岛得到了好评,如员兴宗认为贾岛苦吟之功最为可取,《遣兴十首》之七说:“手弄风月玉川子,肠入诗星贾浪仙。寒吟苦饮息万动,两公等是区中贤。”吕南公则认为贾岛诗之高妙处罕有人知:“岛之诗,约而覃,明而深,杰健而闲易,故为不可多得。韩退之称岛为文,身大不及胆。又云‘奸穷怪变,得往往造平淡者’,予考于集,信然。今世之人,皆知赏识岛诗,至论其所以为岛,则未必知也。彼徒吟之曰‘西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又曰‘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云云,以为贾岛之高妙在此。嗟乎!是不害为不知岛也,安得真知岛者而与之论哉。”吕南公《书长江集后》,《灌园集》卷十七。 慨叹贾岛知音太少的还有晁说之,晁曰:“贾岛云‘岳石挂海雪,野枫围渚樯’,予谓不愧谢康乐‘扬帆采石华,挂席拾海月’。谢句喧于寰中而贾句未有一人目之者,何耶?二人分散动静之势极殊,而幽深闲暇,俱绝俗则一也。”晁说之《论诗》,《嵩山文集》卷十四,四部丛刊续编本。
“郊寒岛瘦”的另一主角孟郊也得到肯定。许说:“孟郊诗苦思声远,可爱不可学。”许《彦周诗话》,《历代诗话》,第385页。魏泰则认可孟郊苦吟之功:“孟郊诗寒涩穷僻,琢削不假,真苦吟而成。观其句法,格力可见矣。”魏泰《临汉隐居诗话》,《历代诗话》第321页。俞桂则认为孟诗是穷而后工:“自古岛郊贫彻骨,诗逢穷处始为奇。”俞桂《吟诗》,见陈起编《江湖小集》卷五十三,四库本。
李商隐也受到好评,范温说:“义山诗世人但称其巧丽,至与温庭筠齐名,盖俗学只见其皮肤,其高情远意,皆不识也。”范温《潜溪诗眼》,《宋诗话辑佚》卷上,第329页。许甚至提倡李商隐与黄庭坚并参:“作诗浅易鄙陋之气不除,大可恶。客问何从去之,仆曰:‘熟读唐李义山诗与本朝黄鲁直诗而深思焉,则去也。’”许《彦周诗话》,《历代诗话》,第401页。朱弁则认为杜甫、李商隐、黄庭坚三者有渊源:“李义山拟老杜诗云‘岁月行如此,江湖坐渺然’,直是老杜语也。其他句‘苍梧应露下,白阁自云深’、‘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之类,置杜集中亦无愧矣,然未似老杜沉涵汪洋,笔力有余也。义山亦自觉,故别立门户成一家。后人挹其余波,号‘西昆体’,句律太严,无自然态度。黄鲁直深悟此理,乃独用昆体功夫,而造老杜浑成之地。今之诗人少有及此者,禅家所谓更高一着也。”朱弁《风月堂诗话》卷下,《冷斋夜话·风月堂诗话·环溪诗话》,第112页。
此外,得到肯定的还有杜牧、司空图、罗隐等晚唐诗人。如朱弁说杜牧:“杜牧之风味极不浅,但诗律少严。其属辞比事殊不精致,然时有自得处,为可喜也。”同上,第107页。许论司空图:“司空图,唐末竟能全节自守,其诗有‘绿树连村暗,黄花入麦稀’,诚为可贵。又曰‘四座宾朋兵乱后,一川风月笛声中’,句法虽可及,而意甚委屈。”许《彦周诗话》,《历代诗话》,第383页。评罗隐:“罗隐诗云‘只知事逐眼前过,不觉老从头上来’,此语殊有味。”许《彦周诗话》,《历代诗话》,第393页。如此等等。
与为晚唐诗人平反相呼应的是对于苏、黄的怀疑和反驳。蔡絛(?-1126)就东坡所说的“蔬笋气”问题展开了论述:“东坡言僧诗要无蔬笋气,固诗人龟鉴。今时误解,便作世网中语,殊不知本分家风,水边林下气象,盖不可无。若尽洗去清拔之韵,使与俗同科,又何足尚?齐己云‘春深游寺客,花落闭门僧’,惠崇云‘晓风飘磬远,暮雪入廊深’之句,华实相副,顾非佳句耶?天圣间,闽僧可士有《送僧诗》云‘一钵即生涯,随缘度岁华。是山皆有寺,何处不为家。笠重吴天雪,鞋香楚地花。他年访禅室,宁惮路歧赊’,亦非食肉者能到也。”蔡絛《西清诗话》卷中。他肯定了“蔬笋气”合理的一面,认为这是一种美学风格。曾季狸则谈到了自己在摆脱苏、黄等人影响后审美趣味的自我恢复,《艇斋诗话》:“予旧因东坡诗云‘我憎孟郊诗’及‘要当斗僧清,未足当韩豪。何苦将两耳,听此寒虫号’,遂不喜孟郊诗。五十以后,因暇日试取细读,见其精深高妙,诚未易窥,方信韩退之、李习之尊敬其诗,良有以也。东坡性痛快,故不喜郊之词艰深。要之,孟郊、张籍,一等诗也。唐人诗有古乐府气象者,惟此二人。但张籍诗简古易读,孟郊诗精深难窥耳。孟郊如《游子吟》、《烈女操》、《薄命妾》、《古意》等篇,精确宛转,人不可及也。”曾季狸《艇斋诗话》,《历代诗话续编》,第324页。此段话也见出苏、黄辞世以后,其影响力在逐渐减弱,审美趣味向多元发展。张戒更是首将矛头直指苏、黄,颠覆了苏轼、黄庭坚长期以来的崇高地位。《岁寒堂诗话》说:“苏、黄用事押韵之工,至矣尽矣。然究其实,乃诗人中一害,使后生只知用事押韵之为诗,而不知咏物之为工,言志之为本也,风雅自此扫地矣。”张戒《岁寒堂诗话》,《历代诗话续编》,第452页。吴沆记载的一段对话也颇具颠覆色彩:“环溪仲兄问:‘山谷诗亦有可法者乎’环溪曰:‘山谷除拗体似杜而外,以物为人一体最可法。于诗为新巧,于理亦未为大害。’仲兄云:‘何谓以物为人?’环溪云:‘山谷诗文中,无非以物为人者,此所以擅一时之名,而度越流辈也。然有可,有不可。如‘春至不窥园,黄鹂颇三请’,是用主人三请事。如《咏竹》云‘翩翩佳公子,为政一窗碧’,是用正事可也。又如:‘残暑已趋装,好风方来归。苦雨已解严,诸峰来献状’,谓残暑趋装、好风来归、苦雨解严、诸峰献状,亦无不可。至如‘提壶要沽我,杜宇赋式微’,则近于凿,不可矣。”吴沆《环溪诗话》卷中,《冷斋夜话·风月堂诗话·环溪诗话》,第133页。其中“山谷诗亦有可法者乎”一问,充满怀疑与不信任,而回答也很有意思:“于理亦未为大害”,言下之意是山谷诗害理;又答:“然有可,有不可”,可见对山谷是一种审视态度,这与早期许多诗人对山谷敬仰崇拜有很大不同。
既然连苏轼、黄庭坚这样的领袖人物都遭到质疑和否定,那些后生小辈们所受的批判就可想而知了。杨万里的老师王庭珪批评当时之江西派时说:“近时学诗者悉弃去唐五代以来诗人绳尺,谓之江西社,往往失故步者有之。鲁直之诗,虽间出险绝句,而法度森严,卒造平淡,学者罕能到。传法者必于心地法门有见,乃可参焉。”王庭珪《跋刘伯山诗》,《卢溪集》卷一,四库本。同时人陈岩肖也对江西诗派现状不满:“然近时学其诗者,或未得其妙处,每有所作,必使声韵拗捩,词语艰涩,曰‘江西格’也,此何为哉!”陈岩肖《庚溪诗话》卷下,《历代诗话续编》,第182页。
与王庭珪一样,陈岩肖对于“近时学其诗者”也是深为失望,认为这些人不知山谷妙处,只见皮毛。李正民指出江西末流好大喜功:“近世之士,喜广己而造,大凡赋咏则长篇短韵,欲与李杜争衡矣。此所以不能立名于天下也。”李正民《与祝师龙书》,《太隐集》卷六,四库本。想和李杜争衡当然没有什么错,关键是要增强自己的实力,“广己而造”,没有基础,连立名都困难,何谈与李杜竞短长。胡仔于江西末流之浅薄亦有体会:“近时学诗者,率宗江西,然殊不知江西本亦学少陵者也。故陈无己曰:‘豫章之学博矣,而得法于少陵,故其诗近之。’今少陵之诗,后生少年不复过目,抑失江西之意乎?江西平日语学者为诗旨趣,亦独宗少陵一人而已。余为是说,盖欲学诗者师少陵而友江西,则两得之矣。”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四十九,第332页。
对于江西诗派的指责尚多,兹不一一列举。实际上,自吕本中、陈与义、曾几之后始,江西派就走上了末路。正因为江西诗派已是穷途,才会有一批想有所成就的诗人“背叛”它,这批诗人被称作“中兴诗人”。
§§§第四节 中兴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