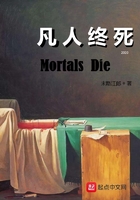◎文/陈艳涛
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他们是特殊的一个群体,年龄上,他们是一个世纪的见证者,所有的命运遭遇与种种政权更迭紧密相连。作为作家,他们更是中国百年风云的记录者,他们笔下,流淌着世纪中国交织的苦难、悲哀、喜悦,为今天的人们留下了巨大的精神遗产。
钱钟书:何必认识下蛋的那只母鸡
1998年12月19日,钱钟书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钱钟书的学问,可以渊博精深四字概之,有外国记者曾说,“来到中国,有两个愿望:一是看看万里长城,二是见见钱钟书。“他去世之后,一个热爱他的读者曾在报纸上撰文纪念,标题是《世界上惟一的钱钟书走了》这句话,可以代表所有对钱钟书有一点点或更多了解的人们的共同心声。迄今为止,钱钟书被学界关注评论的历史,已经有六十多年了。六十多年来,许多中外著名人士,都对钱钟书作了极高评价,称之为“二十世纪人类最智慧的头颅”。
钱钟书先生曾对一位英国人说过:“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这句如珠妙语是钱钟书为人为文一个最好的注解。他在学问的天地里怡然自得,晚年时更是重门紧锁,远避名利。很长一段时间里,在中国大陆几乎无人知道钱钟书的名字。后来“钱学”热衷,他也不以为然。一律谢绝各种祝寿庆功、纪念会或学术讨论会等社会事务,对这类活动,他有言在先:“不必花些不明不白的钱,找些不三不四的人,说些不痛不痒的话。”《人民日报·海外版》上曾发表过一篇纪念钱钟书先生的文字,大意是,对钱先生最好的纪念,莫过于潜心研究他的“钱学”和尊重他的淡泊。这也许也代表了钱钟书自己的心意。
冰心:爱在右,同情在左
1999年2月28日21时,中国“文坛祖母”冰心老人安详辞世,享年99岁,冰心是世纪同龄人,一生都伴随着世纪风云变幻,一直跟随时代的脚步,坚持写作了75年,是新文学运动的元老。她的写作历程,显示了从“五四”文学革命到新时期文学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伟大轨迹。她开创了多种“冰心体”的文学样式,进行了文学现代化的扎扎实实的实践。她还是我国第一代儿童文学作家,是著名的中国现代小说家,散文家,诗人,翻译家。她的译作如黎巴嫩凯罗·纪伯伦的《先知》、《沙与沫》,印度泰戈尔的《吉檀迦利》、《园丁集》及《戏剧集》等,都是公认的文学翻译精品,她的文学影响超越国界。冰心的纯真、坚定、勇敢和正直,使她在国内外广大读者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受到普遍的爱戴。萧乾说,80年代的冰心,还有巴金,是中国知识分子良知的光辉代表。
冰心的一生虽然历经战乱动乱,饱经风雨沧桑,笔下却绝少涉及丑陋邪恶。母爱、童心和大自然,是冰心写作的基本母题。“爱在右,同情在左,走在生命路的两旁,随时撒种,随时开花,将这一径长途,点缀得香花弥漫,使穿枝拂叶的行人,踏着荆棘,不觉得痛苦,有泪可落,也不是悲凉。”这也许是冰心对自己文字最贴切的描述。
1999年3月19日,首都各界千余人送别冰心时,没有哀乐,告别大厅回旋着大自然的音响,人们向安睡在花丛中的冰心,献上一枝枝鲜艳的玫瑰,大厅的正中,是冰心的手书,她一个世纪的遗言:有了爱就有了一切。
孙犁:大道低回,大味必淡
2002年7月11日,著名作家孙犁逝世,享年89岁。在孙犁先生的书房中,高悬着一幅“大道低回”的巨匾。
在11卷本的孙犁全集第6卷的扉页上也有他书赠友人的墨迹:“大道低回,大味必淡。”语出自《汉书·杨雄传》:“盖胥靡为宰,寂寞为尸;大味必淡,大音必希;大语叫叫,大道低回。”这也许恰恰是作家自己文化人生的体验和总结。大道不是直线向前,热衷躁进的,而是迂回曲折,沉思默察的;大味不是吃香喝辣,舌麻脑热的,而是尝尽甜酸苦辣而归于淡泊,淡泊而宁静,宁静以致远的。这是他一生的创作和做人的写照。
孙犁致力于把小说写成美文,不能说他的文字有何等震撼人心的力度,却由清丽至老到,都让人品味到何谓“大味必淡”。
他说得很轻松:“文章写法,其道则一。心地光明,便有灵感。人情人理,就成艺术。”其间追求的是清雅自然,如清水之出芙蓉。他一生都在求真求美,用文字创造着诗意般的境界。因而在孙犁的笔下,战争也没有血腥味,荷花淀在残酷的战争烟云笼罩下,人们仍然积极而诗意地活着。因为孙犁作品精粹,而且为人淡泊,远离名利场。作家肖克凡曾把孙犁称为“一面迎风也不招展的旗帜”。
吴祖光:生正逢时
2003年4月9日,戏剧家吴祖光,在北京去世,享年86岁。吴祖光出生于1917年,他17岁进入文坛,几十年从文生涯中,创作出《正气歌》、《风雪夜归人》等名震剧坛的名作。吴祖光受了特别多的苦,他76岁那年曾在《北京晚报》发表文章,一声长叹:“我的冬天太长了!”但他却是一个异常开朗、乐观、旷达的人。当别人抱怨“生不逢时”,他却在客厅挂上‘生正逢时”的条幅。
吴祖光经常给人题写的另一名言是:不屈为至贵,最富是清贫。他一生最不看重的是金钱,谁需要就可以给谁,哪儿需要就可以给哪儿。正因如此,他的一生,无论环境怎样险恶,他都在自己的精神世界中过得轻松自如。谢泳在《普及吴祖光》一文中说过:“吴先生令人肃然起敬的一面,正是他那种对正义,对公道的被人漠视敢于挺身而出的知识分子品格……”他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之一。
施蛰存:不死就是胜利
2003年11月19日,号称海派文化标志性建筑的施蛰存先生逝世,享年99岁高龄。也许,没有谁像施蛰存先生这样完整地见识和参与了20世纪中国新文化的兴起和发展,他几乎就是新文化的真实见证,如他的名字一样,施蛰存先生解放以后是不太惹眼的,犹如一股持续而从不断绝的水流,他由诗歌、小说、散文,再到教学研究、文史稽勾、碑拓研考等等,为人们留下了五百多万字的作品。
施先生曾说自己处世的方式像棉花,“受到外部挤压时,变为渺小无力。而一旦外部挤压松弛,它就弹性十足地恢复原样。棉花依然是棉花,妙在富有弹性。”
“文革”时,在牛棚的施先生有一句阿Q式的名言:“不死就是胜利。”在“文革”、反右中,他只有老老实实挨批认罪的份儿,而没有任何申诉辩解的机会,但后来说起这些往事,他总是十分平静:“没有啥,我照样看我的书,写我的书。”
施先生的一生犹如一部奇特的文化编年史。从鸳鸯蝴蝶小说到“新感觉”,从旧诗到现代诗,从翻译欧美文学到古籍整理,从作家到教授,从编辑到学者、遭际之多,时间跨度之大,都是无人能出其右的。施蛰存先生见证了一个世纪的风云变幻,他的去世,是一个时代背影的远离。
臧克家: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2004年月5日著名诗人、作家臧克家因病于北京去世,享年99岁。凡是读过中学的中国人,都对著名诗人臧克家的一首《有的人》记忆深刻。诗坛元老曾以活到120岁自励,不料却在今年元宵节驾鹤西征生于1905年的臧老,是对我国新诗作出卓越贡献的著名诗人。他从1925年开始发表诗作,创作生涯长达80年之久。成果之富,影响之大,被认为“几乎可以说就是一部足以现身说法的活生生的中国新诗史”。
他当年为纪念鲁迅而作的《有的人》,成为在广大群众中流传甚广,深入人心的经典。而今,用来送别诗人自己仍是最好的挽歌:“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