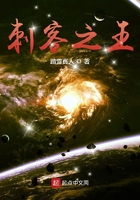ps:明天开始两更以上,一万封顶,终于大考完了,放松一个月……
“吼~啊!”
三四道白影轻啸着,手脚并用,迅速逼近树下营地。
月光清冷,洒在入侵者们身上,给它们披上一层迷蒙的薄纱。四下里,各种鸣虫仿佛受到惊吓,匿了踪迹,藏了音声,林间再度归于寂静。
“呼~哈~吼~啊!”
我微蹲枝叶间,耳边袅绕着古怪的轻嘶,眼下是氤氲茫茫,轻悄取出却邪剑倒扣手里,我俯身盯住树下那几道愈发清晰的白色影子,正准备纵身跃下,打它们个措手不及。
猛然间,一股刺鼻的恶臭粗暴打断了我的动作,令我强行止住几欲蹬开树干的双腿。这臭味十分古怪,将空气中馥芬的月桂清香祛除殆尽的同时,也熏得我眉头直皱。我皱眉并非因其太过难闻,而是因为它的“古怪”,怎个“古怪”法我倒说不清,含糊来讲,可以将它理解成一种糅合了诸多野兽体味的馊臭——有狐的骚味,也有狼的辛味;有虎的苦味,也有山猪的腐烂味。
(这段味道的描述是有讲究的,深山穷林里,每种动物都有其独特的体味,譬如上文所述的四种生物:狐是公认的“骚”,这种骚仿若一瓶过了年份的老醋,酸涩而刺鼻;狼的“辛”,不是中药理论上的辛,而是树木或血肉烧焦后散发的那种辛辣,有道是“打狼容易迷眼睛”,就是被这辛味刺激了眼睛;猛虎的“苦”,尤其是东北虎,据说虎受了伤会自主寻找草药,并将草丛里打滚,令身体沾上药汁,久而久之,这种草药的苦腥便浓郁了;山猪的“腐烂”最好理解,这些畜生是杂食动物,不管生肉腐肉都是来者不拒,吃腐肉不说,它们还喜欢在烂泥潭里打滚,打久了浑身裹满干泥浆,味道闻起来就像生了蛆的烂肉,老远就能闻见)
其中狐骚味最为浓烈,浓烈到我几乎要将那些个白影直接认作放大版的野狐。
可理论上来说,狐狸绝无可能长这么大——我下意识将它们与其身侧的大树比对,那个头,我估摸得有一米八往上!
它们嗷嗷呼着冲过树下,似乎没有发现我的存在。
我想了想,收起肘下的剑,背着剑盒,打算静观其变,若是这些不见面目的东西有任何威胁营地的举动,今夜,恐怕又要见血了。
很快,它们冲到营地近前。
雾绡般的月光,穿透婆娑树影,照及它们的身躯。
借着这阵光影,我总算看清了它们的真面目——原来是三四只猿猴模样的野兽,浑身覆盖着纯白绒毛,身材高大,面长马脸,脸上两只眼睛有如铜铃,冒着油油绿光,眼下是一对厚似熏肠的黑唇。
这些“猿猴”长得与人有几分相似,还有一头凌乱的“黄发”。更古怪的是,它们的后脚跟似乎长反了。
难不成……
盯着树下手脚并用踏过遍地朦胧月光的数道身影,我眼睛微微一眯,脑海里蓦地浮出一种生物:野人!
虽说身处无人区,我却从未听闻过蒙山有野人出没。
而且,野人应是浑身黑毛、体躯健硕如猩猩,怎会像现在这般,披着一身白毛不说,模样还奇形怪状,几分像人,几分又不像人。
“吼~啊~哈~啊~”
这时,只见那几只姑且可称为“白猿”的生物,忽而停下脚步,好死不死滞留在我的正下方。
一只首领模样、体型较之其他同类更为健壮的“白猿”抬起前肢,朝身后挥了又挥,口中发出“吼吼哈哈”的怪叫,仿佛在呼唤自己的同类。
俄而,我看见营地外,一处幽邃的草丛中,钻出一只体型矮小、狐骚味却更为浓烈的“白猿”。这只“白猿”手中捧着一块山岩,很吃力,一步一个脚印彳亍到“白猿首领”面前。
健硕“白猿”接过它手中的石块,又“呼呼吼吼”一阵,随后转过身,将石块抬高过头,作势欲要扔向营地中央的篝火。
这些鬼东西不愧为灵长类中的一员,智商不低,还知道“先熄光源、再做歹事”。
暗中戏谑一声“聪明”,我动作却没敢缓慢。
左手握住尚未打开保险的微冲,把背后的剑盒甩进右手里,想了想,还是不愿在今晚多作杀业,于是便没有取出二剑,只将合金剑盒充作“板砖”,照着首领“白猿”当头,一跃而下。
人尚在空中,一声大喝率先脱口而出:“敌袭!!”
“吼~哈~”
这声咆哮不可不谓响亮。
惊得皓月失色、夜雾退散、满山栖鸟飞遍苍穹的同时,也将树下几头“白猿”吓得浑身瑟缩。
尤其是首当其冲的健硕“白猿”。
只见其前肢一个抖擞,掌中石块猝然掉落地上。
下一秒,一块“板砖”狠狠拍在它的后脑勺上。
就听它“啊呜”哀鸣一声,身体不住往前踉跄。
“他奶奶的,什么东西?”
不远处的一顶帐篷里,忽而响起刘正国的怒骂,良晌,他端着一柄SCAR,目含隐焰,拧着双眉冲出帐篷。
他一眼便看见营地外这几道白花花的影子,面上惺忪瞬刻瓦解,迅速打开步枪的保险,一边避入身旁的灌木后,一边呼喊着司马宏的名字。
“司马宏,司马宏,起来,有……”
话到半截,他的目光忽然巡弋到我身上,嘴里的吼声一下就止住了。
“徐先生?”
下一刻,一声更大的呼喝接着上一句的话音传荡山林。
“什么情况?”
此时,司马宏迷糊而不失警惕的面容闯进我眼帘,手里握着一把徳制的G36步/枪,同样一眼就瞧见了营地外纷散站定的那几道白影。
我猜,“白猿”们现在铁定很蒙圈。
所以,我打开微冲的保险,并将剑盒护在胸前,防止那些“白猿”暴起暴起攻击我。
由于“白猿”首领还躺在地上,无法发出指令,其他“白猿”叽叽喳喳交流了半晌,也没能做出实际行动,只留在原地,对我们张牙舞爪,似是想借此恐吓我们。
“司马宏、刘队长,你们切莫开枪伤及这些猴子!”我一边防备地接近猿群,一边高声吩咐刘正国他们:“我担心这些鬼东西会记仇,你们留在营地警备,其余我来处理!”
话音甫一落地,倏然听得一声“呼沙”闷响。
藉由月光拂照,我隐约看见,半截迷蒙黑影从我面前一晃而过,腥恶的体臭尽然扑进我的鼻子,再定睛看时,眼前瞬时少了一样东西。
那只首领“白猿”!
“呜~吼~啊——”
身侧,再度响起它的咆哮。
我循声望去,只看见一张埋进灌木里的马脸,说来也怪,那张脸狰狞得明明能“止小儿夜啼”,脸的主人却胆小得令我诧异,脸上两颗大如铜铃的绿色眼眸,显明地写满了畏怯。
我以为它会就此馁却。
不曾想,这畜生蓦然抬起双手,亮出掌中两块黑乎乎的东西给我看。
月华旁溢,被风栓着撒在那两块东西上面——赫然是两只灰绿色的登山腰包,不知是哪两个倒霉蛋的东西。
“吼~呼~哈!”
首领“白猿”又发出一阵挑衅似的怪叫,
随后扭身冲进丛林更深处,眨眼间没了影儿。
身前一众“白猿”见首领溃逃,顿作鸟兽散,纷纷藏入就近的灌木丛里。
刘正国眉毛一横,就要开枪,却被我伸手制止:“你们待在这,我去追!”
说完,不及两人反应,我将手里的微冲扔在地上,屈腰钻入草丛,紧追“白猿”而去。
……
夜时的山林,不同于白昼的山林。
正所谓“雁门关外有人家”,就是形容类似这种温差剧烈变幻的地方。
老树蟠根错节,新树枝节横生,叶影婆娑,月光清冷,四下里寒蝉噤声,飞鸟不栖,满林子的静翳,唯有夜雾迷离。
轻嗅着空气中的臭味,感受它由浓到淡的距离变化。我想了想,认准新的方向后,加速追去。
这只领头的“白猿”狡猾异常。
它知道我在追它,竟命令自己的“猴子猴孙”在野林里乱窜,以致漫山遍野都是它们身上的体臭,若不仔细闻,或鼻子不如我发达的人,根本辨别不出哪些气味属于普通“白猿”、哪些属于首领“白猿”。
庆幸的是,我找对了。
手掌虚伸,我拨开面前朦胧的月芒,持剑的右手不停砍向面前遮路的枝丫。
良晌,不远处出现一道模糊的白色轮廓。
正是那只奸滑的“白猿”首领。
只见它提着两只包裹,“呼呼哈哈”地往前狂奔,不时将包裹甩上肩膀,并用起手脚。
但猿类的在丛林中的迅捷,是人类远远无法比拟的,我咬紧牙关追赶,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我与它之间的距离逐渐增加。
不会儿,它的身影眼看着就要消失在夜色中。
紧要关捩,我计上心头。
一边保持着呼吸的节奏,一边握正手里的短剑,闭上一只眼,站定屏息,瞄准……
“嗖——”
却邪剑破空而去。
在它划过弧线、斩开夜色的瞬间,我心中默念一声:“却爷保佑,见血而归!”
两息后,只听前头的“白猿”悲鸣一声,利剑入肉的“噗呲”接踵而来。
空气中,蓦然少了些许刺鼻的狐骚,而多了一点铁腥的血味。
我睁开紧闭的右眼,猛一吸气,全速奔向前方。
拨开身前拦眼的枝叶,我三步并作两步走,终于来到血腥味的源头……
那是一片略显空旷的草地,四处没有参天巨木,只有几颗似是营养不良、黄绿相间的矮树。
月光如凉水,洞彻草坪。
我探头看去,只见草上趴着一道健硕的身影,走近一看,正是那只“白猿”头领。
如今的它,不复方才的狂妄。
背心上插着一柄锃亮的短剑,剑柄处镌着一颗小巧的龙头,“白猿”的血,就顺着这枚龙头泊泊涌流,染红了一身纯白绒毛。
它已经出气多进气少、处于奄奄一息的状态了。
胸口与后背的起伏异常虚弱。
一双油绿的眼眸,低垂眼皮看着我,眸孔深处泛着些许乞怜。
我心无波澜。
虽然我“南洲徐”敬重生灵,但也杀伐果断。
抽出它背心上的短剑,我低喃道:“好走!”
“唰——”
却邪的剑锋划过软绒的脖颈。
血液更加拼命地往外流淌,直到在“白猿”身下积成一条溪流……
我踏过血溪,弯腰捡起地上的包裹。
抬头时,却听见林间响起一阵沉闷的枪声……
我猛地回头,望向营地的方位。
“发生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