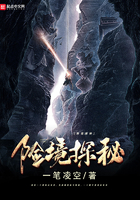他反对婚姻法则,否定父母对子女的权力,无疑,纪伯伦是个思想家,而且是个大思想家,有时他能发表许多独到的见解,尤其在《先知》一书中,他阐述了许多高尚而富有哲理性的教诲。令人遗憾的是,这一巨大的智慧被感情所支配,为驰骋的诗的想象所限制。他追求的只是反叛倾向,而反叛本身总是超越限度的。尽管他批判社会,却并未致力于对它的改良,而只是想摧毁它,因此,他的立场多半是消极的而不是积极的,而积极的立场要比消极的立场更难立足。纪伯伦具有由东方苏菲精神、由火样燃烧的感情、由《圣经》所启示的奇特想象力。在表达中,他作为一个艺术家胜过作为一个作家,他像是在用艺术家的画笔而不是用作家的笔进行创作。他擅长描写,不像一般作家和诗人只会因循守旧,写一些流行的肤浅内容。他的创作发自内心,以其才智创造出许多富于个性的画面。他的大部分描写都是从晨曦、黑暗、光明中得到灵感。
纪伯伦的文笔轻柔优美,如潺潺流水,具有迷人的音乐感,它以其绚丽的色彩和凝练的言辞令人目不暇接。纪伯伦不愧是海外文学的首领,也是阿拉伯文学中第一个采用这种水晶般的奇异风格的作家,尽管作品中有时议论太多,风格也过于纤丽。
艾敏·雷哈尼(1876—1940/1293—1359)
生平雷哈尼出生在黎巴嫩山区的法利凯村。幼时曾在邻村学校学习阿拉伯语和法语。后随家庭迁居纽约,在一所学院学习英文。他曾经商一个时期,并在美国一个剧团当过演员,后在纽约大学学习一年法律。由于健康原因,他不得不回到黎巴嫩,他在故乡学习到了阿拉伯文化知识。返回美洲后,他对宗教及宗教界人士进行猛烈抨击,借此扩大自己的影响。他把麦阿里的四行诗译成英文,从此受到美国各界的注意。他经常往返于美国和黎巴嫩之间,编纂阿拉伯文和英文书籍。他也常到阿拉伯各国、马格里布及黎巴嫩各地游历、讲学和作报告,与思想界知名人士接触。他于1940年去世,安葬在故乡。
作品雷哈尼是个多产作家,他用英文撰写了许多有关诗歌、历史和社会方面的著作。他最主要的阿拉伯文作品有:两卷集的《阿拉伯诸王纪》《纳季德近代史》《伊拉克心脏》,这些书籍记载了他在阿拉伯各地的见闻。《雷哈尼文集》一书是文章、演讲、散文诗的汇集,共数卷。《黎巴嫩心脏》一书是他在自己祖国的游记。《你们这些诗人》一书集中抨击了伤感文学。《极端与改良》是一部有关社会题材的著作。
雷哈尼深知黎巴嫩正在土耳其的统治之下呻吟,各方面离现代文明相距甚远。他看到美国是一个民主、文明和有企望的国度,在那里他贪婪而深沉地呼吸着自由的空气,心胸大为开阔。于是,“他最厌恶的东西是压迫和束缚”,“他理想的核心是自由地爱其所爱,恨其所恨”。伏尔泰、卢梭、艾布·阿拉·麦阿里等社会和宗教改革者的著作唤起了他心中的热忱,他深信,“进行革命的民族能赢得相当于甚至超过物质力量损失的文化和精神力量”。他更为荒谬地认为,除了信仰上帝和人类兄弟之爱外,一切宗教事务都是荒唐和虚假的。他读了达尔文关于物种起源的书,便毫无批判和鉴别地相信进化论。他了解了尼采关于超人即未来理想人的观点,便心悦诚服地信仰它。这样,他回到离别的东方时,带着他祖国同胞不熟悉的西方货色,并向他们兜售,人们称他为“法利凯的哲学家”。但他并没有自己的哲学,只不过是东拼西凑的一些观点。他的社会观点是:个人从无知和偏见中解放出来,国家从暴虐、殖民主义和委任统治下获得解放,东方和西方相结合,主张最广泛的人类兄弟之爱。他认为摆脱无知的方法是兴办学校,用文化、科学和艺术来照亮思想——挚爱与和平的基础。他说:“文学、教育和艺术是使科学凝聚起来的力量,科学能把先知的教诲和学者的智慧连结起来,它同时具有真和美的精神,和平、友爱、亲睦之光从中孕育而生。”人们想摆脱宗教的偏见只有通过互谅和宽容。
雷哈尼猛烈抨击暴虐、委任统治和殖民主义,主张正义与和平。他常到黎巴嫩、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游历,宣传他的观点,号召解放。他说:“争取真理和自由的疯狂,胜似安于受奴役地位的安稳。”1908年,土耳其青年党取得胜利,宣布了宪法,他从内心感到高兴。在小说《囚徒》中,他对阿卜杜·哈密德的残暴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揭露。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全力以赴支持自己的祖国,鼓动海外侨胞为祖国亲人捐款。实行委任统治时,他感到十分痛苦,曾毫无畏惧地公开宣布:“我们从阿卜杜·哈密德时代转入‘幸福的’委任统治时代,从公开的紊乱的暴虐转入隐蔽的有组织的暴虐,从承受尚可防御的棍棒、皮鞭的暴虐转人承受宪法条约的暴虐。”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兴起,巴勒斯坦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分歧加剧,雷哈尼起而维护自己兄弟们的权利,写了不少感情洋溢的文章,在许多公开集会上与犹太复国主义头目们辩论。他还竭力促进阿拉伯各国领导人之间的合作和团结。
东方和西方的结合,是雷哈尼为实现理想文明的奋斗目标。他了解东方和西方,认为前者的精神与后者的科学相结合,能把人提高到他所理想的完美水平。他说:“我希望在沙姆和阿拉伯国家看到先知的成果和学者的成果共结于一棵树上。”他愿意自己成为沟通世界两个部分的桥梁。他说:“我为东方和西方歌唱,这两大源流使人类复苏、强壮,肉体和灵魂得到净化。我为两者自豪,我为两者歌唱,为两者我可献出生命,为两者我工作、痛苦、直至死亡。”
雷哈尼主张人类合作和兄弟友爱,因为他们“是一个民族,共同的文化艺术,一个全面的宗教——其基础是神权和泛爱,把他们联结在一起”。他是全体人类的朋友,因此,他对人类说:“不论你多么富强,也不论你灾难多么深重,我永远是你的兄弟;无论在生活阶梯上你多么崇高,或多么卑下,我永远忠于你、信仰你、热爱你。”
这就是雷哈尼在东方所重复的西方科学解放复兴鼓吹者的言论,它曾获得许多人的赞同。但当西方的声音直接达于他们耳际时,雷哈尼的声音便被忽略,变得低微,几乎被时代所淹没。
雷哈尼从小喜欢冒险,长大后向往到各国游历。他最主要的旅游是1922年在阿拉伯各国的大游历。他到过埃及、希贾兹、也门、伊拉克和纳季德,在游历中收集各种资料,将它写进《阿拉伯诸王纪》《纳季德近代史》《伊拉克心脏》等书中。他每到一国,就要研究它的政治和社会形势,然后详细记录下来。美国《亚洲》画报曾载文说:“许多欧洲人游访过阿拉伯国家……但很少有人像雷哈尼先生那样对它进行正确的了解。”无论走到哪里,他都是国王公卿们的座上客,他与他们讨论问题,分析情况。他的著作观察细致、材料准确、叙事流畅。他描写的场最会使你有身临其境之感,详尽、自然、充满生气。
他写的都是“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亲身所感”的东西,这是他作品真实的基础。他从“最高来源”和“灵通人士”处获取资料,但他并不满足统治者的言谈,还广泛接触各阶层人民。他说:“我每到一个阿拉伯国家,都要接触一切人,从贵族、贝督因人、驼夫、士兵、商贾、政治家那里获得消息。”他的叙述流畅,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并随题材不同而变化,能使读者赏心悦目,尽管有时不免冗赘。
他死后才出版的《黎巴嫩心脏》一书,主要写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在自己祖国游历的见闻,包括了风土人情、习惯传统等。书中有一些比较极端的观点。
雷哈尼十二岁便离开黎巴嫩,没有打下坚实的阿拉伯语言基础。他最初在费城《向导》报上发表文章时,文笔拙劣,缺乏起码文法素养,不得不靠《向导》编辑为他修改润色。他意识到自己的不足,下决心努力丰富自己的知识。他在1901年给自己订的计划中写道:“我应该学习阿拉伯语:学习《需求研究》、阅读伊本·赫尔顿的著作;参考伊斯兰文化史、《修辞坦途》、哈里里的作品、优秀的诗歌和散文选,阅读乔尔吉·泽丹的埃及史,读完《旧约》。”他第一次返回黎巴嫩时,进了盖尔奈·萨赫旺地区的黎巴嫩学校,一面教英文,一面学阿文。他在写给朋友乔尔吉·泽丹的信中讲到了“学习语法的苦楚”,诉说了他在阅读法拉、穆巴莱德、伊本·玛利克和艾赫法什”著作时的艰辛,他希望以后能从“希姆叶尔和泰米姆人的语言中,以及从巴士拉和库法的学派中”解脱出来。这就是雷哈尼为掌握祖先语言而作的努力。他的努力虽然获得可喜成果,但并未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在他一生的著述中,始终掺杂着外语和土语的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