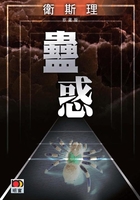群雄抵达西南领地已是半月之后,时值秋高气爽,本是十分惬意之时,奈何天干气躁,若要深入西南领地腹地新月城,须得穿越大片荒芜沙漠。这沙漠据说千百万年之前曾是海洋,每每风大之时,吹起黄沙,便会露出黄沙之下掩埋的海中生灵的森森白骨。也因此,这沙漠得名万骨窟,一路之上水源甚少,无有绿植,旅人要么陷入沙中,要么被蜃景带进万劫不复之地,要么迷失路途干渴致死。穿越沙漠非得有熟悉沙漠之人领路才可,若要去黑金领地,眼下也只有这一条路可走。
四人当晚在沙漠边缘略作修整,安营扎寨,正巧伯克涅手下佣兵提前到达,给几人送来饮水干粮,更有美酒许多,四人作敞怀饮,也算这一路苦旅中少许甜头。伯克涅送出报信用的飞鹰,知会西南八杰门人东海三剑已到,待得接引人一来,四人便要踏入大漠之中。
这夜甚是凄美,背靠沙漠边缘一汪清泉,遥见天边一轮红月,远处沙丘如山峦沟壑兀自沉默不语,暗影连绵,好一派寂静河山。刻利乌斯从前只在梦中见过大漠,那还是周湘芸给他喂下混元丹时的事情,想起来恍若隔世。那梦中的大漠竟与他今日所见如出一辙,毫厘不爽的相似。也是这样漫漫黄沙,也是这样的碧水长空,只不过那时是日头正高,此时是长夜委婉。
刻利乌斯一边饮酒,一边思念起自己从未谋面的生父生母,梦中他二人在这泉边对剑,一战罢,两人双双离去,空余刻利乌斯满腹疑虑。他瞧着水中的自己,蓦然想到,已是多久没有看自己的模样了?此时一看,不由得哈哈大笑,哪里还有半点索萨尼亚领主,当朝驸马的尊荣?说的好听些是落魄公子,说得难听些,不就是个化子么?看他金发凌乱,双目无神,脸上满是风霜,胡茬也成了胡须,俨然一副中年人的样子,这还好意思给人少年少年的叫么?他都觉得自己长得有些陌生了。
这陌生本该是熟悉,他想,自己年纪越来越长,越来越有大人的模样,也越来越像生父生母的样子。可他从未见过他们,对于刻利乌斯来说,他的父母始终是俄琉斯与皮辛垭,可他这个做儿子的,竟越来越不像他们,刻利乌斯怎能不觉得陌生呢?他觉得陌生,一边俄西里斯却宛若再见昔日自己的主子,杯酒下肚,他老泪纵横,言道:“老僧愧为圣灵之仆,老僧有愧啊......”刻利乌斯劝他道:“长老不必自怨自艾,人但凡能生,谁肯赴死?我父曾对我言讲,活着原是最为狠毒的报复,要活,还要活得长长久久。长老能有今日,能呼风唤雨,一洗前尘冤屈,不也正是因为活下来了么?”俄西里斯望着刻利乌斯,越看越觉得他果然是阿列西奥之子,不禁又是一阵哽咽道:“少宗主哪里知道,老僧那时......但不知少宗主是如何得生的?老僧曾听人言讲,阿列西奥老爷家眷老小乃至仆从的亲眷都没有放过,悉数问斩,小少爷还在襁褓中,也被扔进河里淹死了!”
刻利乌斯原本不愿细说过去之事,只是见俄西里斯哭得伤心,这才对群雄讲起自己的身世,阿尔忒弥砂听后似乎很是感同身受,面露缱绻又带无奈,她道:“我与少宗主一样,从未见过我生身父母。”伯克涅惊道:“乖乖,你不是狄俄涅那贼婆......婆婆的闺女么?”阿尔忒弥砂道:“我是我那不成器的父亲与他相好生的。我母亲对我说道,我那父亲脾气古怪刁钻,却是武功卓绝,受人敬仰。他年纪比我母大了许多,我母还年轻时本是师从我父,两人后来走到谈婚论嫁那一步,我母却越发受不了我父那脾气,两人动辄大打出手,我母不愿过那种日子,这才逃婚到了银雀宫中。”伯克涅又道:“那便是了,你可打哪儿来的呢?”阿尔忒弥砂哈哈一笑,问道:“大人以为我从哪里来的?”伯克涅脸一红,回道:“那还不是从你娘的肚子里......呸,你个小女子,问我这种问题,真是有伤风化,哈哈!”
几人都是一笑,俄西里斯道:“人人皆受圣灵灵体,没甚不能言说的。”阿尔忒弥砂点头道:“只不过我来的名不正言不顺,圣不圣洁不好说,总之是不太干净的。我母在宫中已有多年,是年在中立领地再遇我父,见我父那里居然有个不足月的婴孩。我父那人做不得父亲,我母便将孩子抱了回来,几位想的不错,那孩子正是我......”阿尔忒弥砂端凝着刻利乌斯,似笑非笑道:“少宗主的心境,我也不是不解。”
刻利乌斯心想,原来还有这样的过往,难怪阿尔忒弥砂对男子不甚喜爱,又说最恨的是负心汉,如此便能理解了。他也笑了笑,并未说什么。只是这时,伯克涅也不晓得是酒醉还是如何,捏着下巴沉吟起来,有顷他道:“说起孩子么,咱曾听人说,阿列西奥家搜出来那小少爷是给丢进河里了不假,可并没有淹死,而是教人捡了回去。咱也没打听过,谁知是真是假呢。”刻利乌斯苦笑道:“我那小兄弟若是活着,怎么可能不寻回来呢?一定是大家想着忠良不可无后,这才说些宽慰人的话儿罢!”俄西里斯又问:“若是俄琉斯老爷的公子还活着,少宗主怎么打算?”刻利乌斯不假思索道:“我将我有的全部给他,这本来就是他的,我不过代他活着罢了。”伯克涅笑道:“少宗主倒是仗义,就怕那小公子不领情哟。”
翌日午后,眼见得自沙漠中央而来,是两个阿卡贾巴商人打扮的白衣男子。两人骑着骆驼,一前一后,其后还有一队无人骑乘的驼队。驼铃儿做低语之声,引得众人思乡之情泛起,都是低头不语。这当口,两人之中一男子高声叫喊道:“好大的风沙,前面的兄弟们,请分碗水喝!”伯克涅面露喜色,回道:“但不知好兄弟你要喝几碗?”那男子道:“我有几匹骆驼,就喝几碗!”
伯克涅点点头,招呼大家起来收拾行装,他道:“暗号对上了!那是白头鹰前辈的弟子来了,咱们这就出发。”众人闻声都舒了口气,这大漠之中干燥,心情也烦闷,尤其午后之时,阳光甚毒,直教人头晕眼花,谁也不想在此多做停留。
两个男子来至众人面前,甚是别扭的给几人见礼,一人操着一口满是阿卡贾巴风韵的亚兰话对几人道:“英雄们来的好早!”刻利乌斯见那两个男子穿一身白衣,扎着头巾,面上也戴覆面,只露一双眼睛,怎么看都像是阿卡贾巴人而非是亚兰人。他不好意思过问,便悄悄问伯克涅道:“大人,白头鹰老前辈还有阿卡贾巴弟子不成么?”伯克涅似也是有些疑虑,他道:“咱与他家弟子还是头回见面,倒也不甚清楚,想来白头鹰他老人家屈居中立领地,收了阿卡贾巴门人也是有的。”
为首那男子见刻利乌斯与伯克涅交头接耳,他迎上前来给两人鞠了个躬,笑道:“两位英雄,晚辈确是阿卡贾巴人不假,但心与诸位是一般的,两位英雄可不要见怪!”来人笑的甚是爽朗,很有风度,刻利乌斯心想也是,阿卡贾巴人也不一定全是坏人,亚兰人也并不都是好人。两族之间虽多有嫌隙,此时应当以大局为重,暂且信他一回。这人又对另一男子叽里咕噜的说了几句阿卡贾巴话,那男子当即从包袱中取出一物来展示给大家观看,俄西里斯见此物后连番点头道:“不错,不错,这是白头鹰老前辈的佩剑。”几人再没有什么异议,随着两个阿卡贾巴人上了骆驼,向沙漠之中而去了。
路途之中,群雄问起西南八杰的近况,那会说亚兰话的阿卡贾巴人对群雄言道,八杰之中除却西奥波罗斯以外都去了,大多数武功也都失传。尚有弟子门人的仅余百步穿杨神弓手阿莱格农的弟子,大多做了猎户和杀手;鬼头刀客达斯希莫的弟子数人,不知去向。再便是西奥波罗斯门下十三剑士。西奥波罗斯是国之罪人,给赫斯曼抓走以前,过的就是深居简出的日子,世间根本无人知晓他这十三弟子的来路。
俄西里斯年纪最长,与当年的西南八杰接触最多,闻听这些人大多没了后继之人,心痛之余,更是大骂该隐不公。国王仍在世时,对武人的打压就很是猖獗,这还要拜斯基兰所赐。斯基兰商团来往于该隐朝各处,各地城主贵族对他那些恶毒行径大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江湖上的豪杰却揉不得沙子,总不能让斯基兰得偿所愿。皇后与马尔库克斯妄议朝政,说武人威胁皇权地位,国王老儿哪里能允?这才处处与武林作对。终于是自掘坟墓,长眠于敌国土地之下了。说到此处,那阿卡贾巴人却似是随口一提道,赫斯曼帝国对武人甚是尊敬,西奥波罗斯被抓走以后,帝国并没有为难西奥波罗斯门下弟子,甚至还要给他们许官做。
这话说得使几人都大为不快,伯克涅直言道:“自己的狗窝再臭,那也是好窝。别家的金山再高,那也不过是粪山!你们到底不是我们亚兰人,跟我们不是一路子的,真不知白头鹰老前辈怎的收了你们这些番狗做弟子!”两个阿卡贾巴人面面相觑,谁也再不做声,领头在前面行走。俄西里斯对伯克涅道:“大人这话说岔了,什么阿卡贾巴人,什么亚兰人,既然他二人是白头鹰前辈的弟子,身份又有什么干系?”伯克涅故意大声道:“噫!长老这话说的好生糊涂,叫俺好笑!”俄西里斯自然知晓他要说些什么,谁知伯克涅也故意不去问俄西里斯,反倒回过头来对后面的刻利乌斯道:“少宗主可知老哥哥我因何发笑么?”刻利乌斯没怎么注意听他二人说话,便道:“但不知为何?”伯克涅仰天大笑一声,回道:“长老把人和狗弄混了,怎么不好笑?”
这话许是激怒了白头鹰的两个弟子,一人回过头来语气很冲的说了些阿卡贾巴话,伯克涅兀自又是笑了起来,言道:“长老,你听听看,这不是狗吠是什么?”那领头的男子怒道:“伯克涅大人说话真是不中听,我二人到底也是阿卡贾巴人,伯克涅老爷百般羞辱,怕是有些说不过去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