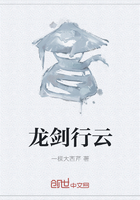他言辞恳切,丝毫无有居高临下要挟制什么人的意思。两人原是水火不容的宿敌,今日竟坐在桌前,谈论着一国之兴旺盛衰,委实有些不切实际的意味在其中。这当口,纳克索不容他细想,又一次追道:“你虽说着没有志向,不愿出世,旁人不知,我怎会不知你心底真正是如何想的?艾儿姐姐,你承不承认都好,咱们也是相识多年,你二人真正的脾性,我再清楚不过。我不止清楚你二人的脾性,我还知晓你二人的本是。咱们不是列昂尼达斯那种只认主子的忠犬,生杀大权要握在自己手上,这才是咱们这种人的本性。”
纳克索眼见的说服不了刻利乌斯,竟然将艾尔莉雅也一并奉承起来,将她加入这思虑当中,却不成想,正是这个举动,彻底使得刻利乌斯醒悟过来,他心道,你这厮,纵容手下妖女毒害了姐姐,眼下又来劝我带着她与你一道做事,哪个知道你嘴里说的是真是假?说什么生杀大权,哪个又知将来你对我二人是如何打算?再者说来,你这等样人,我怎么能与你同流合污?
他不愿耽搁了处决斯基兰一事,故而推脱道:“你今日所言,我权当是从路边酒醉之人的口中听来的戏言。如此大的事,你且容我细细想上一想,咱们眼下不谈自己的生死,还是先谈谈斯基兰罢!”
纳克索嘴角边若有似无的漾出一个不易察觉的笑容,双眼中确露出一丝凶光,一丝杀气。刻利乌斯在这世上多年,笑容见得少,倒是杀气从来逃不出他的眼睛。这杀气固然转瞬即逝,刻利乌斯也还是看出了其中的含义。他心道,有我做你帮凶,你无非手脚利索些。没有我,那我就留不得。眼下你还用得上我,且看斯基兰见了圣灵以后,你还能容得下我么?你与公主是一路货色,更甚于公主之阴险。我早知你对我不会轻易放过,看来你我之间早晚要有个结果的。
纳克索柔声道:“自然,自然。”他站起身来,走到窗边,推开了窗扇,午后清脆如露水一般的暖阳倾巢而入,他背对着两人,又道:“这是大事,唉,兄弟你谨慎些也是好的。我若能像兄弟你一般谨慎,说不定早就寻到我那可怜的妹子了。”
端凝着他的背影,刻利乌斯心下暗暗想道,你虚情假意,多说无用,与我在此做戏,当真无趣的紧,他道:“说这个做什么,令妹她如今一定过着寻常女儿家的日子,眼下这些烂事情,还是不要牵扯到她身上才是。”纳克索看着他,沉声道:“只怕这么大的动静,引也要把她引出来了。”这话很有些深意,刻利乌斯正待要发问,又有人叩门道:“启禀尊主,已经按您尊意布置妥当,尊主还有何吩咐,请示下!”
纳克索回道:“甚好,稍后我另有安排。”他又对席亚娜道:“你去给兄弟们发了赏钱,而后领着咱们事先选出来的人去候着罢!”席亚娜点了点头,临走前还不忘瞥了一眼刻利乌斯夫妇二人,他二人都是脊背一凉,目送着她离开,刻利乌斯才道:“她是记恨我当年杀了许多你手下人么?”纳克索道:“她与你我生在该隐又不同了,她家乡是个民智未开的小国,认死理儿而已......不过么,就是她有那胆子要怎样,兄弟你还怕她不成么?”
屋内只剩他三人,纳克索才道,原来他来此路途之中,机缘巧合之下收买了斯基兰商团中的小头目一人。自波克拉底的莫塞亚公国施政以来,商团早已然不再是从前做些强买强卖这种下三滥买卖的简单团体,而是坐拥数万人大军的私人军队。这支军队靠着欺行霸市来养活手下兵士,其背后之人就是波克拉底国公。国公初听政时,四处军心民意都不稳,还是靠着斯基兰商团的铁手腕才控制住了几分。再说斯基兰其人,他皇后的胞弟,地地道道的亚兰人,奈何他对他义父阿卡贾巴遗民马尔库克斯忠心耿耿,他义父被刻利乌斯斩杀之后,斯基兰继承衣钵,做起了帝国皇帝的附庸,成了披着亚兰人皮的阿卡贾巴人。
如今,这女夜魔要起义的风声越来越大,帝国和公国上下都提防着怕这人当真是传说中的加西亚公主。索萨尼亚是该隐要道,公主若想顺利抵达白石领地,非得过了索萨尼亚斯基兰这一关。帝国上下都怕波克拉底软耳根子,当真被公主说动,是以斯基兰在索萨尼亚驻守,一旦事情岔了,他立刻上了王都,拿下王都城。
纳克索通过他收买的线人对斯基兰放了话,若帝国有足够诚意,他纳克索和术士协会愿意奉上女夜魔及其手下人的名册,行军路线,计谋策略等等。斯基兰开价十万黄金以及中立领地之下的三座城池为筹码,纳克索欣然应允,明日夜里便要在商团驻地与斯基兰见面。
他道:“斯基兰在凯里翁城主城中布下夜宴一席,城外是他手下精兵约三四千人。席亚娜精通远东易容术,要她将你装扮起来,与我一道赴宴。宴上都是他商团中的头目和索萨尼亚的地方官,咱们将这等人一网打尽便是。”刻利乌斯颔首道:“说着轻巧,你我众目睽睽之下,如何动手?”纳克索轻描淡写道:“他既知我是术士协会,自然处处提防我下毒暗害他。明日你扮成我的模样,我另扮成他人样貌,他早见过我的画像,定是要小心着你,却不想下毒之人是我。我先毒倒宴席上诸多宾客,随后兄弟你与我一并将他制服了,令他签下招认他义父马尔库克斯与图满二人当年是怎样谋害权杖骑士团,谋害我父俄琉斯的罪状,再将他斩首就是。城外有我术士协会接应,城内有线人做引,将咱们送出城区。往后我这线人四处打点疏通一番,斯基兰手下大部分兵士都会降了我们,不降之人,绝不可能活着离开。”
纳克索将他大致的计划讲给二人听了,刻利乌斯觉得这计划十分冒险,纳克索却觉得万无一失,这是他筹划许久,绝无可能有差错。是艾尔莉雅问道:“你可见过斯基兰么?”纳克索略一沉吟,摇头道:“这倒没有。”刻利乌斯也道:“姐姐这倒问对了,你没有见过他,倘若他也乔装改扮,或者送个替死鬼来与我们见面,我们到时候深入虎穴之中,费尽周折只杀个替死鬼,本尊却还逍遥法外,岂不是功亏一篑么?”
纳克索思忖片刻,沉声道:“是有几分道理。事不宜迟,我去见一见我那线人,确保斯基兰明日一定赴宴就是。他若送了替死鬼去,咱们也送上一份假的图就是。这事只管交给我好了。”他似是还有什么要说,刻利乌斯便问道:“还有何事?”纳克索只是一叹,并没说具体有什么事,他突然看向自己那只空荡荡的袖筒,语气中带些哀怨呢喃道:“倒也没甚要紧的。觉得有些无趣罢了。想我这前半生做的尽是些见不得人的勾当,多一件少一件,我自己似是都不在乎了......”
他看着二人,露出一副两人从来都没见过的,甚是脆弱而落魄的模样。但他双眼之中,好像酝酿着什么,那什么是刻利乌斯极为熟悉的,好像在迷城地宫之中,他亲手杀了帕德梅以后流露出的怨恨。他道:“兄弟你......你不像我这样,我竟不知道该恨你还是羡慕你。”
刻利乌斯道:“你要恨我就恨罢!”他喝了口酒,直直的望着纳克索,道:“我从前确实欠你的不假,如今我自认问心无愧,对你也没有什么亏欠,你若仍是心有怨恨,我却也不能怨你。你要做你的大事,我不能助你,也无心与你为难,这次我替公主做事情,不也是替你做么?这件事以后,你我两不相欠了,你大可不必再来说这样的话。世上一草一木,都有圣灵冥冥之中的安排,但事在人为,怎样活那是你的事情,与旁人无干。”
纳克索眯起双眼,做了个很是耐人寻味的表情,回道:“你说的不错!我要记在心里的,来日我若做错了事情,定要想起你这句话来。”
夜半时分,刻利乌斯从梦中惊醒,那梦实在是真的不行,似乎身上仍带着梦中的气味。他梦到月黑风高一夜,他被什么人领着走进一片树林当中,林中落得遍地都是枯叶,一轮银白色的圆月在高耸入云的枝头挂着。他踩着枯叶,这一夜很静,除了风声和他踩着枯叶的声音以外,他什么也听不到。不时,哪里飘来烧木头的焦味,领着他的那人将他引到篝火前,要他双膝跪地。这时节,从火中走出一人来,那人竟然是艾儿。艾儿在他身边坐着,她已然不再是许多年前的少女模样,而是出落得款款大方,是当之无愧的淑女了。艾儿轻声细语的对他说着什么,他却一句都听不真切,唯独她的声音让他感到很是熟悉。艾儿似乎说完了话,突然惊叫一声,随着这声惊叫,刻利乌斯大汗淋漓的在初冬这夜惊醒过来。
他身边是熟睡着的艾尔莉雅,房里的火盆早已熄灭,就连青烟也无有了。窗外看不到月亮,他心道,是了,今日是月圆之夜。许多年前,他养母皮辛垭曾对他讲过,离家在外的旅人若是在他乡遇见月圆之夜,很容易发梦,若是不能从梦中醒来,就会被梦中出现的人带走。
他披上一件外衣,坐在窗前凝视着星河,突然想起出发前那工匠曾对他说过的预言。星象预示他在这东征之路上,必会遇见劫难。到现在为止,他还不曾遇到过什么性命堪忧的事件。那也就是说,劫难仍在前路上,说不定就是明日夜宴。
每当大事来临前,他仍像多年前的那个少年一样患得患失而又坐立难安。但他到底也长大了,总也还是淡定了些,他唯一放心不下的是他的枕边人。那工匠虽说,按照星象的昭示,艾尔莉雅的将来一帆风顺,可那一帆风顺的小船上,却没有了他的身影。他分不清自己到底是担心艾尔莉雅还是舍不得与她共同生活的岁月。他只能安慰自己,或许一切都不会发生,或许什么都不必担心。星河流转,说不定那灾星早已随风飘至别处去了。他再一次看向窗外的星辰,哪里飞来的一抹愁云如少女的面纱一样盖在上面,他叹了声气,蹑手蹑脚的回到床榻之中去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