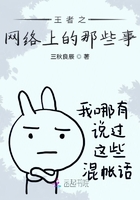PART-1
迄今为止,我听过最刻骨铭心的谎言有两个。
一个是我妈说的。
“你的压岁钱我帮你存着。”
一个是大学宿友说的。
“我男朋友特别靠谱。”
宿友的男朋友就读于导演专业,因为需要完成毕业作品,所以想找人参演他们自己创作的小电影。不幸的是,我天生不懂拒绝,遂被宿友说服,成为参演者之一。
其中有场酒吧的戏,需要打扮妖艳的女配角搭讪男主。并且为了听清台词,音乐得后期配,意味着我要在舞台中央自己瞎蹦几十秒,然后烟视媚行地窜到男主角眼前说:“约吗?”
现场,我还没来得及吐槽台词,和我演对手戏的男主率先破功。
“同学,你这表情不是要约我,是要砍我吧?”
众目睽睽下,他浓眉微挑、满脸揶揄,令我刹那间面红耳赤,连仅剩的那么点耐心都消失殆尽,遂掉头朝着宿友的方向走去。
“看,我说了吧?我真没有表演的天分,不然叫你男朋友换……”
话没完,却踩到七零八落的线,蹬着恨天高的我被重重绊倒在地,整个棚内天崩地裂。
当天,洋相出尽的我躺在地上呻吟,无奈灾难并未结束。被我绊过的那些线牵一发动全身,导致周遭临时的搭建物全跟着散架,我耳边只听得此起彼伏地“天!”“啊!”,接着看拍摄架迎头向我倒来。
我双眼一闭,憋屈着想象将来墓碑上将出现四个大字:拍、戏、而、亡。但没想,最终方潮救了我,就是刚刚那个嘲笑过我的男主角。
送方潮去医院的路上,我全程都用水光潋滟的眼神望着对方,直到他忍不住想从担架上挣扎着爬起来,忍着疼压着嗓。
“小白兔你长点儿心吧,别在脑子里意淫什么公主王子。这电影我也有份组织,要是有人受了伤,不得找我麻烦吗?”
接二连三被推向尴尬之境,我恼羞成怒,高声反驳他:“我才没有想那些乱七八糟的!听你口气,也不是王子的料啊?顶多大尾巴狼。”
大概我生气的样子特别让人过瘾,才令方潮自喉头溢出一声笑。
“我是不是大尾巴狼,小白兔试试不就知道?”
如果由我来选择谁是撩妹界始祖,方潮必定首当其冲。他并非我见过最帅的男孩,说话行事却莫名散发着令人心驰神荡的气场。
有的人坏,坏在心里。他的坏,坏在嘴上。
到了医院,医生说方潮的肋骨有几处骨折。“万幸没有血气胸,休养半个月应该就能下床。”
我松口气,却不得不充当半个月的送饭工,因为他住院谁都没通知,说怕家里人担惊。而真正让我甘愿充当送饭工的原因,也并非他救了我,而是我和方潮早就狭路相逢过。
九年前,我十一岁,还在镇上读小学。原本穷乡僻壤的地方,因为发现了一种稀有矿物而闻名遐迩。陆陆续续有矿商来镇子附近采矿,方潮的父亲就是其中之一。
方氏集团是当地著名的杰出企业,所以开采的规模比以往都大,镇上好多年轻力壮的中年男子都被高薪聘为矿工,周围还衍生出许多卖小食物的摊位,一定程度推动了镇子的经济发展。
那个夏天,方潮跟随母亲到镇上游玩,和我狭路相逢。
彼日,我披着家里的旧床单装公主,颐指气使地让其他鼻涕小伙伴为我采花。
“去,本宫要那朵最粉的月季。”
结果小伙伴的手刚伸到花茎处,就被外来者方潮制止了。
他小时的目光已经有剜人的能力,仿佛手边那朵花是稀世珍宝。而在我看来,它漫山遍野,不足为奇。
被扰乱兴致的我怒不可遏,真当自己是公主般地冲他呵斥:“有种报上名来?我要叫侍卫将你推出午门斩首!”
接着少年时代的他,用青涩的目光嘲讽了我。这也是后来方潮老说我喜欢意淫的原因。他对我的印象,依旧停留在公主戏里。
可我已然忘记当时的他还说过些什么,只记得他出现那刻,霞光漫了山坡。有个小小男孩,护着胳膊里小小的花,倨傲的同我对峙。
PART-2
方潮伤好以后,我的钱包却空了。
刚拿到的奖学金,在半个月里消失近一半。因为方少爷喜欢全聚德的烤鸭,一周三次也不嫌腻。
出租经过花鸟市场时,我的表情依旧苦哈哈。方潮看不过眼了,这才大发善心,下车买回一盆月季塞到我怀里,说是弥补我受伤的心,哦、钱包。
“有来有往。”
他说。
我看着怀里那些浅浅绿绿的花苞,嗅着自然叶香,突然原谅了他的资本家脸孔,只是我依旧开心不起来。
九年前,他抢了一朵原该属于我的月季。九年后,他以阴差阳错的方式还给了我。
这重逢看起来多么像命运啊。但我又清楚地知道,我们这命定般的重逢,或许没什么意义。因为他心里的那所房子,早已有了一个叫杜朵的主人。
杜朵,杜氏企业千金,方潮的青梅竹马。方家人统统不知道方潮受伤的事情,除了她,这已足够证明两人的亲密程度。
不过,杜朵身上没有大家闺秀气质,反而刁蛮任性。来探望方潮过后,临走前,还不忘剥削对方帮她修改论文。
“教授说要重新找个论点,否则这一门可能就要挂科了。方潮哥,你也不希望我挂科吧?”
她眨眨眼,眸里含烟。不柔,却醉人。
杜朵说的那个教授我知道,我和她同系,学管理,并且是那位教授的得意门生。刚入校时,我除了以高分亮相,还曾用一篇定性研究法的管理学论文打动过他。
“交给你了,小白兔。”
待杜朵一走,方潮大义凛然地拍拍我的肩膀。救命恩人的请求,我没有资格拒绝,于是第二天,我将自己帮忙找的新论点资料交给方潮,姿态略显骄傲。在其他地方没有的优越感,此时蜂拥而来。
我没她漂亮,没她家境好,没她可爱,至少我脑子不坏,并且还勤奋努力。不知道你,能不能看到。
很明显,方潮没有看到。因为在送完我一盆月季花以后,他又被杜朵一通电话召走。
再见面,三人晚餐,杜朵做东。
一是为感谢我伸出援手。二是为庆祝,她和方潮正式成为了男女朋友。
我惊诧、惊愕、惊吓,唯独没有惊喜。
怎能不惊吓?杜朵出现的第一天,我就从朋友那里打听了关于她的诸多细节。唯一记得牢的,是她有男朋友,金融系的魏行。那时我还庆幸,这样一来,她和方潮自然没戏,结果神反转,但我并不打算退缩。
从小的环境和遭遇告诉我,想要什么,喜欢谁,都要努力去伸手,因为上帝不会轻易将好东西放在我们这样的人手里。就算努力过还是失败,至少余生不会有遗憾。
简而言之,我打算告白。
挥别方潮与杜朵后,我冲到商场里,买下了自己中意许久的长裙。
裙子是水蓝色的,像白云朵朵的天空,突然被一道机翼划开而泄露的蓝。我曾一眼看中,却因为价格望而却步。为了人生中第一次告白,我铁了心。
第二日晚,我换上水蓝裙子,将和杜朵一样细长的头发放下,甚至扑粉描眉,精心等在男生宿舍楼下。
约莫半小时后,方潮出现。他穿着短袖,露出小麦色的健康皮肤,远远地晃着我的视线。我刚要上前,半路却杀出程咬金。
来者正是杜朵的男友,前男友,魏行,金融系有名的花花公子。他与方潮的个子不相上下,两人不知说了些什么,突然气氛就剑拔弩张。
我猛然记起方潮身上有伤,真动起手必然吃亏,赶紧冲了过去。可惜每到关键时刻,各种什么线什么草什么石头似乎总爱与我为敌,导致我在奔跑时踩到长裙,整个人猝不及防地向前扑去。
方潮是背对我的姿势,魏行却将我的一举一动看得真切。他在我即将跌倒时下意识伸手,堪堪抓住长裙的衣带,一用力,霎时听见空气里裂帛的声音。
挥霍掉所有奖学金买的裙子,才过一天的瘾,魏行就将其撕毁了。他怔怔地看着我这个狼狈的外星来者,惊恐非常。
好半晌,我才反应过来,他看的地方,是我暴露在空气里的肩膀。
“流氓!”
当着方潮的面,我捂住肩带破口大骂,完全破坏我想建立起来的淑女形象。
也许,这才是方潮始终无法喜欢我的原因。
因为杜朵刁蛮,可她从不讲脏话。她只会假模假式地威胁,或娇声娇气地拱手说拜托,任谁见了都心软。
PART-3
方潮这个人真是太狠心了。
长裙事件后,他不仅没对我稍作安慰,反而吐槽我生不逢时。
“这些事情别人做出来,或许能成为一段故事。而你做出来,那生生就是事故啊。”
看着他一口白牙,却老说不出我想要的话,我真怒了。当即推开他,愤愤地反驳:“对不起,我成为不了你想要的那种姑娘!”
接着不管身后的目光多像芒刺,转身就逃。
那段时间,我开始重整心情,只当自己从没去过表演现场,也没遇见过一个叫方潮的男孩,全副身心扑在一个特别难得的实习机会上。
学管理的,瑞士就是天堂。那边著名的金融公司每年都招实习生,要求是四国语言。我只精通两国,好在他们与学校是合作机构,每年有一个推荐名额,可适当放宽要求。
既然不能得我所爱,至少要努力得我所想,不辜负家里人的期望。
只是关于魏行这号人物,以前没在意过倒不觉得,真有了接触,却发现走哪儿都能遇见,晨昏定省般。食堂、小花园、综合性大楼等等……终于我忍不住回头和他搭了话。
“同学,你这样会让人以为你对我有什么想法?”
魏行一脸无辜,带着半分冷淡:“不用担心,见过你最辟邪的样子,任谁都不会产生什么想法。”
他逼我回忆,只能让我想起方潮对我的冷漠,眼角猛然耷拉。魏行却以为自己的话伤害到了我的自尊,遂略显失措地安慰道。
“其、其实呢,你也别灰心。有些人是雪,尽管洁白,可温柔坠过以后总会融化。有些人是水,看似平淡无奇,却总让人感觉不可或缺。”
尽管不清楚自己在不在他口中“水”的范畴。但我不得不承认,魏行其实并不“流氓”,甚至心地善良。
七夕节那天,寝室和过道上张灯结彩,跟过元宵一样。
窗台放着的那盆月季,竟然在那时开出一朵小花,我却无心观赏。因为一看见它,就会让我克制不住幻想,今夜的方潮和杜朵会怎样浓情蜜意度过。于是我只能百无聊赖地躺在床上玩手机,等到耳边甜言蜜语此起彼伏,我再也装不了镇定,起身去外边透气。
目前校园里唯一清静的地方大概只有自习室,我遁逃而去,坐在高楼旁静静发呆,后来干脆和自己的影子演起独角戏。
没想到,那出戏最后有了男主角。
魏行精通皮影,他爷爷是老艺术家,从小他一哭,爷爷就用皮影戏哄他,渐渐耳濡目染。当我见他用各种简单手势做出复杂的行为来,立时佩服得五体投地,对他的戒备顿消。
关于孤单这种情绪,我是这样理解的。
如果身边陪伴的人并不是心里所想那个,我依旧不会快乐。但若我发现世上还有一个人与我感受着同样的心情,我的不快乐至少可以减轻一些。
我也不想将快乐建立在魏行的痛苦之上,但谁叫我俩的心尖人,此刻正背着我们良辰美景呢?
不过,我的状况要比魏行好一点。我从没拥有过方潮,而他,是拥有过又失去。于是我一脸怜悯地拍了拍他的肩膀:“欸,我给你唱首歌吧。”
男孩的目光坚毅:“什么歌?”
“分手快乐,祝她难过,她找不到比你更好的。”
显然,我篡改的歌词让魏行很受用。他眼底透着琉璃样的彩色,稍稍抬高音量,甚至带些欢心地问我:“那么你的意思是说,方潮没我好?”
这家伙触类旁通的本领有些高,差点令我都转不过弯,思虑片刻后才得出结论,回他四个字。
“方潮除外。”
那些被岁月带来的人,无论他爱不爱我,我都舍不得将他用以比较。
因为我清楚,比较过后,我还是会发现,他的脸比谁都好看,眼神比谁都专注,气质比谁都清淡,气息比谁都香。
PART-4
我没想到杜朵会找上门。
她在女生宿舍楼底声泪俱下的痛诉我,插足她和魏行之间,只差没有马景涛附身般地长跪不起。所幸是夜晚,周边来往的人不多。
经过她断断续续的控诉我才知道,她和方潮不是真情侣,只是她和魏行吵架,为了让对方低头,才出此下策。
“杜小姐,你是不是弄错了?我和魏行只见过几次面。”
她将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那为什么我已经给他打电话了,他却说喜欢上你,不想再耽误我?!”
我突然想收回说魏行善良的那句话。
他哪里善良了啊!为了报复女友,竟然将无辜群众拖下水!
为避免杜朵再闹下去,我真背上声名狼藉的罪,遂立即要到魏行的电话号码,给他打了过去。
“魏同学吗?我是林月亮,就是被你‘撕破’衣裳的那个月亮。”
上帝作证,我这么说的第一原因,只为让魏行迅速反应过来我是谁,不料却让魏行在那边笑得颠倒众生,以及令这头的杜朵看向我的眼光顿然凌厉。
这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令我毛躁地搔搔头,头发乱得跟鸡窝般的我对着手机那头的人大吼。
“总之你现在立刻!马上!分分钟!到植物园来!”
挂断以后,我鼓起勇气瞟向冷冷盯着我的姑娘,忍不住吞咽了一下口水道:“有些事情电话沟通没作用,还是当面聊比较好。植物园里有张情侣专用长椅,特别适合约会哟。你们将所有误会解开,一定能重归于好。”
她和魏行重归于好,我才有机会和方潮白头到老。
对,方潮呢?被自己从小到大中意的女孩子利用,该有多心伤。
好像终于找到给方潮打电话的理由,他的声音听起来果然失落。涩涩的,小石子划在黑板上一般,令我抓心挠肝。
“你现在哪儿?”
他顿了顿才答:“足球场。”
我们学校的足球场大得反人类,背靠一座天主教外观的礼堂,高高的阶梯上,晚风轻抚。
方潮始终愁眉不展,我去以后,他的眉头仿佛锁得更深。我努力找话题与他说,例如那盆月季已经开花啦,娇艳欲滴。见他没反应,干脆说起冷笑话。
“有个人没有酒精过敏,也就是说,他没有酒精,就过敏。”
“有一天,我在宿舍吃着吃着饭,突然停电了。我继续扒拉了几口饭,灯又亮了。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扒拉拉能亮?”
前两个,方潮都没什么反应,直到我说完最后一个。
“曾经我暗恋的男孩告诉我,如果我喜欢他,千万别说出来,因为愿望说出来就不灵了。这道理,我不是很懂……”
方潮突然正头,用幽深如湖的眼神望着我,启唇:“如果你喜欢我,千万不要说出来。因为愿望说出来,就不灵了。”
挖坑给自己跳的事儿我可真能干,他这算是以无声拒绝了我吗?怎么办,好想哭。
没几秒,他突然朗声大笑:“唉,仔细想想,也就不想你去瑞士了。因为你一走,就没人能再逗我开心。”
他温和地望着我,表情真假难辨,却还是令我难以控制胸口剧烈地跳动。仿佛有什么话叫嚣着要从喉头蹦出,方潮的手机适时响起,是杜朵。
她在那头情绪很不稳定,隔着听筒声音,我都能听见她凄惶的哭诉。我和方潮赶到植物园时,魏行已经不在了。她蹲在地上,眼妆花得不成样子,似乎哭得过于凶狠,进入了失恋过后的呆滞状态,喃喃自语道:“他走了,他真的走了。”
语毕,我才看清她手里把玩着的是一个打火机,旁边还放着一小瓶打开了盖子的汽油瓶。
方潮的面上忽然呈现从未有过的严肃,他小声警告我:“朵朵小时得过抑郁症,我把打火机夺下来之前,别离她太近。”
后来在所有冰冷的时光里,每当想起他这句话来,我就能满血复活。因为我喜欢的男孩,在发现危险的第一个念头,是保护我。那这世上,还有什么值得我恐惧?
可惜当天的方潮还是慢了一步。
精神恍惚的杜朵见有人靠近,条件反射地打燃火机,汽油一点就着。所幸他手长,千钧之际将杜朵拉离开事故现场,却没在最佳时机将火势扑灭,导致园里的几颗珍贵植物尽成焦炭。
PART-5
我们三人被带去保安处的路上,杜朵已恢复神智。
她全程揪着方潮的衣袖,好像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眼泪走一路掉一行。方潮递给她一个安慰的眼神,不知为何,我的眼皮竟莫名跳了跳。
他俩被率先叫进去询问情况,等了许久,才轮到我。可等我进去,面对的人已经是劈头盖脸一顿责难。
“林月亮同学,你知不知道着火的范围若再大些,是要追究刑事责任的?”
我眨眨眼,一脸蒙。
“知、知道。可放火的人不是我啊?我只是旁观者而已。不,我也不是旁观者,我和方潮本想救火,无奈……”
惧怕被误会的我语无伦次,毕竟我还没圣母到要为了一个刁蛮千金背黑锅,但校长相信。
“已经有两个人证,你还想抵赖?作为学校全优生,出了这样事故,上万人看着,你说,我究竟应当怎样处理?”
我的注意点却没在他会怎样处理我这件事上,而是他口中的“两个人证”,将我打得形神俱灭。
“您说……什么?两个人证?”
“杜朵和方潮都已经承认,你因为不满杜朵抢了男朋友,激动之下行此极端。”
我立时体会到什么叫晴天霹雳,身子一软,真真切切地跌坐地面,喃喃道不可能,直到方潮再次被叫进来,与我对峙。
校长问他,纵火的人是不是我,他连犹豫都没有,轻巧地吐出一个字:“是。”
就像大海中央,唯一指明的灯塔被熄灭,我心如死灰,微微仰头看他。
一般做错事的人,不是都不敢看对方眼睛的吗?可为什么,当日方潮的眼,竟比任何时候都要亮。他的眼角甚至带了微微的笑意,黝黑瞳孔里划过一丝莫名快感,好像为了这一刻,他已然等待太久。
大概见我家里条件确实不怎么样,平常的表现也过于优异,导致好几个教授一起出面帮我向校方说情,才免去赔偿之责。条件是,我在去瑞士的名单里被除名,以儆效尤。
系主任从校长办公室出来,满眼痛惜地对着我摇摇头:“你呀你,原本你走出国门是众望所归,现在竹篮打水一场空,怎么对得起你的父亲。”
他话落,从来坚强如磐石的我霎时热泪翻涌,当即提起勇气,要冲进去再为自己正名,方潮却在那个当头稳稳拦住我,语气成冰说了六个字。
“人在做,天在看。”
无声中,仿佛有人扼住我的喉咙,让整个宇宙颤抖。
资优生为情纵火的传闻在校园里疯传后,魏行激动地要拉我去找校长,说要帮我作证。
“我去见杜朵时,她的确有拿出打火机威胁,但我不知道她的病,以为故作姿态而已。”
魏行说到激动之处,我却在那个当头轻轻抽出手,拒绝。
“你别去,方潮说真相是什么,就是什么。”
他起初目瞪口呆,接着用恨铁不成钢的眼神剜我一眼,骂我蠢。
“难道喜欢一个人真有那么了不起?葬送自己光明的前途也在所不惜?那不叫喜欢,叫痴愚!”
察觉到肩膀处的力度,盯着那比我还愤怒的一张脸,我崩溃在地。
“魏行,你不懂。我哪有资格对他谈喜欢啊?我哪有。”
PART-6
我说过,九年前,来镇上采矿的大户正是方家。
方父作为集团第一继承人全权负责此事,不料遇上前所未有的暴雨导致山体滑坡,部分工人受伤。工人大多本地找的,我爸也在其中。
事故发生后,方潮的父亲挨家挨户寻访,该赔钱的赔钱,该慰问的慰问。无奈有人眼红死者家属的赔偿金过于丰厚,遂联合我爸和其他一些轻伤患者,要求方氏集团同样给予巨额赔偿。我父亲生于乡村,长于乡村,没迈出过镇门,文化无几,到底没禁住煽动。
偏偏方父的性子刚正不阿,不接受威胁,镇里面的工人没了法子,开始不断地打电话骚扰方家。直到那一次,方潮他爸恰好驱车在高速上,突如其来的电话声使得他爸一时分神出了意外,再也没醒过来。
后来,我爸和其他工人被告上法庭,导致平常对我前呼后拥的小伙伴,都在一夜间将我孤立。有那么些日子,我恨过我的父亲,恨他的无知与小市民,我甚至在某个激动的时刻对着我妈大吵大嚷。
“我才不会去看他!我没有这样的爸爸!”
不出意外遭到我妈凌厉的一巴掌。
“你爸这么做,还不是因为你!”
那时,小学要选派学生参加国家级奥数比赛,若拿了名次,可直升重点中学,不过需要集训一段时间,费用不菲。我爸这个老实的农村男人,一心为了我的前途,这辈子第一次出卖人格,却没想间接成为害死方父的刽子手。
所以,方潮是故意的。
故意接近我,故意逗我喜欢他,故意让我因得不到所爱煎熬,也故意用同样的方式以牙还牙。
而我,也是故意的。
故意装作不知道他的企图,故意什么都听他。我以为这样,或许能将他从小缺失的爱弥补些回来,或许能用实际行动真正化解这段纠葛,但我好像,太过天真。
事到如今,我没资格怪我爸,也没办法怪他。如果恨我能让方潮快乐,那就恨我。因为他的余生若是不快乐,我的余生,也不会了。
END
毕业后,我没有立即工作,而是选择去贫困山区支教。似乎这样,就能洗轻一点罪孽。讶异的是,魏行也要去。
他说如果当日好好与杜朵谈判,说不定就没有今日的局面,我也可以顺利去瑞士。所以他欠的债,也要还。
至于究竟什么原因,我没有追问,因为我还是无法控制自己对方潮的难以忘怀,尽管我对他的一切,早已没有期待。
临离开前,我偷偷给方潮打过一个电话。意外的是,他接了。
听筒两边良久无话,直到我打破僵局。
“我只是想问问,那天在足球场,你说不想让我离开,因为未来不会有人能逗你开心,这句话,是不是真心的?”
做不了你的情人,至少能做你生命中的唯一,我也感激。但他不留情面地否认了。
答案似乎早就猜到,我在他看不见的地方微微笑,后来还企图让自己的失败看起来没那么明显,嘴硬地照电影台词说道。
“方潮,我希望你没有说谎。我希望在你的内心深处真的对我没有丁点儿感觉。”
“你最好对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因为但凡你有一点,你将会后悔你什么都没对我说。”
挂断电话之际,我并不知道,有人的眼眶因为我的那番话,被雾气厚厚蒙上。
那个人,一生只说过两次谎。一次是为了将我送进地狱。一次是为了将自己不该有的情愫埋葬。
如果可以,我希望永远也不知道真相。因为彼此喜欢却注定无法相守的爱情,比他不爱我更让人绝望。
只是,当我走在乡间小路上,一个小姑娘指着我怀里抱着的那盆月季,惊喜地叫出了两个字。
“情书?”
我错愕:“什么?”
她的笑容甜甜,说起话来少年老成,像极年幼的我。
“我姑妈可了不起了,她是植物学家哦。她曾经告诉我说,这种粉粉的,颜色层次极其规律的花朵,不是普通月季。它有个浪漫的名字,叫情书。如果将来有男孩子送给我,说明他是真的很喜欢我,只是不敢对我说。”
然后,在那一天的旷野之上,周围的树木和风曾听见过。
有个女孩,失声痛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