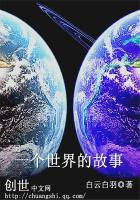满地的鞋子。
纳蜜的脸,微微绷着,神情淡淡的,就像丝绒的鞋面,平整、贵气。这个品牌的鞋子,丝绒平底款做得最好,是那种偶然扫见稍有惊艳的感觉。
服务员倒是一点也不嫌烦,左一双右一双地介绍,声线柔软亲切,单腿跪在地上为母亲服务,母亲显得颇不自在。她是穿惯地摊货的人,跑到名牌云集的太古汇买鞋,是犯罪好吗。
“太贵了。”母亲低头试鞋,忍不住对她耳语。
纳蜜假装没听到,继续陪着母亲试鞋子。
她喜欢宠着母亲的感觉,给她买金戒指,好让她在搓麻将的时候被牌友们惊呼晃眼睛晃眼睛;给她买美容白金卡,好尽可能抚平她脸上或者心里重叠交错的皱纹。母亲太不容易了,自父亲走后,她们母女相依为命,人生惨淡。天资不错的母亲,曾经文艺小清新的母亲,终于被岁月风霜塑造得粗枝大叶、庸俗市井,经常失度胡扯,说些有的没的,或者笑得花枝乱颤。一见到打折商品有用没用都会疯抢,买到便宜货就像捡到宝那么高兴。成为地摊之外随便到哪儿都被嫌弃的那种人。
服务行业的人见到她,就是三句话:没有加大码。这个很贵的。我们店全年无折扣。
好在母亲还有她。
她的确非常优秀。从小就是“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刻苦认真,成绩永远班级前三;考试因为点错一个小数点会自责得想哭;放学以后做完作业就帮妈妈摘菜、拖地;星期天下大雨会跑回学校教室关窗户。
总而言之是那种叫大人放心的好孩子。
可是,架不住时代变了。
长大之后,她发现她这一号人并不吃香,简直就是生不逢时。
然而她的特点便是没时间顾影自怜,迅速调整好人生方向,锻炼出强大到混蛋的小宇宙。哪怕前程伸手不见五指,她也坚信会有开挂的一天。
只是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她这样一身休闲打扮,全身上下无一名牌,更没有拎什么会默默介绍主人品位的包包,还带着一个全身淘宝感十足的老人,服务员为什么还那么耐心呢?
为了若干服务员轻慢母亲,她没少恶语相向。
她看了一眼那个黄毛小丫头,并表示把鞋子包起来吧。
接下来她刷卡,埋单,不看母亲着急并想制止她的眼神。
走前,黄毛丫头双手把装着鞋盒的购物袋提到她的面前,交到她手上,小声赞许道:“夫人真是好品位,这双鞋断货三周了,今天就只进了这一双。”说完不忘莞尔一笑。
“你的气场好大。”黄毛丫头最后补充了一句。
明知道是恭维,听上去还是舒服。
舒服地花钱,是商业王道。
不过,夫人,哪门子的夫人。她一个人生活久了,记忆细碎而且绵长,这样子一个人进出,竟像数学公式一样固定下来了。
她已经变成了一座城池,外面的人进不来,她自己也出不去,固若金汤。
纳蜜回到家中,天已黑尽。
她的这套房子属于地段最好的高档小区,只有四幢深啡色的公寓楼,看上去貌不惊人,但是楼价奇高,管理到位。在任何房地产中介公司都看不到挂牌销售,只因有人出让,立刻有人全价购进,根本没有挂牌的空间。
一是闹中求静,二是有花园回廊、恒温游泳池。重要的是住客都是体面人,当年一套公寓的价钱足可以买城郊的一幢三层别墅,令许多人望而却步。
房子也有血统高贵这一说,因为从来就没有便宜过。
这样的东西无论多么过时陈旧,总让人有一种说不出的优越感。
纳蜜打开落地灯,这灯压根就没有设计,腰身笔直如一棵小白杨,头上顶一个大白碗——乳白色的灯罩,碗口向上,照天不照地,天花板上铺了一层柔光。屋里的人却是不晃眼睛的。
灯下的家具都是极简风格,禁欲系设计。
和落地灯并列的是一株盆栽的仙人柱,浓绿有刺,算是植物界的超模,瘦高而没有表情,忘记浇水也可以傲慢地活着。
客厅里有一面墙壁是高饱和度的莫兰迪色,上面孤零零地挂着一张风景摄影图片,并没有所谓让人惊艳的视觉冲击力,如同放大的最普通的明信片。只是下方有一行字标明:美国佛蒙特州。仅此而已。
丝绒质地的沙发上搭着松软的胖针织毯。
一看就是独居女人的偏好。
纳蜜把手提包信手放在地上,换了拖鞋,去洗了澡。
再来到客厅时,穿了淡粉色的棉质睡裙,由于洗得太旧,细软得像什么都没穿。真好,这是她每天最期待的时光。这样舒服地坐在面对阳台的沙发上,透过落地门的玻璃,她可以看到远远近近的灯光,这是城市的缩影,有一点点迷离和捉摸不定。
似乎又有无限的传奇故事。
如果是台风来临的坏天气,感觉全世界都在受难,唯有自己幸福地活在一个安全岛屿,随时都可以睡去。
秋风拂过,末尾处有一丝不为人察的寒意。
沙发一旁有一辆金色的酒吧车,上面立着挂着各种各样的酒,同时也倒吊着几个高脚杯。琳琅满目的感觉,是唯一富贵的点睛之笔。
茶几上,放着她昨晚喝了一半的二锅头,对,就是小瓶的红星二锅头。她熟练地打开一袋真空包装的红油猪耳,连酒杯都不需要,一边对嘴喝小二,一边用手提出油腻腻的耳丝放到嘴里,味道不是一般地好。
什么威士忌,贵腐,香槟中的大地之魂,装的时候自然得以它们为偏好。
还有手工切片的西班牙火腿、哈密瓜或者杏仁饼,这些套路版的下酒菜,她听都听烦了,只是般配,哪有那么好吃。
但其实,此时此刻才是对自己最深刻的宠幸。
龙虾也是,有什么好吃,就是贵嘛,领班会跑过来递名片。
母亲胃口大开,吃得满面红光。她看着她吃,心想母亲倒是一个简单到幸福的人,她身上发生的事,半点落到别人头上,至少也是愁眉不展。只有她吃得下睡得着,还很疑惑地问她,你怎么不吃?好好吃哦。
每一次见面的模式,基本都是先购物后吃饭。
纵使有些心烦,她也是不能跟母亲住在一起的。她们到底是两个世界的人,而且她也一个人住惯了。
刚才买完鞋子以后,便去惠食佳吃饭。
惠食佳是个小店,正宗的老广东粤菜。店面小小的,虽然侧立街边,然而车速稍微快一点都发现不了,也没有什么精致的装修,却仍旧不妨碍它门庭若市。里面的女服务员没有胖子,统一穿月白色无领偏扣的唐装,自梳女一样的打扮,脸上自带些许清高的冷漠。但不得不承认,服务还是相当周到、勤力的。
本来是去吃鸡汤烫鱼片的,滚烫的鸡汤把超薄的生鱼片烫熟,味道鲜美。
母亲说,请问有擦手的毛巾吗?刚才试了半天鞋子,当然要擦手。
服务员说没有。
可是隔壁桌上的客人,每一位手边都是雪白的湿毛巾,躺在白色陶瓷托盘上。
服务员解释道,他们点了龙虾。
这就是差别服务嘛,好的店就是有这样的细节。吃一盘蒜蓉菠菜需要用湿毛巾吗?成本本身就是利润。
纳蜜便道,那我们就吃龙虾套餐吧。
母亲马上就一副嫌贵的表情,刚想提出异议,被纳蜜用眼神制止了。
为了不丢面子,享受到雪白的热毛巾,人生都是因小失大。
父亲在政府部门曾经分管的那一大块资金,按照他指定的银行存款,因此得到二十万元的好处费,属于职务犯罪,判刑十二年,还没有坐满时日就离世了。
剩下张皇失措的母亲,方寸大乱,似乎跟好几个男人有过牵扯,无论是那些奇怪的男人上门,还是母亲满怀希望地跑去同居,结果都是无疾而终。随着年龄的增长,她身上的校花气质流失殆尽荡然无存。看到她越来越乖巧的神情,越来越会看男人的脸色行事,然后就没有然后了。纳蜜的心里就像插了一把刀。
却又没有任何办法。
最终母亲变成了纳蜜的一件行李,碍手碍脚又没法丢弃。
刚才跟母亲分开的时候,她叮嘱母亲参加朋友孩子的婚礼,要穿得简单整洁,不要红红绿绿地突出自己,但是包包和鞋子一定要讲究,份子钱更加不要纠结,不要让人看低了。直到把她送上神州专车,纳蜜还在喋喋不休。
她们是典型的母女角色倒置。
她这是有多想当母亲啊。
纳蜜扬起头来,又喝了一口小二。
瞬间一条火龙从嗓子眼直接蹿到心底,真心痛快。她喝酒,纯粹是为了助眠,从年轻的时候开始,她就神经衰弱。
在最深的夜,喝最烈的酒,忘了我是谁。
第二天清早,纳蜜醒来,先坐在床上发了一会儿怔。
然后才下床。
穿着朴素的外套去上班。
车也只不过是黑色的凯美瑞,过目即忘。她今年四十六岁,看上去是最普通的上班族,有一点年纪,有一点位置,脸上也有一点步步为营的沧桑。
她的人生也的确是这两年才开挂的。本来她在一所财贸大学教应用英语,半死不活,穷得冒泡。后来学校开辟出一块地方搞再教育培训基地,谁都不愿意去。人都是没有远见的,守着大学都没发财,成人教育的出路在哪里,根本就没有人知道。
系里动员她去,就是把她往外推嘛。
她也习惯了,从小就没有人重视过她。参加工作以后,自己从颜值到才华都不过平平,又不懂哄领导开心,谁还会把她当作一回事。
因为没人肯去,所以纳蜜在基地很快就担任了主要工作,也是承包人。
人最少的时候只有她和梁少武两个人。
那时候梁少武刚结婚不久,每天惦记着往家跑,恩恩爱爱你侬我侬。加班干活这种事,就落在纳蜜一个人的肩上。
基地的位置偏西,墙外有一条主干道,昼夜奔驰的都是些大货车,喧嚣而且尘土飞扬。培训大楼是一座五层旧楼,常年被粉尘袭扰,自然是灰扑扑的,也没有电梯。楼的后面是闲置的后花园,杂草丛生,衰败凄清。
据称这里也是因为常年租不出去,学校才只好自行消化。
闲暇的时候,纳蜜请了学校的花工,贴补他一些劳务费,和他一起重新修整后花园。梁少武不肯出力,不是坐在办公室里织粗线围脖贴补家用,就是在一些私营小店里接活,计件收费。少武的优点是贪财,怕老婆,缺点当然也是这个。所以原科室的人不待见他,把他踢到培训基地也是情理之中。他并不生气,整天笑嘻嘻的。
还说,纳蜜,你这个人哪都好,就是总挂个脸。
这里这里,这里还没扫干净。他总是一边织围脖还一边指指点点让人火大,到底谁是负责人啊。
你们系就是谁都不要看你挂个脸,才齐心协力把你弄到这来的。
纳蜜不理他,一直和花工侍弄后花园。当时的内心戏是,都已经这样了,生存环境总得搞好。当时她住学校的筒子楼,厕所伙房都是公共的,走道里堆满各家各户的杂物,每天就是伴随着笑声骂声吵闹声跳着脚走路,让人完全透不过气来。
既然基地备受冷落,打造一个自己的空间也不错。
当时谁又能想到,也就是在这几年,似乎是一夜之间,突然各种文凭、证书、本本儿变得吃香了,除了以前的成人教育、夜大课程之外,厨师、烘焙、会计、电脑、美容、月嫂、病人护工、按摩师、茶道花道等,只要能想到的全部有人教,有人学。总之每一个找工作的人,面试时不拿出若干小本本往桌上一摊,都不好意思开始自我介绍。
要学习,拿本本儿,就得有场地。
再教育培训基地虽然旧,但是干净整洁,现成的大教室。
还有漂亮的后花园。
主干道铺了柏油路,增加了多条公共交通线路。
变成了理想的学习场所。
最关键的是,再教育培训基地本身就是教育部门的分支,有开出各种文凭的途径和资格。这是独享的红利,外人手伸得再长也够不着。
要不就合作、协办。
比如某个模特公司,要求合开礼仪研修课程。
他们负责难度最大的生源和管理,纳蜜这头只负责师资、场地、教学流程。培养出来的学员中只要出了“华姐”“亚姐”、明星、名媛佳丽,模特公司立马扩大包装尺度,大张旗鼓地宣传,号称自己是民间的北京电影学院,简称民间北电。
那么后继报名的人数就是病毒式增长。
其实一下子有钱的感觉并不是狂喜,而是让人有些眩晕,一时真假难辨。这时候梁少武就起到作用了,他这个人对钱比较有感觉,满脑袋花花点子。只要是赚钱的事,他还真是不嫌烦,反反复复地跟人讨价还价,从中得到不少利益和乐趣。
所以,尽管纳蜜是培训基地的主任,具体做事的却是梁少武。
纳蜜也落得清静。
只有两件事纳蜜是坚持的,先是有了钱,重新装修了培训大楼,在五层的基础上加盖了三层。外墙把原来土气的枣红色换成高级灰,并且加装了电梯。这样一来,整个感觉完全不同,不仅威严而且时尚。
大楼内部当时也算是斥巨资增设了电脑学习室、英文听力训练营、烹饪天地和走秀空间。搞基建就是流水一样花钱,花得梁少武肝颤,小声嘟囔了一句,有这个必要吗?纳蜜立马目光如炬,狠剜了他一眼,吓得他不再吱声了。
第二件事是不靠谱的培训,无论给多少钱都坚决抵制。
比如类似变相传销的培训、古典美人的培训,根本就是政治不正确,被取缔是早晚的事。这也表明在纳蜜心里,没有一天忘记自己是滕哲的女儿。
不能在清风自来的路上掉到坑里去。
事实证明,她所做的一切都是防患于未然。
再教育培训基地效益爆棚早就名声在外,互联网时代就是好事坏事都传千里。多少人跑到校长那去活动,去告状,想顶了纳蜜的位置。
校长岿然不动,只说,还就是滕纳蜜最适合这个位置。
而在纳蜜的记忆里,她根本没有跟校长说过话。
转眼之间,就到了培训基地。
纳蜜停好了车,准备去办公室。途经后花园时,由于南方的秋天并非滚滚落叶一派肃杀,反而中午的温度持续不减,各种花草便在凋零前疯狂盛开,粉红色的三角梅简直无处不在,绣球花开成了傻大姐,艳俗的羊蹄甲花不仅满坑满谷,还摆出各种迎宾的架势,一点矜持都没了。地上也是灌木纵横,杂草丛生。据称这几天花工家里有事回乡下了,果然后花园就变得不成样子。
纳蜜转身进了后花园,在工具房拿了修剪花枝的大钳,一通整理。
然后撑起花园里原有的大阳伞,在伞下拔草。
“又拔草了。”
听到这声音,纳蜜抬起头来,不过不用抬头她也知道是梁少武。只见他穿了一件黑黄间隔的T恤,远看近看都像一只大黄蜂,右手举着一根啃了一半的玉米。少武这个人无论有钱没钱,都是节俭度日,而且始终听老婆的话,孩子也出国留学了。他说包小三这种事谁不想,但是把钱花在这些人身上,不值。
到底是男人,他并不太显年纪,只是头发稍许灰白,但也从来不染。
他蹲下来,跟纳蜜谈工作上的事。
现在的培训基地已经有了二十多个工作人员,但还是感觉人不够用。所有人都被梁少武指挥得团团转,就像雇主绝不能看到保姆有一分钟的停摆。
自从培训基地变成了一块大蛋糕,少武的工作态度也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巨变,像狗一样地看场护院,忠心耿耿。一方面当然是利益决定行为;另一方面他颇为赞赏纳蜜的工作作风,凡事绝不管那么细,分权到位,让他拳打脚踢抡圆了干,同时给他的待遇、红利只多不少,令他充满成就感。
大伙都知道纳蜜主任的爱好是园艺,而且喜欢拔草。
如果要谈工作,不是在办公室,就是到后花园。
花气日影,岁月绵长。
这也是若干年前的事了。
那是一个渐渐夜色压肩的黄昏,纳蜜在后花园里拔草。这时的后花园里是少有的宁静,柳动蝉鸣,翠雾深幽。花工和培训基地的职员都已经下班了,纳蜜一直都很享受这种与花草单独相伴的时空,毕竟这块园地是她一手一脚打理出来的隔世净土。
这时她听到一个童声喊“妈妈”。
而且分明是狮狮的声音。
她回过头来,又四下张望,并没有一个人,没有。
而且她的儿子薛狮狮四岁半的时候,在百货商店走失了,应该是被人贩子拐走了吧。她和孩子的爸爸薛一峰找了五年,一点音信也没有。
找到现在,还是一点音信都没有。
狮狮三岁的时候,喜欢跟着她到培训基地来,大部分的时间他们会耽搁在后花园,便于狮狮奔跑和晒太阳。他们非常快乐,来回追逐。筒子楼毕竟太小了,生存环境恶劣,那时的纳蜜根本没有能力改变现状,甚至连幻想都没有,她能做的就是逃避现实。所以只要有空,就会带狮狮到后花园玩。
甚至,年轻时候的纳蜜,也不是没有一个半个调动工作的机会,但是一想到从此就没有了后花园,狮狮没有了可以奔跑的地方,她就下定决心放弃那些所谓的机会。
狮狮的叫声清脆稚嫩,但在夜色沉沉的黄昏显得甚是萧疏。
令纳蜜万千情丝化作两行清泪。
从此,落下了拔草的癖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