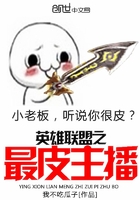还有一个令黑川深感不安的原因,这些土匪首先是中国人。他研究过中国文化,深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道理。日中交战已不可避免,别看他们现在窝里斗得厉害,一旦两国兵戎相见,这些贼胆包天、杀人不眨眼的关东响马就会把枪口对准他们这些“鬼子”的脑袋,尽管省森林警察总队讨伐过摩天岭,可一枝“三八式”步枪也没追缴回来,黑川一想到这些,就会不由自主得倒吸一口凉气。
黑川了解中国人,杀父夺妻不共戴天,王福橖绝不会善罢甘休,他不敢招惹森警队,迟早还得拿老季家开刀,有了老季家这个金钩钓饵,就不愁王福橖这条大鱼不咬钩。同时,他也谙熟杀鸡儆猴的道理,他要借此机会给那些不太理会儿他们的满洲人来个下马威……只是黑川没想到,摩天岭这么快要对季家下手了。
黑川并不是什么正经商人,公开身份是商社的社长,实际上是受日本军部派遣的间谍,他的使命是秘密收集一切有用的情报,为日后的侵华战争作准备。
黑川抄起电话,要通满铁护路队的值班室。值班军官伊藤中尉,认真地听着黑川说出来的每一句话。黑川最后说:“……伊藤君,务必抓住这个机会……消灭了这伙儿强盗,不仅挽回了我天照大御神臣子高贵的面子,也铲除了一个危险的心腹隐患——一箭双雕。你,明白吗?”黑川的语气坚定,丝毫不容置疑。伊藤毕恭毕敬地说:“是,阁下!……请阁下尽管放心……是,九月十三,申时……我,明白!”黑川放下听筒,脸上浮出一丝阴森森的奸诈的冷笑……
这半年,季广源心里就一直没痛快过,被黑川叫到办公室,脸阴沉着一语不发。
没等季广源坐稳,黑川就连日本话带中国话一起用,先是大骂关东响马无法无天,关东响马不在身边干骂不解气,干脆骂开了季广源,直骂得季广源血往上涌,就快沉不住气了。就在季广源要跟黑川翻脸之际,窗外响起了汽车的轰鸣声,门一响,闯进来个矮胖得像个地缸子似的日军曹长。
黑川也察觉出季广源有些不是心思,人丹胡儿翘了翘拍着季广源的肩膀,皮笑肉不笑地说:“这下好啦,护路队给我们的季老板护驾来了,你再也不用担心土匪来找你的麻烦啦!”
季广源猛地站起来:“对不起,我们家的事,不劳黑川社长操心!更用不着护路队给我保驾,我担当不起!”
黑川的眉头扭动着,目光如电直视季广源的眼睛:“季先生,你这话说得不对!你现在是大和兴的人,理应受到保护。如果再出现什么闪失,整个大和兴……不,整个南满铁路,甚至大日本帝国的面子都会被你丢尽的。你的,明白吗?”季广源心里直骂:****小日本儿,你们有什么面子?
黑川丢下季广源,一语双关地对鬼子曹长说:“把你们从宽城子调来,是帮助满洲人剿匪。你要明白,是‘帮助’……唔?”鬼子曹长脚跟用力并拢:“哈伊!”黑川的脸色突然骤变,狂躁地挥舞着拳头,“请转告伊藤,埋伏在夹卵子沟口一线,截断他们的退路,一个也不许放过!”
季广源听见“夹卵子沟”这几个字从黑川嘴里说出来,简直就不像人话,差点儿气乐了——
老林子里的狗熊贪玩。早年间曾经有头小公熊跑到木帮遗弃的楞场玩耍,骑在一棵没被破开的圆木上,抱着木头楔子左摇右晃,结果把钉在圆木上的木楔子晃了出来,把小熊****夹住了……
季广源苦笑笑,心说:“但愿能夹死这驴日的王福橖。夹不死他,将来更是个麻烦事儿!”望着黑川鼻子底下那撮人丹胡子,季广源感到一阵厌恶。别看季广源平时神仙老子谁都不尿,可让东洋人撑腰,他心里却很不是滋味。忍不住暗暗骂道:我们家和胡子的过结是中国人的事情,关你日本人屁事。你个小鬼子,滚他妈一边去吧!
王福橖一步一步踏向黑川掘下的死亡陷阱,他却浑然不知。在此之前,五里桥警察分局的麻局长已经接到了黑川报案。老麻是出了名的和事佬儿,他的处事原则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在他管辖的地面儿上,大大小小绺子也有好几股,他谁都不想得罪,更不愿意得罪王福橖。麻局长的脸抽抽着,黑川看出来他不愿意接这个差事,便以日人商社在华利益受到威胁为由,软硬兼施,老麻只得硬头皮应承下来。刚交火时,王福橖没把警察手里那几条枪放在眼里,不想,应季子祯之邀的各路炮手相继赶来,愈聚人愈多,黑瞎子岭上的火力也愈来愈猛,把王福橖压进夹卵子沟里抬不起头来,他被迫带领队伍顺山沟往回撤,不想被日本人的歪把子机枪封住了沟口,弟兄们死伤惨重……
绺子撞墙,踩了黑川下的夹子,王福橖身中七弹,后背那一枪射穿肺部,造成了血气胸。见大当家从马上一头栽下来,二龙和弟兄们都拼命了,好不容易才保护着王福橖和张素贞逃回摩天岭。
张素贞也挂了彩,衣服有些破烂,肩头被剐了一个三角口子,翻卷的布片儿跟着她一抖一抖的抽噎。下山的时候,张素贞还是英姿飒爽的,此时却是头发蓬乱,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她顾不上伤痛,抱着奄奄一息的王福橖心如刀绞,原本美丽的张素贞,现在是一副深秋后的景象。二龙看到她这般摸样,心跟着一紧一抽的隐隐作痛。
摩天岭大寨内的灵棚里并排停放着土匪的尸体。张素贞把王福橖的灵堂设在卧室里,由一个贴身的女侍从陪着她守灵,其他人一律不让进去,就连各山头前来吊祭的江湖朋友,她也一概不见。
二龙送走“松江好”水绺子的翻垛师爷,回到灵棚坐定,望着灵床上的一排尸体满脸沮丧。弟兄们也没有了嬉闹的心情,沉着脸和尸体对望着,恍似被打死的不是别人,而是他们自己。
一连两天,张素贞不吃不喝,二龙心里不免有些着急。他让伙房做了一碗地瓜苞米面糊糊,双手捧着想进灵堂,劝她好歹吃点东西。不想,二龙的一条腿刚跨过门槛,眼前红光一闪,“砰!”“砰!”两声枪响,子弹嵌进门框,打得木屑四散飞溅。这两枪打得太突然了,二龙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枪一响,他下意识地一缩脖子,一个高儿蹦出门外。二龙两只耳朵被震得嗡嗡聩响,过了好半晌才搞明白是怎么回事,端着剩下的半碗面糊糊,嘟囔了一句:“这小娘们,疯啦?!”
夫人能向二当家的开枪,别人更不敢进去打扰了。第二天傍黑,张素贞像幽灵一样从阴森森的灵堂里走出来,把蹲在灵棚里烧纸钱的喽啰吓一跳。
张素贞的嗓音有些沙哑:“冤有头,债有主。传我的话,一年后,姑奶奶要用季家和那些帮狗吃食的人脑瓜子,给大当家的和死去的兄弟祭坟!”
那个小喽啰把一叠纸钱扔进丧盆站起身来,回禀道:“回夫人,季老爷上吊,死了……”张素贞微微一愣:“死了?死了好!死了,是老东西的福分!”
山岭连绵,林海茫茫,深秋的“五花山”呈现出难以形容的美丽,黄的、绿的、红的叶子肆意渲染着,飒飒作响。摩天岭阳坡又新掘出好几个坟坑,坟坑边上停放着棺材和鞍韂马具和死者生前的心爱之物。
过山风吹得树叶乱颤。张素贞跪在坟坑边上,仰天叫道:“江湖奔班,人老归天!”跪在地上的众匪徒齐声嚎啕:“掌柜的……”“兄弟呀……”“你走好啊,大伙儿都来送你啦!”土匪们的喊叫在山谷里久久回响着,在哭喊和啜泣中,棺材陆续下到坑里。张素贞从地上爬起来,给王福橖的棺材上填了第一锹土……
料理完后事,二龙再次来见张素贞。这次他没敢贸然推门进屋,先咳嗽一声,怕屋里人听不见,又用烟袋敲了敲门框,女侍从从里面将门打开,把他让进屋。
二龙坐定,用烟袋锅在烟荷包里不停地挖着,等了半晌不见张素贞跟他搭话,把烟袋点燃抽了一口,问:“大哥不在了,嫂子想过没,你打算往后咋办?”张素贞眼皮都没抬,冷冷地反问道:“啥咋办?”二龙顿了顿,硬着头皮说:“你呀,你往后有啥打算?”
张素贞闻听这话,不由得心里“咯噔”一下,明白二龙这是要赶她下山,自己好坐绺子的头把交椅。
张素贞摆弄着驳壳枪,一会合上机头,一会又把机头掰开。听完二龙的问话,停了几秒钟,右手握着枪柄在左掌心上一磕,弹夹“咔”地复位,一拉复进机将子弹推上枪膛:“这还用问吗?既然大当家的不在了,我,就是大当家的!从今儿个起,绺子里一的切都得听我的!你来得正好。往后,你得帮我照应着点儿,谁要是敢背着我起妖蛾子……哼!可别怪姑奶奶我六亲不认!”
张素贞如同恶煞附体,令二龙感到不寒而栗,不由想起了几年前第一次让他心房震颤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