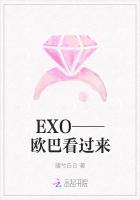摩天岭大寨被松树明子照得通亮,二龙眉开眼笑正领着几个人查验搬运季家送来的枪支和子弹。水耗子揽着大青骡子,把手伸进怀里攥着装银元的小布口袋迟疑着想跟二龙套近乎,见他身边总是人来人往的,一直没有机会和他搭话,无奈之下,只好把已到嘴边儿的话又咽了回去……
红松木刻楞大厅很宽敞,棚顶上吊着一口装着半锅野猪油的生铁锅,锅沿儿上搭着一根擀面杖粗的油捻子,冒着浓浓的黑烟,空中飘着尚未燃尽的油烟絮子。野猪油灯红光四射,在红光照耀下,草上飞端坐在一把桦木大椅上。
草上飞今天显得格外健谈,用烟袋锅儿指着刚搬进了的枪支,跟坐在斜对面的詹先生唠起家常嗑儿:“要说起来,我认识你们家老掌柜的也不是一天半天了。他这个人一辈子本本分分,恨不得看见蚂蚁都绕道儿走,可到了少东家这辈儿,咋就一点儿都不随根儿了呢?……不是我草上飞爱财,我就是为了置这口气!你瞅瞅他们哥几个干的那些缺德事儿吧——搁谁身上,谁能就这么拉倒?”詹先生陪着笑脸说:“是是是,老当家的说得极是……这事一点儿都怪不得旁人。要怪,只能怪我们家少掌柜的年轻不懂事,还望两位当家的高抬贵手,多多海涵才是啊!”
一直没吭声儿的王福橖,突然插话说:“没那么便宜。卖酒的跟拎瓶儿的要钱,这是规矩。他二哥跟小日本子勾搭连环,仗势欺人,害死了我姑父。我今儿个要不活剐了他,对不起老天爷,兄弟们也不能答应!”
站立两厢的土匪头目跟着叫嚷起来:“对对对!不能便宜了这小子。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先插了这****的三王八,再去掏了他的王八窝!”“对,插了他,给宋粮台报仇!”“就是,不卸他个膀子,也得卸他个大胯……”
原本挺和缓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詹先生忙偷眼去看草上飞的反应。草上飞不动声色地用烟袋敲了敲椅子扶手:“冤有头,债有主。你们就别跟着瞎嚷嚷啦!”一扬手,把装着二百块大洋的白布口袋扔给二龙,“把这些老头儿(银元)拿去,去给崽子们劈吧劈吧,叫大伙儿手头儿也阔绰宽绰……常言道,人怕见面,树怕扒皮。如今,老掌柜的诚意到了,詹先生也把话说透了,这次就先放他一马!江湖有江湖的规矩,绺子有绺子的章程,咱得话服前言。过去的恩恩怨怨,就此一笔勾销,咱们依旧井水河水两不犯!”
詹先生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忙抱拳当胸作了个罗圈儿揖:“我替我们家老掌柜,谢谢老当家的、少当家的能如此宽宏大量……谢谢三老四少。承蒙老当家的器重,詹某不才,等我回去一定从中鼎力斡旋,重修旧好……不多打扰了,詹某告辞啦!”
詹先生嘴上说着“告辞”,脚却不挪窝儿,用眼睛跟草上飞要人。草上飞看出来了,仰面大笑,吩咐把季广源带进来,管“秧子房”的土匪头目应声而去。工夫不大,季广源被两个喽啰抬着,“咕咚”一声扔在地上。
季广源像粽子似的被绑得结结实实,半卧在地上,拱了几拱没站起来,詹先生急忙走上前去把他搀扶起来,刚要伸手去摘套在他头上的黑布头套,被草上飞抬手制止了:“詹先生!他的蒙眼儿就给他戴着吧,别往下摘了!……来呀,套车,送詹先生他们下山!”过来两个拿黑布条儿的土匪,把詹先生和水耗子的眼睛也给蒙上了,用马车一直把他们送出了山口。
接下来的事情,并没有像草上飞和詹先生所期望的那样就此井水不犯河水恩怨作罢。回到家,季广源像疯了似的谁的劝说也听不进去。一气之下,詹先生辞别了季子桢回家不干了。季广源背着父亲,偷偷地跑到省城搬来了森警队的警察,打了摩天岭一个措手不及。结果,老土匪草上飞死于那场混战,摩天岭和季家的积怨更深了……
自从老土匪草上飞死后,季家大院成了大龙王福橖的眼中钉,他做梦都在想怎么跟这个老对头算账。翻垛先生刚刚算定,阴历九月十三申时一刻是攻打季家大院的最佳时间。
二龙眉开眼笑地走进来,打着隐语:“想啥来啥,想吃奶就来了妈妈,想娘家人,小孩儿他舅舅就来啦!”翻垛先生告辞出去,王福橖问:“是不是水耗子来拍山门啦?”王福橖见他挑着大拇指光笑不说话,没头没脑儿地说了一句:“亥子此方大失败,鸡犬作怪事难成!——这小子怕是仇怨攻心,气迷了心窍儿啦!”
水耗子是孤儿,从小跟着排帮混饭吃,练就了一身的好水性,在水下能睁着眼睛抓鱼。排帮上的橹子头邰殿臣见这孩子身世可怜,又很机灵便认他作了干儿子。父子两个相依为命,感情也愈处愈深。后来殿臣老了,木帮儿和水场子里的活儿都干不动了,爷俩儿只好辞离了伙计们在五里桥安下家,也开了两孔小炭窑,虽说没有什么太大进项,但维持温饱还是绰绰有余,眼看爷儿俩的日子就要过起来了,水耗子也到了娶妻成家的年龄,老把头殿臣本想好好烧几年炭积攒几个钱儿,给干儿子把媳妇娶回来,自己也好抱抱孙子享享清福,可万万没想到平地冒出个大和兴炭厂。更可恨的是,“大和兴”还没挂牌点火,就四处挖墙角儿,很多窑厂的窑工都被他们花高价挖走了,水耗子家也不例外,眼看着全部希望都跟那两孔炭窑一样快要熄火了,老殿臣急火攻心,一头栽倒在窑坑里,从此一病不起。
邰殿臣中风不语瘫痪在炕上,吃喝拉撒全靠水耗子照料,褥疮溃烂满屋子都是刺鼻的恶臭,熏得人喘不上气来,成群的绿豆苍蝇赶都赶不走。邰殿臣刚强了一辈子,不忍拖累水耗子,吞下一块大烟膏,大瞪着一双不甘的眼睛离开了人世,水耗子把这笔账记在了季广源头上,跪在干爹坟前发了毒誓要报复季家。
水耗子是个很有心计的人。他效仿越王勾践卧薪尝胆,隐姓埋名给季家当起了看家护院的炮手,上次护送詹先生上山去赎季广源,他就暗中跟二龙挂上钩了。
王福橖生性多疑,听说水耗子又来了,不由得心里犯起合计。他确实有点儿信不过水耗子,怕他反盆,又怕二龙多心便敷衍道:“你还是叫他先回去吧!咱不干那捅鸡屁眼子的勾当。等啥时候用得着他,自然会知会他。”二龙疑惑地问:“不用他当内鬼啦?”王福橖说:“先不用!”二龙仍不死心,又问了一句:“硬克硬?”王福橖说:“嗯,硬克硬!”二龙无奈,只得把水耗子打发回去了。
谁也说不上哪面墙会透风,王福橖砸季家响窑儿的计划“封缸”不严,被“插旗儿”的崽子不慎走漏了风声,季子祯闻讯暗暗叫苦。
季子祯清楚,虽然高墙大院还养着几颗快枪,真要是跟已经红了眼的王福橖打起来,维持一时半会儿还行,时间长了恐怕很难预料胜败。尽管他已心灰意冷,对这份不是好道儿来的家业早就不放在心上了,可毕竟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他怎么也不能不顾及自家大大小小那十几条性命啊!迫于无奈,只好硬着头皮给各路朋友送出求援信,来帮着壮声势。百十里地的大荒川,从五里桥镇算起一直到大荒川尽头共有十几个村屯,东荒地离五里桥虽说不是最近,但也不太远,乌白两家炮手自然也在邀请之列。
按照这一带长期形成的规矩,不管是谁家,也不管平时有没有过密的交情,只要接到求救的帖子,都绝不能袖手旁观。但为了避免与黑道朋友结下生死冤仇,不到万不得已炮手们都不会对土匪下死手,更不会赶尽杀绝,七分吓唬三分打,通常是打那种下三路的“朋友枪”,这样,既不与道上结怨又解了事主之围,可谓两全其美,双方都领情,这是常规也是季子祯的本意。可令他们万万没有料到的是,满铁护路队会半路插一杠子,事情就变复杂了,也必然要把他们卷进一场世事难料的江湖恩仇之中——
本来,摩天岭绺子与老季家的恩恩怨怨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他黑川管不着这段儿更犯不上大动肝火,可这伙儿土匪居然敢绑满铁炭社董事、炭厂副总经理的票儿,用老百姓的话说,这是把日本人的面子当成臭鞋垫了!更让他无法容忍的是,大日本帝国制造的三八式步枪堂而皇之地握在土匪手里,这成何体统?在他看来,这两样都是很丢脸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