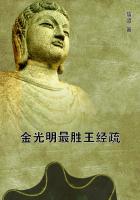1953年冬,郑学礼奉调省委工作,在他担任人民监察委员会理论调研部部长期间,反右运动开始了。
郑学礼依旧像对待历次政治运动一样,积极热情慷慨激昂,毫不保留地参加到了反右派斗争之中。运动之初,郑学礼是监察委员会领导反右运动的“三人小组”组长。七月初,省人委的一期《反右动态》刊登了一篇批判文章,这篇文章的作者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评论者,批判了郑学礼曾经在报纸上发表过的一首诗。诗歌的题目叫《冬之絮语》,四小节共十六句。然而,这首诗歌却给郑学礼带来了灭顶之灾。批判文章说:
这首诗发表在今年5月,正是****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时候,他们叫嚣要共产党“下台”,“让位”,他们通过各种形式,包括用写诗的形式宣泄着对党和人民的无比仇恨和变天的梦想。因此,对于《冬之絮语》这首诗,必须站在政治斗争的高度加以分析……
评论者将其中四句逐字逐句加以剖析:
“野山菊谢了”,就是要共产党下台,称共产党为“野”,实质上与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奥斯汀污蔑我们党毁灭文化遥相呼应。
“我们在寒冬中静默”,则是说右派分子要上台,这里的“我们”就是指罗章联盟。
“冰雪覆盖着山野”,表达了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极端阴谋、极端仇视、极端恐惧的即将灭亡的反动阶级心理,切齿之声,清晰可闻,而且作者的影射还不仅限于此。
“我们静候着春天的风”,其实就是号召公开举行反革命叛乱……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错误地估计了国际国内形势,散布****和社会主义言论,大肆地向党发动进攻,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没有优越性,不如资本主义制度,诬蔑国内形势,全盘否定社会主义改造和各项建设成就,公然叫嚣“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是改变社会制度”。右派分子别有用心地煽动和阴谋活动必须予以坚决镇压!
……
这篇评论文章像炸弹一样爆炸了,有人惊奇,有人害怕,有人发愁,有人兴奋,郑学礼只看了几句就不敢再往下看了,他的脸涨得通红像被人狠狠搧了一记耳光,他想抗议但却发不出声音,他已经被这颗评论新星死死地扼住了喉咙。
“新星”的原则性是那么强,问题提得是那么的尖锐、大胆、高超,立论是那么势如破竹、不可阻挡,指责是那么的骇人听闻,具有一种摧毁一切防线的强大力量,甚至不容探讨和切磋。文艺批评原本是可以提出异议的,而他却没有给郑学礼留有半点儿辩解的余地。更让郑学礼吃惊的是,他发现白纸黑字引发了一个可怕的现象,周围的红口白牙正在无情地咀嚼着他的肢体,他甚至听到了自己的骨渣声。他忽然悟出来一个道理,原来人是可以吃人的,原来人比豺狼更凶残。他思虑再三,敲开了机关党委书记白桦的办公室……
当年,白四爷请了一位晚清举人做白桦的启蒙老师,念了一肚子四书五经,诗词歌赋。不想诗云子曰弄得白桦浑身不自在,后来城里兴办新学,白四爷将女儿送进了奉天的新式学堂,黄氏夫人临终前想见白桦一面,当她回到白家大院时,已出落成一个婷婷玉立的洋学生。
像所有好学又爱美的女学生一样,白桦穿着时髦的宽襟短袖的白市布窄腰衣衫皂青裙子和皂青帮布鞋,齐耳朵短发,鼻梁上架着一副白金脚无边眼镜,无边眼镜似乎不着边际,与姣好的面容融为一体,也挂起了女学究的招牌,尽管是学生装束,却掩盖不了妩媚婀娜的仪态。
莫说在东荒地,就是在县城里也没有几个富家子弟能到奉天去念书,更何况一个女子。白桦回来奔丧,惊动了县里刚刚创办的新学校长,他专程赶来探访,以获得新事物的最新消息……白桦热衷政治,满脑子的新思想、新潮流,令白四爷感到有些茫然。一个女孩子整天价跟在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的男学生屁股后面疯疯癫癫的瞎跑,荒废学业不说,更怕跑出什么事来……事实上,白桦早已远远超出了四爷的想象,她已不仅仅是瞎跑那么简单了,她正满怀远大抱负和一腔热血,在进步青年的行列中接受着新思想的洗礼,成为一个追求新生活和对封建势力顽强反抗的先锋,是报纸上、书本上经常提到的那种女人——新女性。
白桦和许多热血青年一道,辗转于千疮百孔的华夏大地,努力寻求救国救亡的真理,寻找着“德先生”和“赛先生”。“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沦陷,白桦结识了****地下党员郑学礼。经郑学礼引荐,白桦加入了抗日救亡组织,参加过无数次的“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在斗争中他们成了一对红色恋人。解放战争后期,组织上派白桦参加剿匪工作队,在佳木斯牡丹江一带边剿匪边土改,郑学礼则再度转入地下,以教员的身份为掩护继续从事地下活动,迎接吉林第二次解放。
从白桦办公室出来,郑学礼的心情愈发复杂,他想,白桦说的对,他应该相信组织相信党。然而,当他从走廊走过,看到办公室主任、三人小组成员,那个面黄肌瘦满脸皱纹的中年人还在全神贯注地阅读那期《反右动态》,手里捏着红蓝铅笔圈圈点点,他的心又是一阵紧缩,大脑像缺氧似的感到一阵晕眩。
郑学礼扶着墙壁,心里空荡荡的。他可以想象生命的终止,可以想象太阳系的衰老和消亡,却不敢想象眼前这个危险的处境,随即产生了一种令人懊恼的心理: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注意过别人对他的态度,他也想自己可能有些神经过敏,但事实上,那颗“新星”的文章确实产生了巨大的“多米诺”效应。
到了1957年9月,形势开始发生急剧的变化。在一次阶段性总结会议上,一位领导批评了监察委员会反右运动开展得不扎实,出现了“三多三少”的问题:即声讨社会上的右派多,揪出本单位的右派少;揪出来的人员当中,留用的人员多,清除革命队伍的少;基层揪出的多,机关揪出的少。这位领导用手指叩着桌面,一字一板地说:
“监委会的反右运动之所以迟迟打不开局面,是由于身为机关党委书记的白桦同志存在严重的温情主义错误,没有落实好“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部门领导本身就太过温情,还能搞好反右斗争吗?譬如说,省委已经对郑学礼的****言论进行了严厉批判,都过去两个月了,你们依旧按兵不动,还让他混在三人小组里,甚至还担任着三人小组的组长,简直是太荒谬了。这足以说明,白桦同志正面临着堕落的危险!”
迫于压力,白桦不得不频繁地作检讨,郑学礼也被调出三人小组。紧跟着,各部门的运动进入了崭新的阶段,接二连三地揪出许多人,揭批郑学礼的大字报随即出现了。
让人感到奇怪的是,好端端一个人,只要一揭就浑身疮疤——郑学礼曾经嘲笑过某位领导讲话罗嗦缺乏逻辑;郑学礼曾经说过许多文件、演示文稿、材料没用;郑学礼曾经诽谤我们的党群关系有问题;郑学礼曾经散布谣言,污蔑人民监察委员会内部不团结,派系之间互相顷轧;郑学礼曾经诽谤机关干部,有些人为人行事鬼鬼祟祟,正经话不正经说,总喜欢跟领导咬耳朵,……郑学礼说……郑学礼说……郑学礼的问题愈揭愈多。
三天后一个阴冷的下午,郑学礼被工作组叫去谈话,宣布了对他的处理结论。新任“三人小组”组长,那个满脸皱纹、面黄肌瘦的办公室主任,一字一板掷地有声地宣布了对郑学礼的处理决定:
郑学礼,男,汉族,一九二零年三月出生于旧知识分子家庭,一九四二年秋天混入党内,原任省人民委员会监察委员会理论调研部部长。
该郑自幼受反动封建家庭影响,怀着不可告人的个人野心混进革命队伍,在****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时刻,利用诗歌恶毒地向党和人民发起猖狂进攻,其狼子野心昭然若揭,实属资产阶级右派(“极右”)分子。
本着生活上给出路,政治上给宽大的原则,经由组织审查决定,撤销该郑党内外职务,开除党籍,取消原行政15级正处级待遇,遣送农村接受监督改造,每月发给28元生活费……
宣读完毕,他将处理决定递给他,让他在上面签字。郑学礼掏出钢笔,艰难地在文件上面签上了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