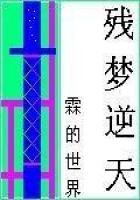一双光洁修长的腿以藤蔓缠绕巨树的方式,狠狠地勒在男人脖颈上,男人也正使出浑身解数,西装上的线一根一根的崩断,露出极其发达的肌肉,如同一个个铁疙瘩一般,却是无法撼动那双看似纤细的腿半分。恰恰相反,那腿愈缠愈紧,男人脖子上的青筋一根根的绽起,豆大的汗珠再无法承受自重,滴在方向盘上,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
右手虽然拼命挣脱,左手却不敢有一丝懈怠,腿的主人也正帮忙驾控这辆车。要知道,这两人的高难度格斗正是发生在最低时速百公里的高速上。
我只微笑着,默默看着两人的争斗。
我想,一个很长很长的故事讲起来,总会是异常费劲。我尽力从光怪陆离中收集记忆碎片,可,几乎所有的所有都解离的干干净净,难以发见,更难以可视化。因此,讲述每个长故事时,我总要花上极长的时间进行整理。
我的丫头无衣爱听故事,尤其是长故事,她总爱在我讲长故事时做些应景的事,比如拼一万片的拼图,比如绣出《清明上河图》的超大字绣,再比如进行一个超大型的单机解谜游戏,一边晃着她那两条白得晃人,长得诱人的腿。
我曾经怀疑这丫头根本没听我讲话,可当我试探时,她以极敏捷的速度回答了我的提问,毫无迟滞之态,甚至还回忆出了我在5分钟前所讲的话(我甚至都忘的七七八八了)。
我因此作出一个大胆的推断:这丫头有两个大脑。
而事实证明,我的猜想。
是正确的。
这是一种特殊的能力,根据相关资料,这种天赋被称为【双相】,这种被精神病医生认定为精神障碍疾病的症状在无衣身上发生了一种极其吊诡的变异,确切地说来,应当不能单纯的定义为双相,家族的人更喜欢称它为【双生】。
曾经有人认为女人较男人更能分心二用,可以一边看电视,一边打毛衣,甚至再一边和别人聊天;而同样的行为,男人就鲜能做到。科学实验也同样证明了这一点。
我一度以为无衣只是较之普通女人更强了一些,直到我在某天了解了有关【双生】的资料。
简要的讲,【双生】又称海豚脑,可以实现左右脑共用。一边脑子在睡觉,另一边可以进行极其激烈的运动是这家伙的基操,别问我她是怎么做到这样还能睡得着的,我也很难理解。
所以,说“分心二用”并不是很准确,应当换个词,比如——二心分用,毕竟在古代心脑一体嘛,虽然这样听起来瘆人极了。
好了,说了那么多废话,还没正式自我介绍。我姓柴,是后周皇帝柴宗训的不知第几代孙,自恭帝被赵匡胤逼宫后,后人多是不知所踪了,有一段时间连族谱都断了,到了明前期才算差不多安定下来,可这时已几经迁徙,早已难觅前迹。
家族虽大,却是各走一方,有的更名换姓,有的客死他乡,直至我父亲重祖的重祖的重祖这一代,在洪武年间,从镇海迁至舟山,来到了舟山的某个小岛上,除了没改姓,也不再提及自己的皇族身份。
按照家族排辈,我正好轮到了“宗字辈”,巧就巧在我这辈全是些姐姐们,我便是家中独苗。
我出生时,族里的老人们经过长达一旬的讨论,最终取定“训”字,换言之,我的名字,同那位后周皇帝一般。我并没有感觉有何不妥,难道和《盗墓》里面的张起灵是一个道理吗?怎么可能呢,柴家是挺大,可要说真有什么特殊的,可是一点说不上来,我也从没在意什么过。
说是一点神秘色彩也没有,那绝对不是。或许是由于吃鱼的缘故,柴家通族均有极高的智商,也上下流窜着一股痞气。
正是因此,整个家族除了有一些约定俗成的规则,倒也没什么繁文缛节,活得自在。
曾经有人说过,柴家祖上曾干过海上没本钱的买卖,我倒没怎么在意这点,当个海盗,听起来也蛮酷的。
无衣和我年纪一样大,是我的贴身丫头,具体的称呼有待商榷,不过这家伙自打7岁开始就跟着我,说是丫头也未尝不可。
这丫头绝非正常人所能认知的普通女孩,她从5岁开始参加由CIA特别进行的MSS计划,这项计划目的是培养个人素质极强的特殊士兵,要求之苛刻,往往令你我之类的凡人瞠目结舌。
九岁时,她又拿到了空手道黑带,并在11岁时参加国际级别HF比赛,取得了九场不败的成绩,至今是赛会纪录保持者,之所以是九场不败,纯粹是由于这丫头当时还没发育完全,要想KO别人,实在是有些困难。必须解释一下,HF又称地狱自由搏击大赛,它的规则变态至极,胜利不靠点数,纯靠KO,30分钟内,双方不分胜负,即算和局。而且有条更变态的规则:不分男女老少轻重进行比赛。
不过这家伙之所以那么牛,也该归功于【双生】,她完全可以不睡觉,事实是,她确实以3年的时间完成了一种极度极限的训练,在保持精神上充足休息的情况下,使肌肉长时间处于超负荷状态,全身上下都是教科书级的腱子肉。
众所周知,海豚的寿命较之人类要短得多,一定程度上是受到长时间保持兴奋状态的影响。
只是,她并不在乎寿命长短这一点,倒不是她不要命。她不是柴家的后裔,她来自一个很罕见的姓氏——第五。无衣原名:第五无衣。曾有一种说法,无衣的先辈是不死鸟的一个变种——火鸦。
当然,作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我对此不置可否。倒也不是相不相信的问题,而是根本无从考证,即使不相信,也是白费力气。
按照正常的套路,我应该也有点什么特殊技能啊,主角光环之类的东西,可哪怕是我离开家族前往本岛的那天,我仍旧没发现自己有什么特殊地方。
硬要说有,就是数学奇差无比,族中对孩子的智商非常看重,往往到了某个时候就会进行某种形式的测试,现在业已记不清具体内容了,唯一有印象的就是我的数学差到爆炸,在其他成绩都显示“正常”的情况下,我的数学既显示了排名,又显示了总人数,鲜红的大字令我沮丧至极。
也正是从那一天起,我被通知尽快离开家族,同无衣一道前往本岛。
别误会,家族没有驱逐数学学渣的意思,这是一种特殊的规矩,适龄少年将会离开家族,不过适龄的定义却是非常模糊。
这样一来,我就离开了家族,直到后来我才明白家族让我离开的目的。
也就是2010庚寅虎年的10月1日,自那一日起,我暂时开始独立生活,族里给了一笔巨大的财产,数额之巨大,是先前离开的族人决不能企及的。只是当时我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而是很开心能离开家族。
其实我和无衣更习惯朴素些的打扮,因此这样一笔巨款几乎是用不完的。
10月1日是国庆节,正是东南沿海地区台风到来的日子,整个舟山群岛都被笼罩在雨幕之下,倾盆这个词用来形容雨势恐怕不够确切,每一滴雨都拼命拉着其他的雨,像是自杀一般冲向大地,雨蓬,一切的一切;飓风几乎是狂笑着吹刮着,肆虐着。
没有经历真正台风的人根本无法想象这样一种自然灾害的恐怖,即便在这片故土上几经春秋的老人也还是会被惊到,吓到。
严格意义上来讲,对于那天离开本岛的许多事我都已忘记,可我记得很清晰,那一天,我的心中既没有迷茫,也没有害怕,肾上腺素使我感到极其兴奋。
我们乘的是最后一班航次,台风带来的是大面积的停航停运,托了人脉才够到两张船票,我接过母亲递上的行李箱,费劲的迈进快艇,最后瞥了一眼母亲和一旁站着的父亲,我发现他点了根“阿诗玛”,父亲向来不喜抽烟,我感到有些疑惑,他的脸上和母亲一样面无表情,坚毅的像铁一样。
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他们眼中有种什么陌生的东西,不是担心,不是难过,而是一种难以用言语描述的,现在不由自主感到后怕的深邃目光,并非后怕父母两人,而是后怕这种目光背后的警惕,时至今日,我仍旧难以忘记,甚至愈发清晰。
父亲将无衣抱起,我接过她的手,此前一直是从小到大的玩伴,抓住她的手已无数次,可这一次,出人意料的冰冷,像是血液凝固了一般,我险些一哆嗦,只是忍住了。
我很清楚,她很紧张,可是紧张什么,我并不明白,她并未回头再与我的父母打招呼,而是径直走向船舱,握住我的手柔弱无骨,却又极其冰冷,死死地抓着,指甲都嵌了进去。
远处传来几声爆竹的声响,有一些不同寻常的诡异,台风天的婚礼,或许应该那么诡异。
我最后看了一眼父母,他们的脸色极其糟糕,但我并未出声,只是默默上了船,与他们挥手告别。
直到现在,我仍在回忆,当时我还能不能做点什么来挽回一些现已不存在的东西。答案是否定的,这是我无比悲怆,却又无可奈何的。
一切自某个我没有注意到的点,一个已悄然流逝的点中,就已然注定。
雨太大了,坐在船舱中,望着舷窗已经成一种模糊状清晰的样子,我回头看了一眼缩成一团的无衣。
在这时,我才发现她怀里抱着一只箱子,是一只正方体的青铜箱子,分量应该不小,每一个面上都有着一只睚眦和一些我看不懂的古篆。
我一点也没有想帮她的意思,我太了解她了,这家伙看起来瘦弱,实际上,即使是一个成年男人的极限负重也未必能超过她,她早先练出了一膀子力气,要不是我跟她说我不喜欢金刚芭比,这几年她的线条会更加硬朗。
好在,现在一旁的姑娘已经比几年前圆润了些,更漂亮,也更适合她自己了。
她仍旧是紧张,一种近似于害怕天敌的紧张,我并未详问缘由,却是对她怀中抱着的箱子好奇。
无衣只淡淡的回我一句:
“你会知道的。”
我碰了个软钉子,只好悻悻的望着船舱前部堆放的大大小小方块状的行李箱以及巨大的包袱。
台风天的浪总像是能把船掀翻一样的大,不过这已经是停航之前的最后一班船了,再晚些时候,就算是直升机也不能将你带离这个岛了。
浪把整个船里的人晃得七荤八素的,多数乘客面色铁青。我也不怎么喜欢这种晕眩感,可我逐渐逐渐的发现,那段船上的经历,该是我最放松的一段时间了,这是家族为我做的最后的礼物了。
无衣静静的靠在我肩上。作为一个半女军人,她总对周围的环境敏感过头,只不过,现在的她更像是慵懒的橘猫。
仔细看这丫头,比起我最早看到她,亮眼多了,只是她由于紧张,面无血色,嘴唇也冻得发紫。
到本岛大约有两个小时的海程,我很清楚这姑娘看上去进入熟睡,实际上没准比我还清醒,连口气也不敢叹,只好继续让她枕着,这样的结果是到了本岛,她开始有些红润的脸色,而我的肩周炎开始发作。
实话实说,我对离开家族还是充满期待的。不是我对独立生活有多少信心,而是我对家族充满信心,当家族允许族人离开时,往往经过了详细的,缜密的计划,甚至可以算到你将走的每一步,即便是会有小概率事件发生也有应急预案,只是......
我突然发现我漏掉了一件很关键的事,而这件事,恰恰是极其致命的。
家族放人出来是为让族人进行历练,或多或少会布置任务,不管是短期还是长期,任务将成为族人行动的导向,也是一条极其关键的线索。
而眼下,我没有任何关于任务的通知,不管是书面还是口头。
我不相信家族会犯下如此大的纰漏,只有两种可能,第一种,任务从家族上层下发时,被截住了,就这一点而言,实际上是极其可能的,总有几个心大的族中长辈会迟几日发布任务,一是测试出访人的应急能力,二是为了保证在完全恰当时间发布任务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第二种,是我根本不敢想的小概率事件。
家族根本不打算给我布置任务,或者说不是不想,而是根本没能力再布置任务了。
不过,我是个很懒的人,除了发现了这一点异常,我根本就懒得去判断到底是哪一种情况。
如果连家族那些精得要命的老家伙们都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我去绞尽脑汁大概率也是白搭。
想着想着,我的拖延症又犯了,便在不做大幅度挪动的情况下,躺在椅子上,放松下来。
我深知,如果真是后一种情况,我将面对的对手,可能会像柴家一样,深不可测,麻烦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