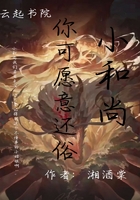夏怀慕一连几日都撑了小舟去游什么所谓的曲院风荷,湖上小舟稀疏,岸边垂柳摇曳,曲酒飘香,田致远在船头撑着船,夏怀慕则在船尾有时候教我吹奏玉笛。为了方便行事,夏怀慕给我专门做了几件男子衣衫,清一色的月白,乐得我扮起男子来玉树临风,俊朗无双。
过得时日,也许是我天资聪颖,天赋异禀,我的玉笛也吹的有模有样,最早学的曲子《醉日月》已是出神入化,就连是老师的夏怀慕有时候听得都会入神。
坊间也开始流传,这几日的曲院风荷多了一大胜景,那便是有位雅俊公子吹奏的玉笛仙音,湖上游船渐多,有达官贵人乘坐的豪华画舫,有年轻公子独棹的兰舟,更有岸边伫立静听的路人,都只为一睹吹奏之人玉颜。
自从我在玉笛上取得不俗的成绩后,我正在想是不是以后生活拮据之时,能卖唱为生,夏怀慕让我盘坐在船坞内吹奏,毋须再抛头露面,免得惹事生非,更增加了一份神秘之感。
我心知他身份特殊,搭讪之人又甚多,为了不给他惹下麻烦,便坐在乌篷船里吹了一日,半日下来,双腿酸麻的无法行走。
“致远,如此便回去吧,我看小月子身老体弱,一会儿吹了湖风,我怕她从此瘫痪在床了,拖累了我不说,关键到时候你要照看一切。”该死的夏怀慕见状还添油加醋的调侃我一番。
“好,从此你我师徒关系恩断义绝。”我本来感恩于他教我吹笛,如今倒好,我为了他而不能露面,他还有心情揶揄我。
我佯装恼羞成怒拍着大腿道。
入夜,他坐在案子旁翻着一本书,我收拾好床铺,用紫砂壶沏了上好的普洱茶,香烟袅袅。来府上这几天,劳碌万分不说,还与夏怀慕同住一室之内,我躺外间,他躺里间,还美其名曰,晚上有事可以互有照应,有风都我替他挡了。
“公子夜里渴了,你要倒水。”田小厮交待道。
我心里嘟囔着,真是个多事的家伙,晚上别喝那么多水,小心晚上掉茅坑。
然后睨我一眼,接着道“起夜要你掌灯。”
铺好床单,倒头睡去,管他晚上会不会渴死,夜里会不会起夜。
你若让生活很平淡,它就很平淡;例如说每夜夏怀慕每夜都把我吵醒,不是倒水,就是去茅房。怪不得田致远如获大赦般逃离与夏怀慕同处一室的殊荣。
你若创造精彩,它就很斑斓,例如说昨夜夏怀慕把熟睡的我摇醒,非得要我掌灯陪他去茅房。夜风熄了灯笼,我在茅房外打了半个时辰的睹。也不知道夏怀慕是不是掉进了茅坑。
第二日,我本还以为,又要泛舟湖上,遮遮掩掩坐在舟上吹曲。
夏怀慕却闭门不出,开始在萧瑟的落叶中闷声不吭的作画。
糖槭苑里的碧绿一夜秋雨过后,全都重新染了色般,红透了半边天。
夏怀慕依旧着青衫,在纸上用朱砂调入颜料画满目的红叶,我静静的研墨,看他妙笔生花,画出寥廓的秀丽江山,别致的风花雪月。
任谁都不想惊扰此刻这种恬静画面,你作画,我研墨,偶尔笛箫和鸣,这种清淡雅致的生活也有一番情趣。
“夏督军,真是好雅兴。”熟悉的声线,让我记得我还有一个大师兄,陌生的称谓让我想起夏怀慕是穆国派来的督军。
“大师兄。”我有些许疑惑,月余不曾见过的大师兄,金冠箍发,红色朝服在身,俊颜多了几分肃穆威严,少了几分昔日的嘲弄嬉笑之色。
“士别三日当刮目相待,师妹的笛子吹的真好。”大师兄敛目看了别在我腰间的翠色玉笛,别有意味的说道,虽是夸耀,但让人感觉不到我是受了夸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