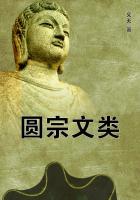自言自语了一阵,流水站在梁上睡着了。不知道过了多久,她听见敲门声。
“真么晚了,谁上阁楼来?难道是花氏夫妇,他们知道我们吵架了?”
流水从梁上飞下,变成人身,问道:“谁啊?”
“是我。”花盛开回道。
流水惊异地瞪大了眼睛,手一指,烛火就亮了。从洞房到阁楼他要爬过花园,爬到阁楼,他的腿一点劲儿都没有,完全靠两只手的力气。她莫名地心疼,但一想到他叫错名字又着实地痛恨。
”绿杨芳草长亭路。年少抛人容易去。”花盛开念起诗来,“楼头残梦五更钟,花底离情三月雨。无情不似多情苦。一寸还成千万缕。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
念诗声停后,流水狠了心,把火灭了,没有开门。
“你不开门,我晚上就坐门外了。”花盛开说得很坚决。
春天的夜晚,还是挺冷的,门外也没有东西遮挡,花盛开的衣服被茶水淋湿了,凭他自己换不了衣服。他冷得直抖索,嘴里发出嘶嘶声。
“让他冷死好了!”流水狠着心想,扯开被子,躺到床上睡觉。她没有睡着,睡不着,眼睛睁得大大的。
咣---咣---咣---外面打更的更夫敲了三下锣,每一次的锣声都震得她心疼。已经亥时了,她侧耳倾听,门外的嘶嘶声没有了,没一点动静。她下了床,点亮蜡烛打开门,花盛开随即倒地。他一直靠在门上。
她伸手到他腋下,把他拖进来,再施法术把他升浮到床上。她拍拍他的脸,脸上冰凉。
“花盛开,花盛开。”流水叫道。
叫了好几遍,他都没有醒来,流水慌了,趴到他身上,抱住他,把身上的热气传给他。大约过了一刻时,花盛开的手指动了动,他抬起手,抚摸她的后背。她像被烫似的蹦了起来,离他远远的。
“我知道你舍不得我死。”花盛开笑起来,“你过来,我手破了,拿手巾给我擦擦。”
流水拿了手巾扔给他,“自己擦。”
花盛开一路爬过来,再爬上楼梯,全靠手臂的力量,两双手掌都磨破了。
“你睡这儿吧,我下去睡。不要再爬下来了。”流水背对着他说。
花盛开用手肘支起身体,坐起来,“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直到你原谅我为止。流水,在第二次被你救起之前,我一直把你当成她。第二次落水,我看着你朝我游过来,才真正觉得你不是她,你是一个比她更好,更值得我去爱的女子。我承认我心里还有她,她还在我心里的某一处,晚上的酒把她从我心里有唤醒了,我向你保证,我会一点不剩的把她从我心里抹去。”
流水想到傅佩瑶毕竟是他青梅竹马的未婚妻,而她和花盛开相识两月不到,他心里有她也不奇怪。
“你的衣服又湿又脏,我去给你拿件衣服。”
“你一定要回来啊。”
“嗯,你自己先把衣服脱了,盖上被子。”
流水噔噔跑下楼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