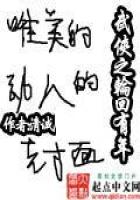陌易唐跨门而入,汪凌峰见到他的到来,马上起身行礼,他正心烦的很,根本顾不上这些雍容的礼节,大手一挥将一干人等招呼到一旁凉快去。
郎中还有陆府伺候从未见过圣驾,一见之下只觉得太过冷硬,都惊慌的不知所措,只好惶恐的跪倒在地,见此,汪凌峰便识趣的将那些不是心腹的侍从全部遣了出去。
整个内室只有陌易唐,汪凌峰,禄升,还有躺在床上一脸惨白的陆远兮。
眼见陆远兮胸膛还插着一柄断了的剑刃,他的情绪滕的一下焦躁起来,怒气冲冲的转身看向汪凌峰,声调也不自觉的拔高了,“怎么还不诊治?”
“断刃正好插在左胸,离心脏太近,郎中说是要拔的,可陆大人死活不准,情绪激动地不让郎中靠近。”汪凌峰并无皇上的激动,一派事不关己的口吻陈述事实。
在他看来,这陆远兮死不足惜。陆家倒了,朝堂上才能挪出空来,他汪家才有出头之日。
可在陌易唐看来却有些失望。他这个表弟自幽州便一直为自己出谋划策,在夺嫡这场不见硝烟的战争中,汪凌峰从未失手过。
比起其他人,与其说说汪凌峰是臣子,倒不如说他是陌易唐放在朝堂最亲近的人,就因为两人关系亲近到视如亲兄亲弟,方才还在宫里自禄升口中得知是汪凌峰在监管此事,他才微微放了心。
可他怎么也没想到,事发到现在,陆远兮的伤口竟然还未进行包扎处理,陌易唐迫使自己稳住心神,冷然的问,“怎么回事?”
汪凌峰极快了望了一眼床上的人,“微臣怀疑,那断刃是陆大人自己捅进胸膛的。”
“什么叫他自己捅进胸膛?”那么近的距离,那么长的断刃,那么深的伤口,只差一点,就要夺了他的命了。
“微臣的意思是,本来陆大人兴许伤的不重,但不知为何,就抄起地上的断刃捅了自己。”
“你如何得知这是他有意为之?”陌易唐紧紧盯着床上那一动不动的人,目眦尽裂,甚至妄图想要自陆远兮身上寻出什么线索来。
汪凌峰抬眸看了他一下,复又极快的低下头,“因为陆大人一直不让郎中靠近,还一直嚷着微臣去请示皇上。微臣劝诫先行治疗伤口,说是夜半皇上不会出宫,他却一口咬定皇上一定会亲临陆府。”
事到如今,陌易唐像是明白了陆远兮的意图,完全的冷静下来,“他可还说了别的?”
汪凌峰似乎是想到了什么,但碍于皇帝的自尊和骄傲,到底是摇了摇头。
陌易唐摆手,“你们都下去,朕有话同陆远兮交代。”
得知他与良辰的关系,陌易唐曾咬牙切齿地想要将陆远兮碎尸万段,尤不解恨,可最后还是听信汪凌峰的建议,走了迂回策略,他眼睁睁看着陆远兮为救良辰脱离皇宫而东奔西走,等到最后再一掌拍死他的全部希冀和努力。
他知道自己的行径有些幼稚,他与陆远兮就像两个互相抢玩具的矛头小子,但是身为男人他同样知道,以权压人或许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但度陆远兮来说,却是最为毁灭性打击。
他用这样幼稚的行为,为自己的幸福博得一个心安,而陆远兮却回赠了这样鲜血淋漓的一记,似乎是要用这样惨烈的方式,要白良辰永久记得他。
走到床前看着陆远兮惨白的脸色,陌易唐的唇角逸出极美的笑容,却如同刀子一般形成极为凌厉的弧度,“刺客的事,是你安排的?”
陆远兮微微侧头,大概是牵动了胸口的伤口,良久才自唇间挤出最生硬颤抖的两个字,“不是。”
“不是?”陌易唐走到床前,用手指弹了弹还未完全没入胸腔的断刃,指甲弹在铁器上,发出清脆的一声碰撞声,陆远兮爆的一头冷汗,显然疼的不轻。
陌易唐这才呵笑一声,“看样子没做假?你倒是对自己狠得下心,离心脏这么近的地方也敢刺。还是你觉得,这一剑要不了你的命,反倒能救你于水深火热之中?真是异想天开。”
在他的逼问下,陆远兮只觉得顺着断刃的纹路,胸中有一团火似要喷涌而出,抑无可抑,只能恨恨的看向这个居高临下的男人,声讨的声音如同倾尽全力。
“刺客虽然不是假的,那也仅仅是季晨敏那个蠢妇人听闻皇上就要将笑之公主下嫁与我,她害怕我抢了她儿陆远鸿的风头,就雇佣杀手来取我的性命。只可惜那刺客武功招数太过蹩脚,想刺杀我,还嫩了些。”
“只是,这却给了微臣绝大的机会。边和刺客打斗,边大声喊出与东崖联姻的事情,赶赴过来的家奴,都以为刺客是因为我极力奉行将白良辰送嫁东崖而动了杀机。”
“微臣纵容是一个不值一提的庶子,也经不起皇上这样的践踏和玩弄。皇上说我是异想天开,那我就异想天开的用这个刺杀让天下都知道,微臣是因何受了重伤卧床不起。”
还未等他说完,陌易唐就卡住他的下颚,呼出的气息也带着粗重的喘息声,昭示着他的烦暴与不耐,黑眸中的烈焰似乎要将陆远兮挫骨扬灰了也不解恨,“那你抄起断刃捅自己是什么意思?是要告诉良辰,朕玩弄了你,践踏了你还不止,非要了你的性命?”
“是!”陆远兮毫不迟的承认,“汪凌峰带人赶来的时候,刺客已经被我击毙,再没有人能作证,那季晨敏再蠢也不会蠢到主动站出来说刺客是她雇佣的,而皇上也不用费尽心思找人顶罪了,家奴都听见了,那刺客是不满白良辰联姻而要刺杀我的,谁还敢来出这个头,顶这个死罪?”
惨白的脸色下,那黑眸入浸了彻骨的仇恨,毫不畏惧的与这个站在权势之巅的男人对垒。
一时之间,两人都不说话,好像要凭借眼神对撞,分出个高低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