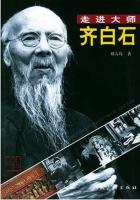关于《秧歌》还有一个问题:张爱玲是否亲身参加过土改?张爱玲在《秧歌·跋》中列出了一些小说素材的来源,包括《人民文学》里的一篇自我检讨,《解放日报》里一小方块有关天津饥馑的新闻,一份报纸上连载的一个女干部的自传,电影《遥远的乡村》以及一些“路边消息”。张爱玲写道:“这些片段的故事,都是使我无法忘记的,放在心里带东带西,已经有好几年了。现在总算写了出来,或者可以让许多人来分担这沉重的心情。”这篇跋是回应那些批评她没有土改经历的人。如果参加过土改,张爱玲直接说出来就是,其他资料不提也罢,但张爱玲就是没有说自己亲身参加过土改。
祝淳翔在《张爱玲参加过土改吗?》(《东方早报》2013年3月24日)中详论其他人的说法,发觉都不大可靠,因为都说不出具体的地点与时间。反而这篇文章有一句精警的句子:“即便没有亲历土改,缺乏感性认识,但凭着过人的才华(及其农村经历),再加一些客观材料,张爱玲照样能虚构出逼真的土改小说《秧歌》来。”相对来说,其他人即便花十年在乡下也未必写得出一本好小说。
现在大家把张爱玲的《秧歌》不是当作国家民族正史,就是当作社会学实地考察来看,或是农民调查报告,偏偏没有人拿它当小说读。与其跟人争辩美国新闻处有否commissioned《秧歌》,或张爱玲有没有土改经验,倒不如拿《秧歌》来看看,自己来判断更好。
对于《秧歌》的评价,读者见仁见智,因为各人的口味与审美观不同,但我们还可以看看作者自己的意见。
张爱玲在《忆胡适之》一文中写道:“1954年秋,我在香港寄了本《秧歌》给胡适先生,另写了封短信,没留底稿,大致是说希望这本书有点像他评《海上花》的‘平淡而近自然’。”1955年1月25日,胡适回信:“你这本《秧歌》,我仔细看了两遍,我很高兴能看见这本很有文学价值的作品。你自己说的‘有一点接近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我认为你在这个方面已做到了很成功的地步!这本小说,从头到尾,写的是‘饥饿’,--也许你曾想到用《饿》做书名,写的真好,真有‘平淡而近自然’的细致工夫。”在1978年4月23日致宋淇的信中,张爱玲又说:“‘平淡而自然’一直是我的一个标准。”
当时张爱玲寄了《秧歌》给胡适,而不是《传奇》《流言》或《赤地之恋》。她写道:“别的作品我本来不想寄来的,因为实在是坏-绝对不是客气话,实在是坏。但是您既然问起,我还是寄了来,您随便翻翻,看不下去就丢下。”由此可见张爱玲是如何喜欢《秧歌》的。
《赤地之恋》是张爱玲离开内地到香港后创作的长篇。这部小说是香港美新处commissioned张爱玲写的,也因为如此,有很多人将这部小说看作是美国新闻处的宣传工具。但如果《赤地之恋》是美国新闻处委托张爱玲创作的宣传作品,那么就应该有一整套相关的宣传。既然请到一位知名作家根据他们预设的大纲去写书,自然会大肆宣传,例如发新闻稿、开记者招待会、写书评、赠书给图书馆和学校等等,令投资发挥最高效能。现在,我们看看实际情形如何。
《赤地之恋》正式授权的版本有:香港天风(1954年,中文),香港友联(1956年,英文),台湾慧龙(1978年,中文),皇冠(1991年,中文)。《赤地之恋》版本并不多,远不如张爱玲其他受欢迎的小说。
对此,我父亲在《私语张爱玲》中说:“书成后,美国出版商果然没有兴趣,仅找到本港的出版商分别印了中文本和英文本。中文本还有销路,英文本则因为印刷不够水准,宣传也不充分,难得有人问津。”
《张爱玲语录增订本》中也记录了张爱玲的两段话,都是发泄不满之情:“《赤地之恋》中校对一塌糊涂,但是所有黄色的地方都没有错字,可见得他们的心理。”“《赤地之恋》印得一塌糊涂,幸亏现在我正为了《秧歌》在美出版事而很开心,否则火气更大。不过我也吵不出什么来,天生不会吵,说厉害点的话也不会。”
1956年8月18日,张爱玲致信宋淇,谈到对《赤地之恋》英文版的不满:“《赤地》英文本我刚收到,印得不像paperback(平装书)而像学校教科书,再加错误百出,我一肚子气,Dick(麦卡锡)问起时我只说收到了,其他一字不提,否则一定要吵起来。”
自上世纪60年代起,台湾皇冠便重新出版张爱玲的作品,《张爱玲短篇小说集》《流言》《怨女》《秧歌》陆续出现,但《赤地之恋》迟迟未出。1977年7月12日张爱玲致信夏志清:“《赤地之恋》再版只好再等机会,皇冠出全集的时候,这一本也签了约,没印,想必销路关系。”
1977年年底,台湾慧龙出版社隆重刊登广告,宣布出版张爱玲的《赤地之恋》。台湾皇冠出版社负责人平鑫涛看到后写信给张爱玲:“《赤地之恋》在多年前排好版子后,因为有关当局认为内文有若干地方,应予删改;我们一向尊重大作,不愿受到割裂,虽已排好版子,还是忍痛搁置未能出版,错在我们没有把详情告诉您(因为不希望把这些烦人事烦您),一直等到慧龙的广告,才知道被他们出版了。我们有幸出版您所有的作品,现在有一本《赤地之恋》未能包括在内,总觉得十分遗憾。”(1978年1月28日)
慧龙出版社是不是真的那么神通广大,可以做到连皇冠也办不到的事呢?
张爱玲回复平鑫涛说:“《赤地之恋》的事,经过是这样的:以前跟皇冠签约后没有出书,我一直以为是因为小说销路不好而弃权,根本没想到违禁……后来慧龙的唐吉松来信要我出这书……没来得及跟宋淇商量,就签约,不过删去‘得要求作者改写’一项,没想到他们可代窜改,实在痛心,已经来不及挽回了。”(1978年2月22日)
慧龙出版社应该是心知肚明审查过不了关,所以预先要求作者改写,但张爱玲从合同上删掉这项条款,结果慧龙竟然自己操刀改写后再出版。慧龙窜改了什么呢?平鑫涛曾指出:“小说中描写共产党员辱骂国民党政府,甚至对先‘总统’蒋公也颇有讽刺。”(见彭树君《瑰丽的传奇·永恒的停格-访平鑫涛谈张爱玲著作出版》)根据高全之在《张爱玲学》里的考据,一共有三处是对蒋介石与国民党不敬。
第一,天风原版有一处群众上街游行的情节:“……推着一辆囚车,囚车里是孔同志扮的杜鲁门(当时的美国总统)。另一辆囚车里是张励扮的蒋介石。”慧龙将“蒋介石”改成“反动分子”。当时在台湾,蒋介石通常被尊称为“蒋公”“蒋先生”或“蒋总统”,不会直呼其名,这里自然是犯了忌讳。但小说里不可能说“另一辆囚车里是张励扮的蒋总统”,所以囚车里的人就变成了一个无名无姓的“反动分子”。
第二,天风原版形容一个外国人黎培里的照片:“是他谒见蒋介石呈递国书的时候拍摄的。”慧龙将“蒋介石”改成“国民政府的首脑”。小说里的人物都是大陆人,他们不可能说“他谒见蒋总统”,因为蒋介石已经不是大陆人的“总统”了。
第三,天风原版有这句话:“这篇文字就证实黎培里是勾结蒋政府的特务。”慧龙将“蒋政府”改成“国民政府”。政府不是蒋介石私人所拥有,所以改成“国民政府”也算合理。
现在看来,这些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当年就是过不了台湾审查这一关。
1978年5月5日张爱玲再致信平鑫涛:“我把他们(慧龙)出的《赤地之恋》仔细看了一遍,错字很多,但是并没有窜改……这件事的误会,起因是多年前当局不愿张扬检查出版物的事,不顾作者精神上的痛苦--以为销路坏到出版人弃权,做梦也想不到……小说会违禁。”
看来连张爱玲自己都看不出上述那些窜改。
1978年3月7日张爱玲致信宋淇:“《赤地之恋》的故事来自USIS(美国新闻处),所以我对它不像对别的作品。如果不是平鑫涛讳言censorship(审查),早就会酌改,不会等到现在让他们滥改了。我删去合同上‘改写’一项是因为目前没工夫,而且以为现在放松了不需要改-连陈若曦有些崇拜周恩来的话都照登。”如果出版社事先肯好好跟张爱玲商量,她其实会同意改掉那些较敏感的内容的。但出版社觉得此事不可提,才导致后来发生的各种误会。1991年皇冠出版张爱玲全集,由张爱玲亲自校对,《赤地之恋》仍然跟慧龙版一样,囚车里坐的人是“反动分子”。
1978年7月19日我父亲致信张爱玲:“《赤地之恋》销路不如理想,一则可能由于你所说非你心甘情愿而写,最重要的原因是事过境迁,读者已不感觉切身之痛,提起韩战,美国、中国年青人知都不知道。当局那时犯忌的话,现在认为不成问题,由此可见。”
这里我想谈谈《赤地之恋》的英文版。1956年友联社在香港出初版,现在已经绝版多年了。1998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出版社得宋家授权重印张爱玲的英文长篇小说,但只有《怨女》与《秧歌》两本,没有《赤地之恋》,引起外界诸多揣测。实际原因是美国新闻处commissioned此书,等于已买断了版权。当年美国新闻处已经改组,美国在台协会表示他们要保留版权,但多年来他们都没有企图出版的迹象。
我觉得如果《赤地之恋》是一项宣传计划,那它是非常失败的。主办单位、出版社与作者都心不在焉。它最强烈的宣传效果反而显示出台湾有一段时期出版审查得非常严厉。
在众多读者中,作者本人的意见当然是很重要的。以上已经列出多处张爱玲如何不满《赤地之恋》一书。张爱玲致胡适信中说:“还有一本《赤地之恋》,是在《秧歌》以后写的。因为要顾到东南亚一般读者的兴味,自己很不满意。而销路虽然不像《秧歌》那样惨,也并不见得好。我发现迁就的事情往往是这样。”
我父亲在《私语张爱玲》中写道:“这次经验更坚定了她的信念:决不写她不喜欢、不熟悉的人物和故事。”但张爱玲知道《赤地之恋》“已经成了自己的东西”。正如张爱玲可以公开说她不喜欢《殷宝滟送花楼会》《连环套》《创世纪》《小艾》等作品,但最后还是收录在全集里面,因为它们已经成了她的东西。
我看过很多评论《赤地之恋》的文章,其中最有趣的是作家李碧华回忆说:“(张爱玲的作品)我全部都有,甚至各种版本都有,包括中国大陆翻印的粗陋版。而手上最珍贵的一本《赤地之恋》,天风出版社出版,定价二元五角。它已昏黄残破,很多年前,不记得是中一抑或中二,是文字的震撼力驱使我,自学校图书馆偷来的。”
至于我本人,《秧歌》与《赤地之恋》是我首先接触到的张爱玲作品,所以有特别的感情,可惜当年我家中翻看的天风初版《赤地之恋》已经遗失,也应该没有什么图书馆还会有。
许多有关《赤地之恋》的争论都围绕着小说是否真实地反映“土改”“三反”“抗美援朝”的情况,但争论一本虚构小说是否真实好像很荒诞无稽。如果没有看过这本小说,最好还是找来看看,自己判断好了。
目前《秧歌》与《赤地之恋》在内地是没有正式授权出版的。虽然小说是买不到了,但有心的人总有办法找到,有关联的学术论文亦发表了不少。
有关《色,戒》的误会
近日,钱锺书、杨绛的私人书信和手稿被拿来拍卖,以致年过百岁的杨绛也不得不出来维权。其实钱锺书的亲笔信,我家中就藏有六十多封,而张爱玲跟我父母四十多年的书信,合计起来更有六百五十封以上。前几日看《锵锵三人行》,主题是名人信札市场,节目嘉宾许子东在节目中提及我。他说:“大家知道,《小团圆》差点被烧掉,是因为宋以朗决定才给它出版,他现在垄断着一大批张爱玲给宋家的信息。”另外他又说我没把张爱玲的信件全数出版,“他说在慢慢整理中,急死人吧”。早就有人说我出版张爱玲的方式是“挤牙膏”,仿佛我故意吊人胃口。说到底,真有必要“慢慢整理”吗?甚至你还可以问,私人书信是否应该出版呢?
关于第一个问题,答案是肯定的。就私人书信而言,读者不是收信人,不可能完全明白背景,若不附注说明,只会看得一头雾水。所以不论是夏志清或庄信正,还是我的《张爱玲私语录》,都要给张爱玲的信件加上按语,而很多资料也必须核实。这就是我要“慢慢整理”的原因。至于第二个问题,即书信是否应该出版,我觉得可以借《色,戒》的事来说明一下。
2006年,导演李安向我买下《色,戒》的电影版权。我当时看小说就觉得有点奇怪,就这么二三十页的篇幅,头几页还是一群太太在搓麻将,恕我实在看不出什么戏味,李安要怎样把它拍成长片呢?于是,我又把张爱玲和我父亲在通信中讨论《色,戒》的内容看了一遍,但我完全没有想过要发表什么文章。事后,我非常后悔,如果我赶在电影《色,戒》上映前说明经过,就不会有以下事情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