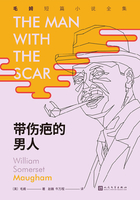前面提到过,我被指派为佩内洛普的替补是出于两个主要原因——父亲的大发善心以及他务实的行事原则,而且我觉得我母亲的遗愿可以算作第三个原因。
或许还存在第四个原因:佩内洛普和我在基因方面的匹配程度非常符合“分解球”的要求。“分解球”是一台机器,可以把你的身体分解、激发为非物质形态的分子能量场,允许你从物体中穿过,或者让物体穿过你的身体。所以,在时间机器把你送到过去时,无论你和尺寸多大的物体相撞,或者卡在物体里面(抑或是物体被卡在你的身体里面),都不会受伤。时间旅行者回到过去之后,会继续以非物质形态存在,无法触碰任何物体,也无法被别的物体触碰。
非物质形态最多可以维持十四分钟,超时之后,你的身体会变成散落开来的分子。换言之,你已经死了。从你身体分解的那一刻开始,你只有十四分钟的时间回到分解球进行分子重组,否则就永远回不来了。
因为这十四分钟的窗口期极为短暂,六名队员必须拥有各自的分解球,这样才能做到在进入时间机器之前同时被分解球激发为非物质形态。这种分子水平的仪器需要经过极端复杂的校准才能满足精确度的要求,而且非常昂贵。
有助于校准和降低成本的做法是:让两名基因吻合度高的参与者进入同一个分解球。因为如果两名参与者的基因严重不匹配,重新校准会花费很多天的时间。因此,在父亲的这项发明投入市场之前,他必须先研究出更有效的方式,但在目前的实验阶段,他还不需要操心这个问题。
佩内洛普·韦施勒的基因恰好与我高度匹配,甚至满足细胞捐献的条件——假如你存放在医院里的胚胎干细胞冷冻失败,你又患上某种分子生物学方面的疾病,就需要细胞捐献,细胞捐献还可以帮助某些类型的不孕不育者。我和佩内洛普的染色体能够像拉链那样自然地啮合在一起,当作为替补的我需要使用分解球的时候,技术人员可以快速方便地重新校准佩内洛普使用过的分解球。
他们告诉我,在所有的替补队员中,我的二次校准要求是最低的。毫无疑问,这是我唯一的优势,但这项优势应该派不上用场,因为我只是个陪练,最大的可能就是被淘汰出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