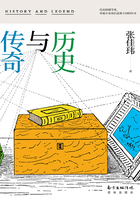十
相比京城的血雨腥风,这儿是风和日丽。
开春后,天气日渐转暖,从王娅家到山湾开阔处的小径两侧,绿竹枝繁叶茂,愈发地苍翠,洼地处的温泉不再散发浓雾,清澈的能一眼看清泉水冒出时带起的细沙,那儿成了我读书的好地方,每到午后,妮儿姐就会将一张坐榻、一张小桌,一壶茶摆在温泉旁的柳树下,待我放下怀抱里的纸张笔墨,翻开书读出声来,她就悄然离开。
空旷的山野树林间,偶有叫不上名字的鸟滑过,留下几声清脆而又孤单的鸣叫,一股潮湿柔和的暖风抚过我脸颊,在树枝上、竹叶间沙沙作响,只要我的读书声一停,四下里就静的出奇,仿佛天地万物都停了下来,我喜欢这静,静的叫人入迷、沉醉。
《左传》、《论语》这两本书我能全文背诵,尽管是囫囵吞枣、不知所云。
当然,我说的风和日丽不仅是天气,还有人和事。
每天上午照例到场院里清理卫生、洗刷牲畜,我不仅学会了使用铁叉、铲子、扫帚,还能熟练地给王木头往铡刀下喂草,连驼背三叔都会时不时地夸赞“看人李公子,闷声不响地干活,有板有眼,干啥像啥,粗看着柔柔弱弱,其实人有内秀。”
他是除我母亲之外第一个夸赞我的人。
夜幕降临,是我的习武时间。
王娅第一次教我使剑时说:“怡儿,你现在开始练剑年岁是大了点,筋骨已经长结实,剑舞是不能练了,学一些击杀、护身的很招吧,不能告诉任何人你的剑技是从我这儿学的。世人只知道公孙大娘剑舞冠绝天下,却不知她老人家也是仗剑杀人的侠客,我也不想让人知道,记住啊。你姐打会走路就修习剑法,剑技已不在我之下,你先看看我母女俩的搏杀技。”
相距十步持剑相对而立的母女脸色凝重,像是两个宿敌狭路相逢,王娅说道:“攻,使出全力。”
一直以来,我眼中的剑是将军、游侠的佩饰,是王公贵族、文人雅士用以把玩欣赏、展现权柄的器物,是身份的像征。我心里的剑是文雅、高贵、卓而不群的乐器,如同笙箫、胡琴、鼓瑟一般,而不是上阵杀敌的兵刃。
妮儿姐简单、直接、疾速的攻击王娅,挑、刺、划、抹,出手很辣,剑锋总是指向王娅最易受到攻击的部位,动作不像舞剑那样优美、灵动,甚至有些别扭,王娅挡、格、闪、跃,极力躲过攻击,妮儿姐剑尖贴上王娅的前胸时,王娅的剑锋搭在了她的颈部,打斗戛然而止。
那晚,王娅和妮儿姐用手中的剑颠覆了我的认知。
我的练习对像当然是妮儿姐,刚开始走不了一个照面,只一近身,要么被她打翻,要么剑脱手飞出,能往来反复七八个来回落败,已是在三个月以后。每次对练结束,妮儿姐就打来热水给我擦洗,仔细察看有没有伤到什么地方,一脸的怜惜,每每这个时候,王娅总会摇头叹息。
夏收到了,王七带着全村人立在地头,大吼一声:“开镰喽。”村人排成一列半蹲在地头开始收割小麦,看到村人轻松地割下小麦,我也想试试,王木头说:“这个你干不了,看着简单,其实不比上阵打仗轻松,跟着我收拢,把撒在地里的麦穗拾掇到一块儿就行。”我刚要跳进地里,妮儿姐拉住我:“不许下地,带你来只是看,知道粮食来之不易就行,我可不想让你变成粗卑的庄稼汉。”说着话对王木头直翻白眼。
妮儿姐说的话我不敢违抗,乖乖蹲在草地上,拔根青草的嫩芽儿咀嚼着,嘟囔一句:“打猎可以,喂马也行,学学收庄稼咋就不行了。”
“傻弟弟,不一样,那是雅事。”我想不出打猎、喂马雅在哪儿,也不想再争辩。
随着村人一拱一拱地起伏,镰刀很有节奏地挥舞,成片的麦子被放倒,我无聊的摆弄手里的青草,妮儿姐说:“别着急,一会儿让你看个好玩的物件。”她让王木头割下一大把青草,捋顺后编结到一起,三两下就编出个马头,我不再觉得无聊,盯着她舞动的手指,不一会儿,一匹绿色的马捧在我手里。
太阳刚升到树稍,王七就吆喝大家收工回家,王妮儿拍了拍我后背说:“回家,收工了,”“这么早。”我有些奇怪,“不懂了吧,一则正午太热,人会中暑,二则麦粒会脱落,你看,就是这样。”妮儿姐揪下一个麦穗使劲摇晃,麦粒随即飞出。
秋日的山林色彩斑斓,山坡上的草地依旧翠绿,山桃枝叶已泛出淡淡的红色,桦树林、白杨树林则一片金黄。天空湛蓝,无一丝云彩,水洗过一般干净,只对面山峦的半腰上玉带般地缠绕着一圈白雾,似凝脂一样纹丝不动。山风迎面吹来,有些凉,却教人更加清爽。
我仰面朝天躺在干草窝里,右手边伏卧着王木头,左手边紧靠着的是妮儿姐。远处是王七带着全村的男人埋伏成半圆圈,今天是一年一次的秋猎,目标是野猪。
早晨出发时,王七不许我和妮儿姐同行,说是女孩子身体自带特殊的香味,野猪鼻子很灵,顺风一里外就能闻到,姐弟都不能去。妮儿姐不依不饶,说道:“七叔,弟弟必须去,我呐,得守着他,你看怎么办吧,反正是跟定了。”我清楚这是王七不想让我两涉险的借口,并没有说破。
王七拗不过妮儿姐,只得带上我们,到了山隘口,在野猪经过的三条道的其中两条上安好铁夹子,挖了陷坑,一条道上什么机关也没有布置,王七他们就在这条道下风口的半山坡埋伏下来,把我和妮儿姐安置在远处,让王木头守护。
有了年前抓獐子的经历,我多少知道些他们围猎的办法,但还是想弄个明白,问身边的王木头:“木头哥,给我说说为啥要留出一条道让野猪通过?”
“这是留的生路,野猪很有灵性,同伴中了夹子、掉进陷坑,野猪群就会选另一条路,这条路就是留给它们的逃生之路。”王木头说。
“这么神。”我惊叹道。
“再神也斗不过人,你们哪年不弄回去四五头。”妮儿姐说。
王木头接话道:“那是,我爹说人才是万物之灵,不过有时候也会发生意外,三叔的腰就是野猪伤的。”
“这个我知道,是和尚叔讲的,那年野猪群没有走三条道中的任何一条,直接冲上山坡,埋伏的村人猝不及防,一场人猪大战后,三叔伤了腰。不过那年收获也最多。”妮儿姐说。
“既然野猪那么聪明,会不会从其它地方翻过这座山。”我还是很疑惑。
“不会,它们要到过冬,只有通过这个山口,年年如此。”王木头停顿一下接着说:“留的这条路就是让野猪知道,我们并不想赶尽杀绝,谨防野猪在绝望中死拼,我爹也搞不清那年野猪中了什么邪,那条路都没走,直接朝人冲过来,打那次出事后,每年猎野猪都要准备大枪、盾牌、火种。但愿这样的事别再发生,太可怕。”
太阳没入西边的山坳时,山风渐渐变大,风中夹杂着一丝腥臭味道,王木头说声:“准备弓箭,来了。”
我翻身坐起,取下弓,抽箭搭上弓弦。
山脚下什么也没有,只是风中的腥臭味愈发浓烈。
远处王七在朝我们挥动手臂,三人弯腰跑过去,王七紧绷着脸,神情凝重,说道:“不对劲,味道这么大,它们应该到了,咋还看不见,听着,准备好火镰。把李公子、小主人围在中间。快点。”
一阵沙沙声传来,山脚下出现一片棕黄色,先是一声尖利的嘶叫,接着嘶叫声结成一团,此起彼伏,我从来没有听到过这种声音,像是那种将要死亡时的哀鸣,也像是拚死一搏时的嚎叫,更像是生命结束时的惨吼,刺的人耳朵疼,那片棕黄色开始缓慢移动,待能看清最前面足有牛犊子大小的野猪时,嚎叫声停了下来,整片的棕黄色突然四散开来,到处是呼哧、呼哧的声音,王七大叫:“开弓,放箭。”几十枝长箭飞过去,只有两三枝射中,有的箭射到野猪身上被弹开,一头中箭的野猪倒地嘶叫,野猪群并没有放缓爬坡速度。
那头最大的野猪奔跑起来,“放箭、放箭,”王七的声音越来越急,越来越高,近乎嘶吼,有几头野猪中箭倒下。野猪群渐渐逼近,已经能看清前面野猪鲜红的眼睛和朝上翘起的獠牙,王七大叫着:“点火,立起盾牌,准备大枪。木头护好主子。”
黑暗好似突然降临了,火堆和浓烟阻止了野猪的进攻,片刻后,那头最大的野猪狂奔起来,绕过火堆,高高跃起,重重砸在王七的盾牌上,身后的王木头从盾牌缝隙捅出大枪,扎中野猪腹部,猛地抽回,野猪哀嚎一声,扭身就跑,野猪群随即转了方向,涌上了留给它们的生路。
村人收拾好铁夹子,用大枪扎死受伤后掉队的几头野猪,捆绑在木杆子上抬着往回返。
尽管猎物丰厚,大家却没有守猎成功的喜悦,只是闷头走路,似乎还没醒过神来。我很想问王七,他们每年捕猎,野猪群都是丢下被铁夹夹住或者是掉进陷坑的同伴逃命,偏偏我和妮儿姐参与捕猎,野猪群就冲上来袭击狩猎者。又一想这样的事曾发生过一回,谁也说不清原因,看着王七低头纳闷的走路,把想问的话吞了回去。
这个疑惑困扰了我许多年,直到碰见一位见多识广的伊姓景教长老,他给出的答案是:“王家旮旯的人长期生活在山林之中,身体里已融入了山间的林木、动物气味,野猪不易分辨。而对野猪来讲,智诚和尚和我是生人,野猪群闻到生人味,察觉出危险,选择了攻击。”
无论这个结论是否正确,我都得接受,总不能让我去问野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