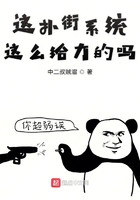见他及其产出神地盯着房间看,滕跃然极其不悦道“谦然!”
被这吼叫,刚才堪堪回神,面上倒是丝毫不见被抓包的尴尬,只是复又淡然的看着他“兄长,你可知嫂嫂如今的叔父在何处高升?”
“我道是什么了不得的,不过是个四品四品侍郎,又有何惧?”当他还说道什么,听着嘴下勾起嗤笑。
这笑意落在滕谦然眼里更觉可笑,一双瞳里夹在这可笑,面上确实丝毫不显露“若当真是四品那倒是简单了,想来兄长是在这宅院深深里柯梦难醒,不曾关乎外头的事情。”
满耳的讽刺,滕跃然早已经不耐“有话便直说,何至于夹枪带棒让我难堪。”
“或许兄长不知,嫂嫂的叔父已从侍郎直升为正三品尚书大人了。”
这消息甚是出乎他的意料,忙惊呼了一声“怎会!”
那表叔他一贯不拿他作数,毕竟是个左右青黄不接的,侍郎这个职位其实尴尬,伤头有顶头上司尚书压着,自然翻腾不出什么风浪来,但如今,他若为尚书那便是大不相同了,这个表叔直属吏部,吏部下设吏部司、司封司、司勋司、考功司,掌管天下文官的任免、考课、升降、勋封、调动等事务,大约上封之事全是仪仗,是说任谁申壬都是由天子断定,但所有资料都是出自吏部,若当真惹他不快,相比入仕高深之路也是断了干净了。
“吏部之重,想必兄长多有了解,这姻亲之好本也就是为了锦上添花的,何必图惹是非,成了怨怼,徒增事端,难不成想我滕氏子弟的柬帖再递不上天厅?至此无路吗?”说着眼里是世态严重的肃萧之气,一瞬不瞬盯着他,警告他!
之前还觉得无甚所谓的腾跃然,现在心上不免还要掂上一掂了,面上变得有些难看。
“还有一事,你可知,这叔父可是找了个好靠山?”
靠山?什么样的靠山?以至于他滕家一组都好忌惮?滕跃然似是想到什么?孥了孥嘴终是没敢说出。
只是那谦然看的明白,眼中嗤笑更甚,心中只叹现如今这兄长竟然还望自欺欺人?“便是那摄政大人了”这话一出,原本还略信旦的滕跃然面上都白了三分!一时间觉得骇意深入骨髓,这般日头,竟然觉得寒冷冰凉彻骨,后怕敢侵袭而来。
忽的,戚长在房内听到摄政二字,心头突突直跳,便觉得浑身僵硬窒住,身上血液逆行,心中缓缓升出一种苍白无力感,到底他是如何沦落至此,竟然发生这样匪夷所思的事情,若非往日记忆如走马历历在目,见她都要觉得自己魔怔了。
他复又仔细回想,他所谓的那位叔父到底是是谁,实则,自己的亲信自然遍布朝堂,吏部自然也是有的,只是这朝堂之上百废待兴,六部人员皆有跳动,他尚不能确定,可能人员尚有五位不止,所以不论是谁,这叔父这条线断不得,他本也不在意这原配是何处置,现在还需依赖这原配附中朝堂才是,但不能让她有任何闪失,要尽快与这朝堂之人取得联系才是。
他在房内百转千回思索着,外头却是僵持住了,自然是这藤跃然被面前阿弟逼得节节败退,几乎没有尊严,尚无台阶下来,这滕谦然这回确实毫不退让,似乎非要面前兄长低头认错。
两兄弟便这般僵着,滕跃然面色难看至极,风簌簌吹起,衣袂翩翩。
戚长那一宛若清泉银铃般的声音自房内响起,如沐春风般抚慰心弦。
“郎君,风浓忽忆起当日昏迷之际隐约见夫人相救之姿,风浓如今已然大好,却未来得及与夫人道一声谢意”他昏迷时哪有见到什么夫人相救之姿,醒来已然失忆,这事情腾跃然也是知道的,现在见他如此,便觉得这风浓当真值当他一句心肝,实在是贴心啊。
来了个台阶下,这腾跃然自然顺势而为,只拍了拍自己脑袋,佯装怒意道“你何意现在才说,让我平白误会了夫人,既如此,你便好生休息,我先去看看夫人才是。”
说着便是匆匆卖了脚步走出了院子,那滕谦然只是略带着意味深长的笑意又盯了盯自始至终规闭的房门,转身便跟上了滕跃然的脚步,事情似乎开始好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