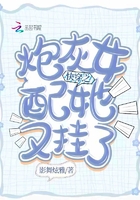李守礼被捉进了衙门。
门前死了人,就是浑身是嘴也说不清。衙门亲自来人,带刀捕快拿人,王玉凤想要作证,可东南巷道,人微言轻,又有谁真正听得了她的话?无非是浪费些口舌罢了,到头来一文不值,少年粗布,坦坦荡荡,即使是嫌犯也依旧挺直了胸膛。先生曾说过,君子不立危墙,可若真的有朝一日墙塌了,也不必弯腰……
小镇不大,小半个时辰,死人的传言已经甚嚣尘上,东南巷道倒是第一次展现在那些富贵人家的眼前,只不过也是掩着口鼻匆匆望了一眼,仿佛多看一眼就脏了自身一样。
李守礼被换上了囚服,扔进了大狱,少年没有愤怒,也没有恐慌,平静的很,死人都见过,血水染了衣襟,还怕这丈许牢房?只是气味儿着实不好闻,腐朽夹杂着极淡的霉味儿,让李守礼有些念家罢了。怪不得曾听说那些个富贵人家有人一入大狱就疯了,想来也是舒坦日子过多了,禁不起打击。可这对于李守礼来说就显得有些微末了,十几年的打磨,东南巷道也不见得比这牢狱好多少。
落幽河畔,终于是有了变化,大河奔腾,其音似九天神雷,隆隆作响,鱼儿争相跃出水面,若是有心人观察,定能看见它们的不同,姹紫嫣红皆浑然,有一枚金色鳞片隐藏在每一尾鱼儿的背脊处,金辉点点。
小镇中,老道人掐指一算,摇头晃脑道:“造化已有主,全都是徒劳而已,说不得还要留下一二性命,七情六欲终究是过不了,也对,圣人都是如此,遑论其他?”
摊子前,两方布,知生知死,知因知道,如今再看来,倒也有几分那么神仙气韵。只是仙神全有理,也管不了人心,贪欲作祟,却忘了知足才能常乐。老道人似是想到了什么,咧嘴一笑,露出了两颗大黄牙,道:“那小子倒是知足,十几年也不见追根溯源,是铁打的心吗?”
私塾里,朗朗书声依旧,对于这些鼻涕娃来说,死人离他们太远了,每日关心最大也不过何时下学,顶天了也就是去哪撒欢儿。教书先生站在院中,目光悠远,望着的方向正是落幽河:“千万不要动了不该妄动的贪念,否则落幽河里说不得要添上几条亡魂。”
倒是衙门之中隐约有咒骂声传出,翻来覆去也就那么几声,也不知是何人在怒骂,“老掉牙的老不死,成天摆弄,老子迟早有一天拆了你那两颗大黄牙!还有私塾里的那个笑面虎,长着一张脸,也不知道勾搭多少黄花大闺女!”
……
王玉凤吓坏了,妙龄女子何时见过死人?还是那般血腥,血水流淌,就似妖魔杀了人。王乞丐心疼啊,可李守礼被下了大狱,让他有火难出,想找个人骂骂都找不到,倒是王玉凤的乞丐娘长着一副泼辣模样,竟直接骂到了衙门门口,这倒好,直接让衙门里的大人抓到了出气筒,命人捉拿,狠狠打了一顿。王玉凤不忘那一碗“鱼恩”,即使惊吓过度也想为李守礼作证,只是“无处话凄凉”,根本没有人听。
小镇上的人都认为李守礼这次该是要偿命了,杀人抵命,欠债还钱,这是天经地义,自古以来的规矩就是如此。就是李守礼自己都以为大抵要如此。大狱中,少年靠墙坐着,李守礼在思索,那人为何会出现在自家门口,再联想那钓叟与面纱女,一时间竟有些头疼,少年揉了揉眉心,自嘲道:“这就是命,十几年前的那个大雪夜就该死,十几年的时光,合算!”
李守礼很乐观,即使是如今这个境地,也不见他痛哭流涕,脸上挂着的也只是冷静罢了,甚至有时候还有丝丝缕缕的笑意,也不知是想起了这十几年来的哪一抹温暖。
是随打更人一起打更,还是先生门外的朗朗书声,亦或者是与王玉凤的家常拌嘴……
时间飞快,转瞬即逝,三日就像是一睁一闭眼。李守礼终于是察觉到不对,这大狱看起来倒是可怕,但为何三天过去了也没有一个人来审他问他?反而将他晾在此地,不闻不问,除了每日送饭才能见到一人,其余时间,孤寂的很。
这一日,辛丑年丁酉月二十八日,再过两天就到了十月,落幽河翻腾,金光漫天,惊动了诸天神佛。小镇亦沸腾,生人身影眨眼成空,到底是没能经得住诱惑,那泼天造化遮蔽了人眼,看不清各自的斤两。来者皆是修道人,只信缘法,大多都觉得与此造化有缘,可人心通透,到了自身,也全然看不透,不,或许是不想看透,就像那死在李守礼门前的男子,老道人有了一签之言,救得了就救,救不了也算了,不可再多说,多说就是天机。
而天机最是玄妙,不可泄露。
白净和尚拈花一笑,端的是我佛慈悲,可谁也不知,那东南巷道亡魂最是恨佛。
病马驱车,病老头咳嗽连连,也在摇晃间赶向落幽河畔。
那夜小镇外山岭间的妇人与少年亦是如此,造化显现,龙门一跃,即可化龙。
此龙非彼龙,并非成龙身,而是有了真龙命。
此为钓叟所言的天命加身,亦是教书先生星空所望的紫薇帝命!
落幽河畔,钓叟盘坐,依然在垂钓,蓑衣沾染上湿气,看起来倒像是个假人,背对着苍生万民。
“来喽,鱼儿上钩了。老朽既言护那幼龙,又岂能容你等放肆。可千万别扰了老朽的兴致啊……”
衙门里,那位大人神色凝重起来,气息浮动间,又是骂出了声:“只管脱了裤子放屁,却从来不管会不会带出屎来,难不成老子天生就是擦屁股的命?!哼,此番若是动静大了,你们以为让他待在大狱中就安全?”
清风吹过,到底是无人回答他,只有天地间掉落的一两片枯黄树叶,显得寂寥无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