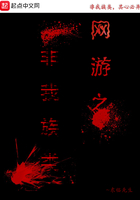一九四四年十月下旬的一个下午,我惊讶地发现父亲独自一人坐在厨房小桌旁。他一天的工作时间通常开始于早上七点,晚上下班往往要拖至十点。那天他突然要去医院割阑尾,收拾好了一只包裹在等哥哥桑迪和我放学,叫我们不必惊慌。他向我们保证“没事的”。我们清楚,早在一九二〇年代,他的两个兄弟都死于阑尾切除术的并发症。那一年,母亲是我们学校家长教师联谊会的主席,正好在大西洋城过夜,为了参加全州范围的家长教师联谊大会,这颇不寻常。在父亲打电话到酒店告知她后,她立即准备回家。我相信,一切都会回归正常。妈妈的治家才干可与《鲁滨逊漂流记》的主角相提并论;她护理我们战胜所有的疾病,即使在弗洛伦丝·南丁格尔那里,我们也得不到更好的照料。事事都会在妥善的掌握之中,那就是我家当时的惯常状态。
那天晚上,当她的火车缓缓驶进纽瓦克车站时,外科医生已打开父亲的腹腔,看到的情形一塌糊涂,开始为他的康复感到绝望。他才四十三岁,就上了病危名单,存活率低于百分之五十。
只有大人才知道当时情形有多糟糕。我和桑迪被允许继续相信,父亲是坚不可摧的——结果,我们的信念还真灵验。尽管父亲多情善感,极易陷入顽固的忧虑,但他的人生标记仍是他东山再起的毅力。我亲密相知的人士中——除了哥哥和我自己——真还没人能比得上他。他情绪的跌宕起伏,幅度既大,速度又快;他对各种事物认真在乎;遇上严重的挫折,坦然地承受折磨;等挫败感渐渐平息下来,他又积极攀爬回去,收复失地,再次向前。
他因新近问世的磺胺粉剂而获救,该药开发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早期,用来救治战场上的伤兵。无论如何,幸存的过程仍是一段可怕的考验。近乎致命的腹膜炎令他非常衰弱,一连十天的打嗝更是雪上加霜。那段时间他无法入睡或进食,体重掉了近三十磅。在我们的眼中,他皱缩的脸庞简直就是我们老祖母的拷贝。他和兄弟们都崇拜自己的母亲(对父亲——一名话不多、专断、冷漠的新移民,在老家加利西亚时学做拉比,来美国后一直在帽厂工作——则怀抱比较复杂的感情)。伯莎·罗斯是一名简单善良的乡村女子,既不郁郁寡欢,也不牢骚满腹。但她日常的面部表情显示,她对安逸的生活从不抱任何幻想。父亲的长相与祖母的神似,这点要到他八十多岁时,才再一次诡异地呈现出来。其时,他陷入了一场生死博弈。这位体格尚算健康的老人,外表上的坚不可摧已被剥夺,只剩下一脸茫然。他的视力问题或行走困难,严重损害了他独立自主的能力。但更主要的是,他突然发现自己不再拥有意志力;在过去,意志力一直是帮他排忧解难的卓越助手。
他在纽瓦克的贝斯·以色列医院足足躺了六个星期,出院坐车回家后,尽管有我们的搀扶,却几乎无力爬上我们二楼公寓并不太高的后梯。那是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一个寒冷的冬天。透过窗户的阳光照亮了父母的卧室,桑迪和我进来问候,既害羞又心存感激,为他的无助感到震惊。他有气无力地坐在角落里一把孤独的椅子上,看到我俩时再也无法自控,开始抽泣。他还活着,阳光明媚,他的妻子不是寡妇,他的儿子仍有父亲——家庭生活可以重新开始。一个十一岁小男孩无法理解父亲的眼泪,这一点都不复杂。他心里非常清楚,但我当时实在看不透,难道还会有不同的结果吗?
我知道,在我们的街坊中,只有两个男孩的家里少了父亲。在我眼中,他们的不幸不亚于当时的一名盲人女同学。她曾来我们学校一段时间,全靠他人的朗读和引路。没有父亲的男孩似乎与众不同,在他们的父亲去世后,他们留给我的印象有点可怕,甚至带点禁忌。其中一个是模范服从者,另一个是麻烦制造者。他们所做的一切,似乎都与他们父亲已经死去的事实有关。这种想法尽管天真,但很有可能是正确的。
我不知道街坊中有离婚家庭的孩子。除了在电影杂志和小报的头条新闻中,离婚是不存在的,肯定不会出现在像我们这样的犹太人中间。犹太人不离婚——不是因为犹太法律禁止离婚,而是因为这是犹太人的生活方式。没有犹太父亲喝醉回家,殴打自己的妻子——在我看来,我们的街坊就是犹太人的街坊,从没听闻此类轶事——也是因为这是犹太人的生活方式。在我们的意识中,犹太家庭是不容侵犯的避风港,它对抗一切威胁,不管是个人孤立,还是非犹太人的敌意。它被认作是一个牢不可破的团结堡垒,无论有多少内部的摩擦和冲突。听吧,以色列,家庭就是上帝,家庭就是一个整体。
不可分割的家庭是第一条诫命。
在一九四〇年代后期,当父亲的弟弟伯尼宣布,打算与育有两个女儿、相处近二十年的妻子离婚时,母亲和父亲都惊呆了,仿佛听到他犯了命案。伯尼如果真的杀了人,被关进监狱,尽管这是可憎和费解的罪行,但父母仍可团结在他的背后。但是,当他打定主意,不仅要离婚,还要去娶一名更为年轻的女子,他们的支持马上倒向“受害者”,即弟媳妇和侄女们。由于他的罪过,即违信于自己的妻子、孩子、家族——抛弃他作为犹太人和罗斯家族一员的职责——伯尼受到几乎一致的谴责。
时过境迁,离婚并没摧毁任何一个人,家庭的分裂才得以慢慢愈合。事实上,伯尼的前妻和两个女儿,虽因家庭解体而忍受痛苦,却从没像其他亲戚那样地愤愤不平。很大程度上,愈合的成功归功于伯尼本人,他比审判他的大多数亲戚更善于外交。另外一个原因是,对父亲来说,家庭团结的必需和家庭历史的纽带,战胜了他喜欢劝诫他人的本能。不过要到四十多年后,两兄弟才张臂拥抱,以一个明确无误的行为,来昭示他们无条件的和解。这发生在伯尼去世的数星期前,他已七十多岁,心脏急速衰竭,没人指望他能活多久,包括他自己。
我开车带父亲去看伯尼和他的妻子露丝,他们的公寓坐落在康涅狄格州西北部的一个退休村,离我家二十英里。这一次轮到伯尼换上他那坚忍老母亲的小脸开门让我们进来时,他的容貌就呈现出这一神似。一遇到这样的困难时刻,它似乎会在所有罗斯兄弟的脸上出现。
通常,两个男人见面时握个手就行了。但当父亲步入走廊,大家一下子变得心知肚明:伯尼的时间不多了,几十年的分隔追溯到最初,那时两人都还是父母膝下的小兄弟。于是,握手被有力的拥抱替代,持续整整几分钟,两人都热泪盈眶。他们似乎在说再见,跟已经过世的人,也跟对方。他们是严厉的制帽匠森德和冷静的伯莎幸存下来的最后两个孩子。伯尼安稳地靠在哥哥怀里,似乎也在向自己告别,没有丁点的防范、抵抗、反感,甚至没有回忆。兄弟俩之间尽管有差异,但都深切感受到同样的亲情煎熬;所忆起的一切都是沉淀下来的纯真性情,简直叫人难以承受。
父亲回到车上说:“上一次这样拥抱,我俩还只是小男孩。我的弟弟快死了,菲利普。他坐在婴儿车里,我曾推着他到处闲逛。我母亲和父亲共养育了九个孩子,我将是最后一个。”
在开车回到我家(他就睡在我家楼上的后卧室,声称每次都能像婴儿一样倒头就睡)的途中,他重述了他五个兄弟坎坷的人生——破产、疾病、亲家争执、婚姻纠纷、不良贷款、子女麻烦、他们的高纳里尔、里根、考狄利娅[2]。他还忆起他唯一的妹妹的殉难,以及她和所有亲戚所承受的苦楚,她的簿记员丈夫喜欢赛马,因贪污坐牢。
我并非第一次听到这样的故事。他的知识的表达形式就是叙事,但他的叙事内容从不丰富:家庭、家庭、家庭,纽瓦克、纽瓦克、纽瓦克,犹太人、犹太人、犹太人,有点像我自己的叙事。
作为一个孩子时,我曾天真地认为,我永远有一个父亲,现实似乎证实了这一点。我们有时相处得尴尬,很容易发生分歧和误解,虽有不同的人生经历,却有同样的不耐烦和任性,相互碰撞,徒增紧张,外加男人的笨拙。尽管如此,我与他的联系仍无所不在。更重要的是,现在,他不再以鼓起的肱二头肌和道德约束来攫取我的注意力,也不再是我必须抗衡的庞然大物——我自己也在渐渐步入老境——我变得能够享受他的笑话,握着他的手,关心他的健康,以自己十六、十七、十八岁时所憧憬的方式来爱他。当年,既要与他打交道,又觉得抵牾迭起,这种形式的爱是不可能的。由于他所承受的特殊负担,以及他在无法自选的制度中的挣扎,我对他素来怀揣尊敬。在我这样的家庭中长大,犹太男孩需要扮演一个神话角色——成为父亲未能成为的英雄人物——我可能已获成功,只是没有通过预定的途径。我远离家人将近四十年,现已做好准备,极欲充当一名最有爱心的儿子。然而,他却拾起了另一日程,就是为死做准备。他嘴上不说,可能也不作此类的思考,但这就是他眼前的工作。他会尽量求生,但一如既往的,很清楚什么才是自己真正的工作。
为死做准备不同于尝试自杀——事实上可能更难,因为你在试图做的,却是自己最不希望发生的。你惧怕它,它又客观存在。这份工作必须完成,没人帮忙,全凭自己。过去几年中,他已有两次在鬼门关外徘徊,突然在两个不同的场合病得很重。我当时一年中有一半时间住在国外,赶紧飞回美国,发现他如果没有椅子的支撑,几乎无力从沙发那儿走到电视机前。医生每次为他做细致的检查,都找不出病因,他仍旧每天晚上上床,做好第二天早晨再也醒不过来的准备;醒来之后又需要足足十五分钟,让自己在床沿上坐起来;接下来的剃须和穿衣,还得花费整整一个小时;然后,天晓得是多久,他伛偻着坐在一碗麦片粥面前,一动也不动,全无食欲。
我和他都认为,这可能就是他生命的终点,结果他却没死成。经过数星期,他得以恢复体力,再次成为早先的自己,厌恶里根总统,维护以色列,打电话给亲戚,参加葬礼,写信给报纸,咒骂威廉·巴克利[3],观看《麦克尼尔·莱勒》[4],告诫已成年的孙子,巨细无遗地回忆离世的亲人,正确无情地——全是自告奋勇的——监督善良的同居女子的热量摄入。尽管有社会地位和教育水平的欠缺,他曾在保险业取得显著的成功;相比之下,现在尝试死去,似乎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当然,他最终也会成功——尽管对分配在自己名下的每一份工作都尽职尽责,但很明显,事情并不那么简单。不过,他的遭遇从来都不简单。
毋庸置疑,我与父亲的联系,从不像我与母亲的纽带那样有形、能带来身体上的愉悦。她的身躯已化成一件光滑的黑色海豹皮外套,而幸福地钻进这外套取暖的,就是我这个最年幼、享有特权、受到溺爱的小男孩。那是一个冬天的星期日——我们每半年去一次曼哈顿的无线电城音乐厅和唐人街,父亲正开车把我们送回新泽西的家。我好比一头无以名状的小动物,冠上了已逝外祖父的名字;又好比仍处原生状态的小男孩自身,正在学习如何掘穴藏身;通过每一根神经末梢,与母亲的微笑和海豹皮外套相连。而父亲彻底的尽责、不懈的勤奋、不通情理的固执、苛刻的怨恨、幻想、无辜、忠诚、恐惧,也都是我的原型,让我成为今日的美国人、犹太人、公民、男人,甚至作家。活着本身就是以她的菲利普活着;但在与动荡世界的碰撞中,我的历史仍要以他的罗斯开始。